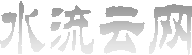徐晋如《缀石轩诗话》
小 序
亥年残冬,蓝师棣之嘱予代撰《二十世纪诗歌史》诗词部分。受命之后,终日乾乾。都计四万余言,阅三载廼毕其功。其犹有未尽之言,则随掇纸什,拉杂书之,自去岁春暮以迄今日,遂渐蓄积。尝思诗话一体,嚮爲吾国文艺批评之大宗,西学东渐以来,虽稍抑其势,尙有王静安《人间词话》、顾羡季《驼庵诗话》、吴世昌《词林新话》之清音缭绕。其自成体系之处,何尝输与现代学术文体哉?于焉因古人之通例,援斋号名之曰《缀石轩诗话》。予于唐宋名篇,多不寓目,而独喜近代以来诗词。故诗话之范畴亦坐此。予之论诗,不重词采,仅重生命,世之知我罪我,并在于斯。
庚辰初夏
徐晋如 于都门
谭復生《仁学》第二十章云“乡愿贼德”,真斯人也而有斯语也。《莽莽苍苍斋诗集》天才卓荦,远超群侪,一言以蔽之,在明乎诗源。夫诗源者何?生机也,元胎也,闻一多所谓有诗骨者也。“与其死于蜮,孰若死于虎”(《鹦鹉洲弔弥正平》)、“短衣长剑入秦去,乱峰汹涌森如戈”(《秦岭》),并具及汝偕亡之慨,乡愿人宁有此哉?
予所赏稼轩者,彼词场之诗人耳。但就情感而言,予深推服其“绿树听鹈鴂”,悲凉激越,一挽颓唐风致,然以夫临于理想论,终不若“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沈著。此真大慈悲、大愿心,殊觉诗家说禅,太多乔张致。世但赏其前阕“少年不识愁滋味”,信乎衆庶之滔滔,难与言也。清季以还,独任公“愿替衆生病,稽首礼维摩”境界差似。
沧趣楼集《次韵逊敏斋主人落花四首》“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一联足压终卷。翻嫌“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太露形容。
王静安先生早年负意气太甚,后廼悔之。壮岁颇喜倚声,尝自矜其词,谓可与北宋诸家相亚。顾不知有宋一朝,自南渡后乐府方臻大雅。静安祇说一个天然——“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不知人工之可以夺造化也。
王国维五古诸作,睥睨千古,当时亦允称独步。《冬夜读山海经感赋》:“兵祸肇蚩尤,本出庶人雄。肆其贪饕心,造作兵与戎。帝受玄女符,始筑肩髀封。龙驾俄上仙,颛顼方童蒙。康回怒争帝,立号爲共工。首触天柱折,廼与西北通。坐令赤县民,当彼不周风。尔臣何人号相繇,蛇身九首食九州。蠚草则死蠚木枯,嗚尼万里成泽湖。神禹杀之,其血腥臭不可以生五谷,湮之三仞土三菹。峨峨群帝臺,南瞰崑崙虚。伟哉万世功,微禹吾其鱼。黄帝治涿鹿,共工处幽都。古来朔易地,中土同膏腴。如何君与民,仍世恣毒痡?帝降洪水一荡涤,千年刚卤地无肤。唐尧廼嗟咨,南就冀州居。所以禹任士,不及幽并区。吁嗟乎,敦薨之海涸不波,乐池灰比昆池多,高岸爲谷谷爲阿,将由人事匪有它。断鳌炼石今则那,奈汝共工相繇何!”格调高古,体制俨然,一种清癯刚健之态,眞可压倒渊明。颐和园诸词声价重于鸡林,不过如《长生殿》、《桃花扇》,虽蒙盛誉,要非词场本色。盖王词欲效梅村,究逊梅村十分之风流。观堂中年穷治元曲,而绝不涉足歌场,大抵生性不能秾艳,学力亦难致之。
鲁迅先生诗作不衫不履,自有无限风流蕴藉。一枝清采,莲蓬人咏,并可想见爲人。翻空妙手,不仅《亥年残秋偶作》而已。
“旱云如火扑晴江”、“但见奔星劲有声”(《赠人》二首),《文镜密府论》所谓“飞动体”也。其生命力磅礴两戒之外,充塞天地之间,绵绵然,汩汩然,而无陵人之势,沛然广大之中,尙具一种醇和温润之意。
元轻白俗,宜罹方家之讥。然元自有情真处,白亦有雅致处,以视当今诗人,不啻霄壤。古今之辨,不但情志耳。“小康奔嚮大康门”,足可令泥人失笑,评论家尙谓爲服务工农兵。
绀弩体如麻辣烫,入口尙佳,但无余甘,是其短处。
沈则不浮,郁则不薄,古人先我得之。今读散宜生集,就中得失,体会尤深。程千帆谓聂氏“滑稽亦自伟”,是何语邪?但滑稽便不自伟。优孟师涓,不闻兼于一人。
北荒诸草,託体稍卑,而语多俚俗。廼今人谓爲奇巧处,卽是其穿凿处。因知南明以《燕子笺》祀天,尙有可恕之道。
南社群公诗,要以黄晦闻节先生称首。“错被美人回靥看,不如漂泊满江南”,望帝春心,引人泣下。虽曰变雅,不啻黄鍾。
苏曼殊句意清浅,但不碍其情真。曼殊清浅处,便是旁人不能到处。天真烂漫,今谁存者?
柳亚子诗非不豪壮,一发无余,祇少无穷蕴藉。
同光体制,实开汉诗近代化之先声。
乐府灭然后诗兴。故知宗宋者生,宗唐者死。
画工者诗卽不工。绘者冀出尘,诗家重入世。如苏曼殊者尙罹诗不如画之讥,郁达夫可谓知言。
杨云史圻自敍行状,谓“我少年时,闻有诗人我者,则色然怒,今闻之则欣然喜。”余自去秋以来,渐了此意境。
杨云史晚年作《天山曲》,浑非江湖庙堂之忧,已隐具希腊精神。“当年助顺闢蒿莱,别有降王壁垒开。一骑香尘烽火熄,明驼轻载美人来。沙场风压貂裘重,阵云满地衣香冻。祁连山月远相随,恸哭爷娘走相送。琵琶凄绝一声声,大雪纷纷上马行。一拍哀笳双泪落,可怜胡语不分明。王头饮器献天子,妾心古井从今始。何难一死报君恩,欲报君恩不能死。”纯是现代意识。金仲荪剧作《文姬归汉》立意略同。云史早岁尙有《檀青引》,体制、气魄稍逊《天山曲》,主体意识则远自不如。
丘逢甲题黄遵宪天问楼联:“陆沈欲借舟权住,天问翻无壁受呵”,真古今第一伤心语、第一愤慨语也。殆由血书,字字皆碧。
丘逢甲诗如程长庚,黄鍾大吕,振聋发聩;陈三立诗如谭鑫培,抑郁悲凉,凄怀感怆。昔程长庚谓谭鑫培:“我死后,子必独步,然子爲亡国之音也。”散原诗亦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然自不失风雅之正。较诸沧海,毕竟未易轩轾耳。
或问余何以能致诗人,应曰:“好色而淫,与民同之焉尔。”
今日之西方诗论尙复义、陌生化,以爲独得之密,不知吾国古诗託比兴于香草美人、炼奇句于平常语外,并与之隐合;又西方自S·艾略特以来,倡言文化入诗,以爲超前,不知吾国之诗人未有不学者也。
易得郁达夫之清丽,难得郁达夫之清癯。恰如赏兰者衆,赏菊者稀。有能味郁达夫之清癯者,不徒知郁达夫矣,更足与论黄仲则。
史笔爲诗,祇在援入苍茫正大之气,倘以诗纪史,本末淆矣。人境庐集多罹此病。余所以崇仙根而抑公度也。
诗道所重惟在贵己。贵己之说,倡自杨子,实吾国思想最具光彩者。贵己则自我充盈,元胎斯具,气格廼生,终至沛然广大,无往而不利。词遒笔健之夫,气格或可仰而仅至;若夫元胎,赤子也,婴孩也,苟非自我,孰足成之?黄公度大篇富气格而乏元胎,消息请于此中探寻。
世间一切第一等诗词,情感必具个人化、超越性之色彩,初与社会集体无涉,故奉命文学鲜有足称。诗人自当悲悯人群,要须是悲悯人群之个人,当谨守自我,固藏元胎,慎不可走洩。罗膺中庸《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絃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祈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调寄《满江红》)虽奉命文学,而“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北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冯友兰评语),词意警拔,寄託幽微者,正坐元胎在焉。当彼之时,个人之追求、自我之追求、之理想,亦爲全中国、全中华民族之追求、之理想,故能守藏自我,葆其元胎。苟非其人,苟非其时,则不能成此绝构。
古今诗人元胎之健未有过于屈原、丘逢甲、陈独秀三子者。其人则鸷鸟不群,戛戛独造,其诗则海啸霆奔,峻极八表。持上数家以视太白,不过一轻薄儿耳。
予不读清浅才人诗。
沈乙庵“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亦“一寸春心红到死”之伦。独寐寤言,居然沈著。理趣而济以深情,斯方足称至境。
吴白屋诗如幽谷佳人,荆钗粗服,自不掩其国色天香。“衣食情性灭,追念以日稀”,于生命不作丝毫苟且。
吴芳吉谓,文学祇有是非,而无新旧。诚哉斯言!自生民以来,文学之所以爲文学者未有根本改变。
天地间至诗,盖皆阳刚爲体,阴柔爲象之俦。体者性命,象者皮囊。然苟无修姱之皮囊,亦不足动人心魄。《易》不云乎,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有体无象,或至叫啸,或至枯寂;有象无体,或至淫靡,或至淡薄。诗中如屈子、老杜,词中如稼轩、白石,并皆得体象之祕。余标出定庵“西池酒罢龙娇语,东海潮来月怒明”一联,以爲体象之妙独绝千古。陆机云:“诗缘情以绮靡。”是之谓也。
柳亚子郭沫若有体无象。剑气不以箫心爲佐,祇一大花脸也。
或拈清空以救呼嗥叫啸。清卽是体,空卽是象。
《今别离》四章,非徒无佳妙而已,直是无聊。爲文而造情,面目忒亦漫漶。
苦水“长眉山样碧,跣足白于霜”,意态幽绝冷绝,第终不掩眉宇间婞直之气。薜萝山鬼,不过于是。全阕调寄《临江仙》,出《荒原词》:“皓月光同水泄,银河澹与天长。眼前非復旧林塘。千陂荷叶落,四野藕花香。 恍惚春宵幻梦,依稀翠羽明珰。见骑青鸟上穹苍。长眉山样碧,跣足白于霜。”体象佳处,不让尧章。
陈衡恪“扁舟无力回天地,雨打风吹过石湖”一联(《忆石湖旧游》),曲尽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份子心灵意态。
文学者,倡优之事业也,亦动夫人情而已。惟红儿雪儿,媸妍何殊;名家俗匠,高下迥别。
“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此周作人少作《天管风筝》所赋。知堂中年变节,于此实种其因。
林庚白氏爲人英风侠慨,磊落无俦。至其描摹闺房之乐,则有“隐约乳头纱乱颤,惺忪眼角髮微披”、“乍觉中间湿一些,撩人情绪裤痕斜”之语,是真名士本色,不滞于物,英雄胆略,至今无匹。
闻一多先生不甚爲旧文学,偶有所作亦不见佳。独“穷途捨命作诗人”一语,如江河行地,万古不废。苏曼殊“尙留微命作诗僧”,凄美处自是过之,惟不若闻一多说得解恨。
黄公度五古大篇以《梦中纪梦述寄梁任父》最称芳馨悱恻。“人言廿世纪,无復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怀刺久磨灭,惜哉我老矣。日去不可追,河清究难俟。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就中哀愤,何忍卒读。至夫“我惭嘉富洱,子慕玛志尼。与子平生愿,终难偿所期。何时睡君榻,同话梦境迷?卽今不识路,梦亦徒相思。”更有阆风高处,不胜凄凉寂寞之慨。
樊易之名并著于世,然易哭庵忒以伧俗。柳亚子谓:“樊易淫哇乱正声”,淫哇自是不妨,但无村气便好。
诗家而都无依傍者,上古惟灵均,中古惟渊明,近世厥惟曼殊。非必曼殊之才足可凌轹前贤,以其血统半爲日人,诗中纤美柔韧之处,华裔所不能到也。齐梁间诗什廼绮丽而非纤美。若冯小青辈则能纤美而不能柔韧。予每读《燕子龛诗》,至“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间鸣。我亦艰难多病日,那堪更听八云筝。”“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爲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此首陈独秀作)二绝,不觉大恸。终当爲情死者,孰谓独王长史哉!
潘仲昂《赠秉衡》有谓:“八载坤维绝,不祥咎佳兵;武人务暴气,政客竞纵横;爲富多不仁,苟苟与营营;儒雅久不作,末伎两间盈,製作斗淫巧,坚利尤所争,弹丸出原子,倾国与倾城,苍烟化顷刻,何辜蚩蚩氓,沃野数千里,百年不可耕;小道有可观,泥远博高名,驯至学典术,贻误尽苍生,圣人与大盗,翻成二难并。推原乱之渐,毋廼人心盲?喜怒与哀乐,张弛丧其贞,平居病瞑眩,无酒三分酲,感怀伤敏锐,触事心怦怦,狷者若春蚕,吐丝自缠萦,狂者如然脂,五内相煎烹,九州成大错,炙手一沸羹。”真须史学家之识见,科学家之逻辑,文学家之心灵,经学家之语言,方得成此制。
郁达夫《乱离杂诗》:“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此等语正可与定庵“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参看。天以百兇成一诗人,而诗人何尝有一语咎天耶?
今世小儿辈所爲文字,或有若千年艳尸,或眉宇间略无血色,皮囊虽具,生息不存。稍能工于感慨,卽恬以名家自居。哀乐恒过于人者,实未多觏。僞体而领一代风花,竟是谁之过欤?
吴雨僧宓勤于诗不辍,1935年中华书局版《吴宓诗集》已得诗991首,词25阕,则平生吟咏何虑数千。惟大率伤于质直,殊乏蕴藉,不然则平淡枯槁。吴宓自论其短,则谓“终未脱自身写照之范围”,之语最切其弊。
有不好诗而不得不爲诗者乎?苟得一,必爲纯粹之诗人。余独恨未及此辈同游。
顾羡季一代词宗,而《苦水诗存》多失之纤弱,盖词人之诗耳。李易安曰:“词别是一体。”此语至爲深刻。大抵诗词兼工者绝少,以词较宜于散文化之人生也。
胡适之于诗未尝依傍门户,浑是一派天真。《如梦令》:“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爲甚闭门深躲? ‘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不意《云谣集》外,尙得睹此构。
于右任伧父面目,廼竟以诗享名。以其人而崇其诗,吾独不服。
程砚秋《花事已开再寄叔通先生》:“松柏青青入眼同,好花不竞一时红。惊心尙有东篱菊,正在风霜苦战中。”于谐和中隐见锋芒。自来咏菊诗,率皆寄言隐逸,未若此篇独能得普罗米修斯之侠慨。俏丽之中,居然肃杀。
程颂云潜于诗专力汉魏,自标一帜,不知风骨在人心不在修辞。虽意态高古,终不能臻于茂郁清深。其于汉魏,亦所谓得其貌而遗其神者也。
概乎言之,诗人卽相信未来之种群。相信未来,却并不抱以希望。
诗人之天赋端在不调和。有超世之人,有顺世之人,有游世之人,此数者皆与诗道无缘。钱鍾书氏故游于世者。尝自序其集《槐聚诗存》云:“他年必有搜集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索隐,发爲弘文,则拙集于若辈冷淡生活,亦不无小补云尔。”此种嘴脸,最令人厌。及观其:“才竭祇堪耽佳句,绣盘错彩赌精工。”(《少陵自言性癖耽佳句,有触余怀、因作》)始信诗有别材,何关乎学哉!
吾国诗歌传统重自然而轻人文。山水玄言以降,性灵之作代盛其伦。惟性灵诗之本质爲乐府而非诗歌。吾国诗歌自屈子而终极审美风格粲然大备,廼厥后反停滞不前者,性灵传统难辞其咎。中间虽有少陵、昌黎、山谷、后山诸贤图振风骚之末绪,而势力单薄,终莫能挽此颓唐。有清诗坛稍见骨力,及定庵以其不世出之才龙见于野,风气始爲一开。迨鸦片战争惜败,性灵诗方走嚮终结。自然退隐,人文则必于焉凸现。试取道咸以来大家诸集细细摩味,故知予言之不谬也。予极言之则谓:天人合一者,诗歌现代化之大贼也。第方今学界巨擘,当不乐闻予此语。
夏承焘词貌丰腴而神旷达,的是一流词品。《浪淘沙·过七里泷》:“万象挂空明,秋欲三更。短篷摇梦过江城。可惜层楼无铁笛,负我诗成。 杯酒劝长庚,高咏谁听?当头河汉任纵横。一雁不飞鍾未动,祇有滩声。”援宋诗手段内诸倚声,效白石而都无踪迹可寻,殆非横绝千古之才而未可。余则更赞一辞,曰明于体象。
一流诗人抒写生命;二流诗人藻雪性情;三流诗人祇是构想、藻饰工夫。然衆庶之所重,世人之所誉,正在二三流间。
张伯驹词构想每能奇崛。《虞美人·本意》:“江东弟子歌中哭,已失秦家鹿。轻撞玉斗范增嗔,何不叫伊舞剑向鸿门。 红顔生死皆千古,怜被英雄误。汉王霸业几秋风,输与美人芳草属重瞳。”则不但构想绝佳,中有大悲悯、大关怀存焉。
“红学二昌”学行并迥不相侔。吴世昌才气汪洋恣肆,《词林新话》体大思精,足堪踵武《人间词话》、《驼庵诗话》而集成一代之议论;若周汝昌者,祇会说“奶奶兰心蕙性”耳。其赠女诗人尽心《鹧鸪天》词:“曾是红楼梦里人,偶来重阅物华新。精魂每验前生印,俊语时翻古句新。 称才女,赞佳文,江湖闺阁气纷纭。鬚眉浊物怜吾辈,那识通灵一性真!”年臻耄耋,犹以贾宝玉自命,虽嫌突兀,毕竟天性所鍾,莫可厚非;惟附注云:“西元1996年,廿四岁之尽心女士,如何能体会、深化、创造中华汉文韵语的情怀境界一至于此?良不可解。最好的解释是她带来了三生的经歷与造诣。除此以外,我都不信是真理。”(1999年1月7日《北京晚报》c第21版)则肉麻已甚。文人恶趣,莫此之尤。吴生大好男儿,廼与此“昌”齐名。
吴虞一生辟儒排孔,五四前后,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爲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诸文,攻击旧礼教、封建文化不遗余力。然《秋水集》中,多是宋儒口吻。《七律一首》:“诗书衰废八儒空,仁义多忧道已穷。人我两忘知物化,尘沙万劫竟谁工?昇平未必无差等,礼运何曾见大同!楷树凋零丝竹杳,萧条洙泗起悲风。”则知文化传统爲灵爲鬼,永难释脱。
刘季平《六朝松》:“惆怅梅庵去不归,庵前一树自斜晖。故家乔木关兴废,城郭人民有是非。几见淮流变清浅,分无花萼斗芳菲。重来不似旁人感,祇惜江头柳十围。”抚时感事,不尽英雄迟暮无聊之慨。尾联深沈中偏能骀荡,则其爲人之潇洒无碍可想。使柳亚子、陈去病辈爲之,不免沈滞太过。
康长素诗多系于写实,虚实之际,不能相生发;而构想平平,都无余致。予阅《万木草堂诗集》,惟觉其“说尽万千偈,漆灯明暗夜”(《爲某僧书扇》)隽永可诵。
诗人必爱慾炽盛、自我充盈之辈。此种禀赋纯由天授,岂学而能哉!然诗人不可学,而诗自可学。但当多诵经史,不须依傍古人门户。要知古人词采,亦自经史中来。
溥心畬诗祇是清雅而已,而词自大佳。彼以盛清王孙,暮年寄寓田横海岛,追怀胜迹、魂萦故国之情,咸託于倚声,每能动人心魄。《浪淘沙·夜》:“往事散如烟,锦瑟华年,三更风叶五更蝉。多少新愁无处寄,瘴雨蛮天。 高挂水晶帘,别恨频添,烛摇窗影不成圆。枕上片时归梦里,故国幽燕。”伤心具结,词采俊飞,方之后主亦未遑多让。至若《蝶恋花·望海》:“苍海茫茫天际远,北去中原,万里云遮断。云外片帆山一线,殊方莫望衡阳雁。 管弦天上春无限,板荡神州,龙去蓬莱浅。杨柳千条愁不绾,乾坤依旧冰轮满。”更觉自然深挚,哀婉低回。浑是发抒生命体验,都不假雕饰,亦不暇雕饰。
心畬但一开口,便是贵族气息。
赵瓯北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神州旷劫,至今数纪,何尝见诗家崛起?
鉴湖女侠诗常病在质胜于文,天才过于学力者大抵如此。纵多秀句,全篇罕足称者,古风尤不可竟读。虽然,其填膺侠慨、补天情怀,仍可激荡千古。“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日人石井君索和卽用原韵》)“楚囚相对无聊极,樽酒悲歌涕泪多。”(《感时》)“英雄身世飘零惯,惆怅龙泉夜夜鸣。”(《柬某君》)问道出此等语者男儿中亦多见耶?
刘光第咏怀五言,高洁芬芳,如公孙大娘舞剑器,妩媚中自蕴一股英气。《远心》:“远心无杂迹,随在得真还。阅世摩孤剑,围书坐万山。雪天生气出,人海寄身闲。愧少匡时略,梅花且闭关。”又《百感》:“百感愁交集,群生劫始过。压云龙气郁,迷月雁行讹。变相逃殷鉴,雄心误鲁戈。东方非野烧,神王天火多。”又《蕙沼》:“美人泣空谷,容华难久持。香草不见怀,憔悴薪刈之。灵根託幽绪,芳意结华池。凉薰度仁惠,微波扇离披。衰荣在靡常,人事同运期。愿纫君子佩,终朝奉光仪。苕年万自爱,勿爲霜露萎。霜露无时至,高节难变衰。”
“世界果然无作者,殷勤重爲拭青锋”(《己亥与章枚叔夜饮,卽送其之天津》),此夏穰卿之慷慨也。惟此公故多歷史忧惧感,终究“千古心期凭寸简,九州容易入斜曛”(《送汪毅白出都》)、“旧游歷歷归青史,秋雨沈沈入长年”(《戊戌中秋与西村白水、陈锦涛、洪复斋、蒋新斋、张养农、方楚青、蒋澍堂、常伯旂同饮天津酒楼,时余将南归,率呈一律》)来得本色。崇高之中,偏饶顽艳。予偶诵此二联,不自觉涕下如霰。
诗与史本泾渭二途,绝不相类。西哲亚里士多德以爲诗比歷史更严肃,更具哲学意味,最是不刊之论。畴昔孟轲始引《诗》与《春秋》相嬗爲用,已入歧途。近人林宰平氏廼復推允陈叔通之“以《春秋》治诗”,云“《春秋》可以断狱,叔通之诗则正如老吏之平亭是非,判定曲直。”(《百梅书屋诗存》序)大言欺世,曾谓堂堂中国竟无人哉?
陈叔通晚年书联明志,云:“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诗人蹉跎有至于此极者。叔通中年哀乐咸备,“同作夜游宁问主,自成岁例不因人”(《双汉罂斋赏梅拔可诗先成次韵奉和》),苏世之姿,居然可想。前后相较,真如隔世。
一切作品,必先具范式然后可以致经典。范式者,可资仿效之因素也。易哭庵、吴碧柳之才非不隽美,但纵才太过,而无范式耳。
定公诗:“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狂来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销。”“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设剑箫爲喻,揭破体象之密,于诗道庶几近之,然终稍嫌单薄。至若谭浏阳“禅心剑气相思骨,并作樊南一寸灰。”说尽诗奥,斯廼可谓至矣极矣,蔑以加矣。清刚妩媚之外,饶多执著深沈。
观堂论词数言境界,而罕言气象。惟于《忆秦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下评曰:“太白纯以气象胜。”大抵诗家气象一语,歷来说者都无言荃。岂大道之至,不落文字耶?余今则曰:气象者,诗人歷史感之客观化也。诗词而胜在气象,惟担荷歷史者爲能。
观堂自作《蝶恋花》“连岭云天知几尺,岭上秦关,关上元时阙。谁信京华城里客,独来绝塞看明月。 如此高寒眞欲绝,眼底青山,一半溶溶白。小立西风吹素帻,人间几度生华髮。”空寞孤抗,眞大学者气象,觉陈伯玉《登幽州台歌》面目亦嫌粗鲁。
有气象,有兴象。沈增植“依然圆满清光在,多事山河大地依。”(《中秋前二夕月色至佳忆甲午中秋京邸望月有诗今不能全忆矣》)气象也。“祇借柏庭收寂照,四更孤月瞰江楼。”(《偕石遗渡江》)兴象也。
寒柳堂《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爲怀抱”感题其后》一首最致沉痛:“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语虽平常,然至能惊心动魄。其所以然者,祇在“无可柰何”四字。
夫诗不于不可不爲之时呻吟而出,终无足称焉。棣之师所谓“一切文学经典都是有病呻吟”者也。柳亚子太熟于诗,直是用韵语説话,故吾先无取焉尔。
计八十一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