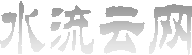诗美创造学
作者:毛 翰
第八章 诗的意象(下)
1、关于社会意象
如果问什么是诗的意象?中国人可能不假思索地回答,风花雪月、梅兰竹菊、绿水青山、黄莺紫燕等等便是。现代西方人也可能作出类似的回答,因为在他们那里,“整个自然是人类心灵的隐喻”(1)这样的命题也很流行。意象就是隐喻人类心灵的自然物象、自然景观,这回答当然没有错,只是还不完备,自然意象并不是诗歌意象的全部。“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声律启蒙》(2)开篇所罗列的这一连串意象就不全是自然意象。
除了自然意象,还有哪些别的意象呢?学界对此意见不一。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意象的内容,可将意象分为五类,除了自然的,还有社会生活的,人类自身的,人创造的,人虚构的。(3)
这种意见可能比较允当,上述《声律启蒙》开篇所列的意象就恰好为例:“云”、“雨”、“雪”、“风”、“晚照”、“晴空”、“来鸿”、“去雁”等属于自然意象,“途次早行之客”、“溪边晚钓之翁”属于社会意象,“两鬓”、“一蓑”属于人类自身的意象,“剑”、“弓”、“清暑殿”属于人创造的意象,“广寒宫”属于人虚构的意象。
不过,这样将意象一分为五,不免有些烦琐。为论述和运用的方便起见,意象的分类,可以考虑“二分法”,即简单地分为自然意象和社会意象。这样,我们不妨将有关“人类自身”的意象一般归于社会意象,如眼睛作为心灵的窗口,头发作为青春的旗帜,皱纹作为阅历和人生沧桑的见证,都与社会情怀有着天然的联系;将“人创造”和“人虚构”之物,如剑、弓、清暑殿、广寒宫,以及“人创造”和“人虚构”的故事,如大禹治水、嫦娥奔月,也一并归于社会意象。这样一分为二,简单明了,自然意象即物象,社会意象即事象。
社会意象,就是以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作为诗的意象,包括各种事物、人物和人类生活景象,以及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曲折反映的神仙鬼怪的生活景象。社会意象入诗,其作用与自然意象的作用大致相同,也在于抽象情思的具象化,使情思的表达含蓄蕴藉。上一章归纳的意象的五种作用,也都适合于社会意象。
2、社会意象的营造
社会意象即事象。营造事象,就需要叙事,就需要借助在传统诗学中与“比兴”手法相对的“赋”的手法。“比兴”就是拟物,就是营造自然意象。“赋”就是直陈其事(4),就是叙事。所谓“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5)“叙物”即“叙事”。叙事可以是客观地叙述故事,叙事本身就是目的;也可以是借叙事以抒怀,其所叙之事,只是作为寄意之象。例如,作为叙事的一种,“史诗”偏重于客观地叙述历史,“咏史诗”却只是将所咏之史作为事象,另寓情思。
社会意象和自然意象,在诗中的作用大致相同。人造之物作为诗的意象,与自然之物作为诗的意象,在诗人的感觉中,是没有多大区别的。试想,诗家咏物,咏自然之梅与咏人造之剑有什么不同?咏人工建造的亭台楼阁,与人虚构的天上宫阙,与大自然幻化的海市蜃楼,又有多少不同?甚至“人创造”的故事,与“大自然创造”的故事,作为诗的意象,其区别也是有限的。例如,唐人钱珝笔下的《未展芭蕉》:“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这就是大自然创造的一个故事。我们却不难把它改成一篇人类创造的故事,只要把“主人公”未展芭蕉,改成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就行了,“东风”就是那重色思倾国的汉皇,一切现成。
事物意象的营造
社会事物包括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科技、艺术、宗教、民俗、灾难、战争、体育等。其中每一项又可细分,如“生活”可分为饮食、婚恋、服饰、居住、旅行等,“艺术”可分为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文学等。诗人可以将这些事物作为意象运用于诗中,以寄托情怀。
低沉的长号,催动野谷和鸣
煨桑的香烟,招来一群苍鹰
静静地等待着,要扑上去吞噬
任剖尸人口衔腰刀
在羽毛上抹血,也不飞不惊
没有捶胸顿足的哭号
也不见对死亡的悚惧
鼓角声中喃喃地祷祝
仿佛是送亲友骑神鹰遨游
去采摘星斗,收获阳光,放牧白云
风萧萧,添几分壮烈
幡猎猎,飘缕缕肃穆
转经筒旋转的轨迹
划出生死界线的圆
多么坦荡、豁达的民族
不留遗骸,不塑雕像在人间
岩石般地来自大地
阳光似地去之空间
让人生的季节交替
任生死的花朵枯荣
从这块净地交出自己
从这月台上送别
坦然地走完各自的旅程
──白渔《天葬台》
这是以天葬这一民俗作为事象入诗。天葬,系我国藏族地区的丧葬习俗:人死后,遗体被送到天葬场,由天葬师将其割碎,投喂鹰、雕等飞禽,以期亡灵随之升天。诗人的动机,也许在于通过这奇异的葬仪,展示一个为虔诚的宗教信仰所浸透的民族,其开朗、旷达的性格,和迥然出尘的精神世界。而对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外界世俗社会,这雪域高原上的天葬情景,却无异于一个别有意谓的事象,会让我等尘俗之辈从中得到许多启迪。
人类依然好斗/当毒蛇猛兽海怪山魈甘拜下风/纷纷躲进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当百兽之王告别山林献媚人间/沦落为马戏团的小丑/茫然四顾/在古罗马斗技场的废墟上/孤独的人类/便只能以自己为对手
胸腔里奔腾着兽性的血/掌心里攥着莫名的仇/同类相残其乐无穷啊/如果没有机会亲赴沙场制敌于死命/或运筹帷幄/于股掌之间玩弄阴谋/百无聊赖的人们为之亢奋的/莫过于围观一场流氓斗殴
咫尺拳坛上/看拳王一身蛮勇两目凶光啸傲群雄/那真是过瘾啊/便是他手下败将皮开肉绽/在最后一秒钟爬起来作困兽之斗/也能煽起全场观众恶毒的热情/联想到情敌政敌同行冤家不共戴天/而狂呼加油加油
人心啊竟是如此丑陋/此刻夜莺之歌天鹅之舞都已黯然失色/神父的教诲天使的劝谕也置之脑后/全世界的绅士淑女名门政要三教九流/蜂拥赛场或一齐打开电视机/兴致勃勃地看这个文明社会/设置万金巨奖/甚至天网恢恢的法律也网开一面/声明致残致死决不追究/怂恿两个职业或业余的亡命之徒/赤膊上阵/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野蛮决斗
拳击是现代人热衷的野蛮运动,与人类文明的进程背道而驰,却堂而皇之地忝列奥运项目。拙作《拳击》以这一充满荒诞色彩的事物为意象,意在借题发挥,抨击人与人之间的无休止的斗争和倾轧,尤其是中国人的“窝里斗”,谴责人心的险恶,呼唤人类之爱。
人物意象的营造
作为意象入诗的人物,包括各种职业、各种性格的人物,现实人物、历史人物和虚构的人物。人物作为意象入诗,也在于抒发诗家情怀。
张乔就以累经沙场九死一生的退伍老兵的凄凉晚景,寄寓无尽的家国和人生之慨:
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
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
──[唐]张乔《河湟旧卒》
柳宗元政治失意贬逐南国,其一腔愤懑,则隐约透漏于渔家仙人般的孤高自在的意象中: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唐] 柳宗元《渔翁》
秦韬玉以待字闺中的平民女儿自喻,抒发一介寒士怀才不遇、久居人下为人驱使的哀怨和不平: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唐]秦韬玉《贫女》
在这几首人物诗中,《河湟旧卒》境界廓大,“独吹边曲向残阳”的意象况味无穷,《渔翁》略次之,而《贫女》境界格局较小,“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意象寓意明确。前者是象征性意象(征象),后者是比喻性意象(喻象)。二者相比,象征性意象更为诗家所推重。尽管比喻性意象亦不乏佳作。如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通过对新媳妇见公婆之前的惶惑不安的情状的描写,含蓄地表达自己临近科考的紧张心理,和希望得到举荐的急切愿望。曾任水部员外郎,世称张水部的张籍旋即有诗《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6),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以采菱姑娘秀外慧中歌喉出众,鼓励他应有信心。两首诗一问一答,在诗史上传为佳话。
那时间──
她拿棍子赶着小伙子走,
背过脸,
骂着她家大丫头:
“哪有女娃招后生?
十七大八不知羞……”
昨晚上──
她拿筷子戳着三闺女的头,
嘱咐着:
“抹抹嘴儿还不赶快走!
省得他,
在咱家门口儿干咳嗽……”
──张志民《倔老婆子》
新诗中,张志民(1926-1998)笔下这位农家妇女,她对先后两个恋爱中的女儿的一以贯之的训斥口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诗人意在通过这一人物意象,折射出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
表妹们总是很温柔很美丽的
穿月荷色布衫平底鞋梳好看的发式
表妹们月光一样走路
亲切得没有一点声音
表妹们最流行的装饰是线装书
古典诗和一枝腊梅花
天气暖和的时候
表妹们普遍瘦弱
表妹们走亲戚都有一种
寄人篱下的感觉
看见黑蝴蝶飞出小巧的檀香扇
表妹们要流好多好咸涩的泪水
心晴朗时表妹们很含蓄
表妹们笑不露齿
表妹们的偶像通常叫表哥
表哥在结尾一般都出家了或者
爱上另一个少女
使表妹们总要在最后的特写镜头里
大口大口往绣满情诗的素绢上
平平仄仄地呕一枚枚芳心……
很久很久以来,中国的表妹们
就是这样落寞地生长和凋谢
──詹永祥《表妹们》
表妹们的模特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林妹妹吧。林妹妹穿戴雅致,梳好看的发式,为悦己者容。捧一卷线装书是《西厢记》吗?林妹妹为莺莺的故事叹息。天生爱诗,偏好弄梅,怜香惜玉,多愁善感,林妹妹是病美人。蝴蝶自然是梁祝所化。要得俏,一身皂,黑蝴蝶是蝶中最俏者,是理想爱情的象征,可惜扑不到。林妹妹预感到红颜命薄故而潸然泪下。果然,林妹妹最后呕心沥血焚诗而终,使其悲剧人生出现一个凄恻动人的高潮。在诗人看来,林妹妹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事件,而是旧时中国女性的共同悲剧,所以诗题作“表妹们”,强调这个复数。诗句天籁流啭、柔媚从容,诉说千百年来封建礼教禁锢下的中国女性(以及男性,不然,表哥为什么出家呢)的忧伤哀怨,显得十分得体。而从纯技术的角度看,“表妹们”作为一个社会意象,人物意象,它在诗中与一个自然意象,如一枝病梅、一只孤鹭的作用大致相当。
天地是牢,日月如囚。
那个老狱卒说:我可以给你饭吃,
但我不能给你自由。
半个世纪黑也幽幽白也幽幽,
原来那“国”字
是王者之口──
金口玉牙威威然堂堂然疏而不漏,
是龙你盘着,盘得风凄血冷,
是虎你卧着,卧得皮老骨瘦。
风流倜傥的少将军,
转眼苍苍白了头……
终生幽之辱之而不杀之,
这东方式的虐杀专嚼好男儿的骨肉。
叫你天天滴血,
而无处喊冤,而无处呼痛,
无处用自己的手掷自己的头,
击穿三千铁栏,
砸碎王者的丑陋!
最可悲英雄难以英雄,
五尺宝剑嘶鸣,却不能自救。
一个人的命运,一个种族的命运,
必须依赖另一个人
活着或死去才能
结尾或开头!
这深刻的悲剧,该使我们
每一个心头流血,
每一根手指哭泣……
敲敲我们的额头,
敲敲我们的骨头,
为什么人的声音每每刚一出口,
便见血封喉?
牢是自身为牢,
囚是自身为囚。
──少帅老矣,尚能饭否?
身前一柄佩剑身后五百佛经,
谁能把世界拯救?
老人透澈如风站在众生之上,
他说:莫谈尘事。
这是王鸣久(1953~)笔下的《张学良•中国老人》。张学良这位特定的历史人物,一旦作为意象入诗,其寓意就超越了特定的历史环境,而具有普遍性了。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心境读去,自会读出不同的意味。
场面和情节意象的营造
叙事诗自不必说,抒情诗有时也需要有一个故事情节,至少是一个生活场面。场面是情节的基本单位,是某一时空中人物活动构成的生活画面。如果情节是一册连环画,场面则是其中的一页。场面和情节在诗中的作用也相当于意象,在于使诗的情思有所寄托,并使其艺术表现多姿多彩,曲尽其妙,避免构思的趋近趋同。试看我们熟悉的一些唐诗名篇: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早发白帝城》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崔护《题都城南庄》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杜牧《清明》
渭城客舍举酒,友人出关而去;轻舟顺江而下,逐客意外归来;人面桃花有约,奈何人非物是;欲寻酒家买醉,行人请示牧童……在这类抒情诗里,作为叙事成分的场面,是诗人情思的不可或缺的载体,也是诗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七事变后第二年,田间(1916-1985)鼓动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墙头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其中也有一个场面,一个让国人触目惊心,让国人无法忍辱偷生的场面,一个使诗获得感人的艺术力量而有别于标语口号的场面: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五十年代一枝独秀的闻捷(1923-1971)爱情诗,其《吐鲁番情歌》一组中,几乎每一首都有一个优美的情节,从而洋溢出动人的民族风情和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试看这首《种瓜姑娘》:
东湖瓜田百里长,/东湖瓜名扬全疆,/那里有个种瓜的姑娘,/姑娘的名字比瓜香。//枣尔汗眼珠像黑瓜籽,/枣尔汗脸蛋像红瓜瓤,/两根辫子长又长,/好像瓜蔓蔓拖地上。//年轻人走过她瓜田,/都央求她摘个瓜尝尝,/瓜子吐在手心上,/带回家种在心坎上……
某年某月,我有机会下渝州、过三峡,横穿中国。航程中,邂逅一缕缠绵。改《诗经•郑风》之《有女同车》旧题,作《有女同舟》:
是曾照过文君、昭君的那弯月吗/你的名字就是一首诗/月华穿过千年古意/忽又镀亮我金秋的梦旅
在甲板上,我猜你的身分/影星、模特儿、导游小姐/你都摇头/那你是从江心跃出的美人鱼吗/你笑了,对我吐露了你的秘密/包括芳龄和初恋的失意/感伤时你含泪的眼睛勇敢地/望着我,一个天涯浪子/也失态地对视着,半小时前/还素不相识的南国少女
江岸,延绵百里的奇峰绝壁/偶尔点缀着岩羊、农舍/云雾间的传说/总显得苍老而迷离
你说,我们唱歌好吗/于是你抱来厚厚的南国歌谣/一页一页,在船舱/让我沉醉于不知何方仙乡软语/多好哇,这只有一个听众的/独唱音乐会,多好哇/这峡江之行,一个凄美的逃逸/临别,你留下电话号码/提醒我,不要让一个女孩儿/消失在她那座多雾的城市
当船儿抵达终点码头/无奈的航程便化作一支旋律/那旋律憔悴在秋风中/是如此的娇弱无助/她自己还需要有人搀扶呢/人间的忧伤,她如何搀得起
其中的情节基本上是原原本本地取自生活,不曾作什么虚构,作者只是在叙述一个故事。诗成之后,我自己都为之惊讶,诗原来还可以有如此作法!待回到我习惯的作法,滤除原生态的生活情节,借助喻象,又得小诗一首,曰《凉州词》:
我那一首
平平仄仄的凉州词
填不进
你天籁般的小夜曲
九月
渐行渐远
江风
无怨无题
凤尾竹扫落
昨夜星辰
我沉重的韵脚依旧
跨不出唐人故居
清人吴乔有一段名言,说“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7)其实,酒也有不同的酿造方法,饭不变米形,酒也未必形质尽变。酒有米酒和白酒之分,诗有叙事诗和抒情诗之分。保留着米形,即保留着原样的生活场景和情节的,是米酒,是叙事诗;形质尽变的,是经过蒸馏,去除了米糟的白酒,去除了叙事成分的抒情诗。
场面、情节入诗,对于避免构思雷同,成就一首诗的独特审美价值,也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说《凉州词》的“词”、“曲”之喻可能与他人撞车,前方既可能有车挡道,后面也可能有车袭来,《有女同舟》的情节化则使之很难与人不约而同,挤到一条窄道上。
在另外一些时候,诗中的场面、情节可能不是从现实生活中采撷来的,而是虚构的,幻想的,只存在于虚拟世界、梦幻世界,只存在于与实数世界相对的虚数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对的影子世界。如晋人郭璞《游仙诗》(其二):
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
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
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
翘迹企颍阳,临河思洗耳。
阊阖西南来,潜波涣鳞起。
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
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
借仙界漫游餐霞饮露的瑰丽情节,表达蔑视权贵、绝意仕进、不屑于尘世功名利禄的超然与愤激情怀,虚拟的游仙情节成了诗人怀抱的极好寓所。
穆旦(1918-1977)的《神的变形》则可作为新诗运用虚拟情节的一个范例。类似于诗人四十年代的名作《森林之魅》和五十年代的名作《葬歌》,它以戏剧化手法,虚拟了四个角色:“神”、“魔”、“人”和“权力”。通过这四个角色的对话,明确地表达着一个对于今天的读者已不陌生,而在现代迷信的香火正旺的文革后期,则显得世人皆醉斯人独醒的石破天惊的主题:权力使神腐败,绝对的权力使神绝对腐败,神的腐败使神的统治失去了合法性,使得魔有机会和可能窥探神器,而魔掌握了神器之后难免又重蹈神的覆辙……诗中表达着忧国忧民的无限悲慨,表达着对人性的弱点,包括权力欲、独裁欲的透辟了解、无情鞭挞,和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思。此诗写于文革闹剧闭幕的1976年,也是诗人去世的前一年,也许几个月。“其鸣也哀”、“其言也善”的诗歌语言表达也一洗玄奥之风,给人以平淡、隽永,一派返朴归真、清纯如水而波澜不惊的感觉:
神
浩浩荡荡,我掌握历史的方向,
有始有终,我推动着巨轮前行;
我驱走了魔,世间全由我主宰,
人们天天到我的教堂来致敬。
我的真言已经化入日常生活,
我记得它曾引起多大的热情。
我不知度过多少胜利的时光,
可是如今,我的体系像有了病。
权力
我是病因。你对我的无限要求
就使你的全身生出无限的腐锈。
你贪得无厌,以为这样最安全,
却被我腐蚀得一天天更保守。
你原来是从无到有,力大无穷,
一天天的礼赞已经把你催眠。
岂不知那都是我给你的报酬?
面对你的任性,人心日渐变冷,
在那心窝里有了另一个要求。
魔
那是要求我。我在人心里滋长,
重新树立了和你崭新的对抗,
而且把正义,诚实,公正和热血
都从你那里拿出来做我的营养。
你击败的是什么?熄灭的火炬!
可是新燃的火炬握在我手上。
虽然我还受着你权威的压制,
但我已在你全身开辟了战场。
决斗吧,就要来了决斗的时刻,
万众将推我继承历史的方向。
呵,魔鬼,魔鬼,多丑陋的名称!
可是看吧,等我从地下升到天堂!
人
神在发出号召,让我们击败魔,
魔发出号召,让我们击败神祇;
我们既厌恶了神,也不信任魔,
我们该首先击败无限的权力!
这神魔之争在我们头上进行,
我们已经旁观了多少个世纪!
不,不是旁观,而是被迫卷进来,
怀着热望,像为了自身的利益。
打倒一阵,欢呼一阵,失望无穷,
总是绝对的权力得到了胜利!
神和魔都要绝对地统治世界,
而且都会把自己装扮得美丽。
心呵,心呵,你是这样容易受骗,
但现在,我们已看到一个真理。
魔
人呵,别顾你的真理,别犹疑!
只要看你们现在受谁的束缚!
我是在你们心里生长和培育,
我的形象可以任由你们塑造。
只要推翻了神的统治,请看吧:
我们之间的关系将异常谐和。
我是代表未来和你们的理想,
难道你们甘心忍受神的压迫?
人
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谁推翻了神,谁就进入天堂。
权力
而我,不见的幽灵,躲在他身后,
不管是神,是魔,是人,登上宝座,
我有各种幻术超过他的誓言,
以我的腐蚀剂伸入各个角落;
不管原来是多么美丽的形象,
最后……人已多少次体会了那苦果。
3、无意之象
物象入诗,其作用并不总是立象尽意的。有时候,诗人在诗中描绘客观景物,并不是为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而只在感叹自然造物的神奇,只是礼赞那景物本身的美。寄意之象,可能变成了“无意之象”;托物言志,可能变成了“玩物丧志”。事象入诗,也可能只是叙事而已,别无寄意。
得象忘意又何妨
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8)。意思是说,就像捕得了鱼儿就可以忘掉渔具一样,悟得了意蕴就可以忘掉语言。用以论诗,后人在“意”与“言”之间加入了一个中介──“象”。意、象、言,遂为诗之三要素。在纯意象诗中,诗人以言造象,以象寓意,语言是用来营造意象的,意象是用来寄寓情思的。因此,情思得以传达了,就不妨忘掉意象;意象得以营造了,即不妨忘掉语言。“得意忘象”、“得象忘言”遂成为前人津津乐道的诗歌创作及鉴赏中的一种至境。(9)
但是,在诗歌创作和鉴赏中,也不必总是“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譬如,有时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得象忘意”呢?当诗人手植一组意象,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意象鲜活灵动,明丽可人,此中依稀有真意,但那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那旨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10)
,读者又何必冥思苦想,上下求索,务求条分缕析,“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呢?诗无达诂时,诗其实也无须达诂,见仁见智时,但得诗美,又何须拷问仁乎智乎?甚至连“知人论世”的功夫也不妨省去,颂其诗,醉其象,不知其人,不知其意,也没有什么不可的。听人讲围棋,说某个图形很好看,但得图形赏心悦目,又何必锱铢计较,细辨其战术意图?当然,这是一种很高的弈境,前提是弈者和观弈者都具有很高的棋艺修养。
所谓得鱼而忘筌,乃是一种唯目的论的思维方式。只要目的达到了,便可忘掉一切为达目的所曾经运用的手段和经历的过程。只要得到了鱼,那为得鱼所曾经使用过的渔具及捕鱼过程都可遗而忘之。其实,手段(及过程)与目的,未必只有这一种关系模式。在某些时候,我们可能更看重那工艺品般的造型精美的渔具,和捕鱼、垂钓的充满乐趣的过程,而并不在意最终获得了多少鱼儿──不是“得鱼而忘筌”,而是“得筌而忘鱼”。超然于功利目的的人们,如姜太公,是不会为几条上钩的鲜鱼而忘乎所以的。七月七日鹊桥幽会,也并不是为了孕育一个小牛郎。
诗的意象经营,并不总是为了传情达意。目的淡化之后,手段(及过程)本身就成了目的,诗家便不妨“得象而忘意”。
自然意象的非意象化
物象入诗,大致有两种情形:
一、旨在立象尽意。此时,状写客观景物的目的,在于表现主观情怀,让主观情怀有所寄托、有所附丽。意象设置是为情设景,为意置象。诗人的兴奋点在于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以象寓意。
二、写景状物而已。此时,状写客观景物的目的,在于再现自然美,呈示景物自在的审美价值。对其中可能具有的隐喻意味,则漫不经心。其诗给人的印象是,得象忘意,玩物丧志。
在中国诗史上,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一路,一直被认为是诗之正宗
,受到推崇,而玩物丧志、得象忘意之作的存在价值则受到质疑。“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11)诗歌必须服务于政治教化,必须以美刺载道为旨归,持这种唯政治功利是图的实用主义诗观的白居易,更是否定“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式的写景状物之作,认为“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12)。王维式的山水诗,即便不被否认,也要强调其社会的、人生的隐喻意味。而在某些西方诗人看来,山水景物只是主观心灵的客观对应物,山水景物入诗更不能构成独立自足的、纯粹的存在。(13)
这当然是失之偏颇的。就像我们承认,偏重客观叙述历史的“史诗”与偏重主观评述历史的“咏史诗”,有着同样的存在价值一样,我们也应该承认,偏重描摹客观景物的、得象忘意的“物诗”(恕笔者生造),与偏重抒发主观情怀的、以象寓意的“咏物诗”,是有着同样的存在价值的。咏叹自然的诗篇,其中有无人生的或社会的寄托,并非判别其艺术品位高下的标准。强求寄托,实际上是否定诗对自然美的纯粹的摹写和咏叹。
这里有两点可以质疑:一、是不是所有的咏物写景诗都必须有寄托?无寄托者是否就没有存在价值?二、如果一定要有寄托,那么寄托什么?身世之感、君国之忧是寄托,政治讽喻、思想教化是寄托,而自然之怀、风物之恋,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种寄托?
如果说在王维《辋川集二十首》里,《文杏馆》“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是以山中悠悠白云化雨人间,隐约述说出世与入世的彷徨,那么《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只说山中芙蓉自开自落,又寄托什么呢?远离尘世的自鸣得意或寂寞难耐吗?
社会生活不必是诗人唯一的兴奋点,置身大自然物我两忘的咏物诗、写景诗,有时何妨纯而又纯,不刻意寄托“身世之感,君国之忧”呢?
古往今来,物象入诗,托物言志者众。从庚信《秋夜望单飞雁》:“失群寒雁声可怜,夜半单飞在月边。无奈人心复有忆,今暝将渠俱不眠。”以秋夜孤飞之雁,寄国破家亡、身世飘零之慨,到黄巢赋菊、陆游咏梅、于谦吟石灰以明志,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但没有寄寓“身世之感、君国之忧”,或寄意淡远,若有若无的咏物诗,也为数不少。例如,骆宾王七岁《咏鹅》,只在摹拟鹅的天真烂漫模样
。苏轼《海棠》(14)只在表现花的可爱和诗人爱花之痴:“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望庐山瀑布》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望天门山》
关于庐山瀑布,关于楚江天门,李白也只是摹写,只是惊叹自然山水之雄奇美妙,并没有关于人生或社会情怀的任何寄托。有人说,李白这些诗通过对祖国壮美山川的描绘,抒发了诗人的爱国之情。这似乎有些牵强。如果这香炉峰、天门山坐落在外国,诗仙于出游出访途中,惊呼“疑是银河落九天”,感叹“孤帆一片日边来”,又该是抒发了什么情怀呢?总不至于外国的瀑布就不能“飞流直下三千尺”,外国的峡江就没有“两岸青山相对出”吧?
纤细如一握楚腰/在杨柳风里/甩开葱绿的水袖/袅袅婷婷/舞出千古风流//二十四桥箫声/化作婉转的黄鹂/洒落一路清幽/五亭之下/引出多少明月/在碧波中漂浮//北海的白塔连夜飞来/依依不愿再走/隔江的金山涉水而过/分一片奇峰/在湖中淹留//最多情是水边垂柳/把绵绵幽思/写满荡漾的绿绸/是杜牧的诗/还是姜白石的词/谁能猜透
──黄河浪《瘦西湖》
昔日苏轼出守杭州,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即为千古绝唱,后人再度来游,往往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岂敢再轻以美女取喻?今人黄河浪(1941-
)此番知难而进,径取扬州瘦西湖之一“瘦”字,喻以雅好细腰的楚王国中那婷婷舞女,虽已神形毕肖,仍不免胆怯。乃再三调度艺术想象,以箫声月色勾连人间天上,白塔奇峰联络北国江南,垂柳绿波拂荡唐风宋韵,为壮声色,可谓用心良苦!而黄河浪此篇却也仅仅是礼赞自然山水别无寄托的。
诗画同理。曾经深受封建礼教禁锢的中国人,在人体艺术这个领域,总想划清,却总也划不清艺术与色情的界线。为此,有的美术理论家提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划分标准:表现人体的作品,有寓意的为艺术,无寓意的为色情。这显然又失之偏狭、武断,甚至还有伪道学之嫌。毕竟人体是一种美妙绝伦的造物,能用作意象另有寄托固然好,仅仅展示其自身的美,包括女性的娇柔之美和男性的阳刚之美,此外别无寄托,也绝不是什么大逆不道。有没有关于社会的或人生的寓意,有没有关于哲学的或宗教的寄兴,并不是判断一首诗以及一幅画、一支乐曲、一段舞蹈的艺术真伪和价值高下的标准。
“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15)
如果这里所说的言志是指托物言志,咏物是指“咏物而已”,这“余事”和“本意”也许可以三七开,二八开,一九开,但总不至于十零开吧。我当然也无意贬低诗的托物言志,主张诗都应该无所寄托。我只是认为,“托物言志”或“玩物丧志”,偏重寄托人生情怀社会忧思,或沉迷自然之美,礼赞自然造化,两种咏物诗可以并存。
近人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有云:“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究其实,他说的无寄托,还是有寄托,只是无明确寄托,以致“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而拙著这里标举的,是得象忘意、玩物丧志式的无寄托,是真正的无寄托。读这种无寄托的诗,则仁者不见其仁,智者不见其智,作者未尝然,读者何必然。
社会意象的非意象化
诗要表现的,是诗人的主观世界,和诗人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在主观世界一方,诗要表现的是情、理、美,即诗人对世界和人生的情感体验、思想颖悟以及审美感受。客观世界要求于诗的,则是状物和叙事,状自然之物,叙社会之事。其所状之物、所叙之事,可以作为意象,寄寓主观情思,也可以不作为意象,只是状物、叙事而已。
社会意象进入诗中,有时,它们的寄意可能会很淡,从中我们所能体会到的,只是淡淡的情怀,若有若无的思绪。或者说,社会事物、人物、场面和情节等,有时并不是作为寄托情怀的意象入诗的,诗人并不是希望通过对它们的吟咏,另抒情怀。它们本身就是吟咏的对象,而不是征象或喻象。它们已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时,一般作为社会意象的事物、人物、场景和情节,已经非意象化了,其诗也不再是“立象寓意”的抒情诗,而只是“口述故事”的叙事诗,“笔录史实”的史诗。
历代诗人以诗笔记录社会生活最多最成功的,大概莫过于杜甫,他的“三吏三别”等号称诗史。对于杜甫这样以史笔作诗,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太过泥实,缺少空灵蕴藉之美。有人声称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浪漫瑰丽诗风,对杜诗的“写实主义”敬而远之。然而,毕竟除了表现功能,诗还有再现功能;除了教化功能,诗还有认识功能。在孔老夫子那里,诗在兴观群怨之余,也还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功能。尽管后者可能是次要的,或者不是诗歌最为擅长的。即便是“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16),也不能否定甘居其下、无意寄兴的咏物和叙事之诗的存在意义。试看杜甫《近闻》并序:
永泰元年,郭子仪与回纥约,共击吐蕃。此年二月,吐蕃来朝,诗纪其事。
近闻犬戎远遁逃,牧马不敢侵临洮。
渭水逶迤白日尽,陇山萧瑟秋云高。
崆峒五原亦无事,北庭数有关中使。
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
仅仅是“诗纪其事”,纪事即其目的,纪事之余,别无它意。不管你喜欢与否,这是诗之一格。
张籍这首《江南曲》津津乐道于江南风土民俗,与之异曲同工:
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苎。
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
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
青莎覆城竹为屋,无井家家饮潮水。
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
娼楼两岸悬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
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
而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读其诗前之“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已经让我们心旌摇曳,不胜向往之至了,作为其主干部分的刻意抒情的诗,倒有点像是蛇足,一般读者甚至只知《桃花源记》,不知还有《桃花源诗》: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遗憾的是,这种“诗并记”的形式至今还被沿用着。往往是诗题之下,先讲一个见死不救或别的什么足以见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新闻或故事,引出诗兴,然后以分行文字大发感慨。作为读者,遇到这种作品,我通常是匆匆览过其“记”,决不再读其“诗”的,因为在知道其所记之事以后,我完全想象得出,它接下来要抒什么情,言什么理,感什么慨了。当然,写得好的除外,例如前述叶文福的《美学新论》。
---------------------------------------------------
注释:
(1)[美]爱默生语。
(2)[清]车万育作。
(3)金声《近十年文艺意象研究述评》,载《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
(4)[宋]朱熹《诗传纲领》:“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
(5)[宋]胡寅《与李叔易书》引李仲蒙语。
(6)朱庆馀为越州(今绍兴)人,故诗中出以“越女”。“镜心”一语双关,既为镜中,亦为越女采菱所至的镜湖(鉴湖)湖心。
(7)[清]吴乔《答万季野诗问》。
(8)《庄子•杂篇•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荃,同筌,捕鱼的工具。蹄,捕兔的工具,用以系兔足,故称。
(9)[三国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以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10)[清]叶燮《原诗》。
(11)[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12)[唐]白居易《与元九书》。从功利主义出发,《与元九书》甚至对李白、杜甫也多有否定:“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者……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
(13)参见陈本益《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中外抒情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我曾改其中两句为“白毛试绿水,红掌探清波”赠一少年文学报,这倒有所寄托了。
(15)[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16)[清]薛雪《一瓢诗话》。
来源 古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