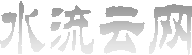木斋《苏东坡研究》
第四章-- 苏轼“豪放雅词”论
自从明人张綖(南湖)首创词有婉约、豪放两派之说,后之论词者,大多宗之。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豪放词的数量不能与婉约相匹俦。如认为“宋人论词,虽说有婉约、豪放两派,但我们衡量词史上的名家,究竟有多少可属于婉约派?有多少可属于豪放派呢?一般公认的比例数,大致是五比一。”(见郑骞《词曲的特质》)北宋豪放派一般仅承认苏轼一人,而苏轼的豪放词,按台湾王保珍先生所标举,为20余首(参见王保珍《东坡词研究》):“综观全部东坡词,其豪放之作,不过二十至二十五首之谱,比例不大。”也有论者认为苏轼词真正够得上是“豪放”词的,仅有“大江东去”一首而已,从而就在根本上否定了“豪放”词派的存在。
这种现象,说明对“豪放”词艺术特质、审美价值缺乏理论的、系统的认识。提出“豪放”、“婉约”之说的张南湖说得很笼统:“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二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然亦存乎其人。如少游多婉约,东坡多豪放。”(《古今词话》)“气象恢弘”四字,可说是论者对豪放词的直观感受,尚缺乏细致的分析。
总之,豪放、婉约之说统治了学术界长达数百年之久,笔者在前文中,提出苏词的本质是“雅词”,无疑是对传统的一次挑战,但仍有不足,譬如,豪放词与雅词之间的关系尚需论述。笔者在此章中试图将二者合一,提出“豪放雅词”的概念,因“雅词”问题在前文已经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此处主要从“豪放”的角度论之。
第一节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苏轼豪放词风的创立
当苏轼步入词坛之时,面对他的仍然是唐五代两个源头而来的两派词风:一是由民间词为源头的柳永的市井词,一是由文人词发展而来的晏欧词。两派词虽有不同,却又有共同之处,即相对以后出现的苏辛派词人而言,他们又都可以划入婉约的范畴,他们都以花间樽前为背景,都以表现男欢女爱、离情别绪为第一主题,并都具有阴柔婉约之美。只不过市井词低俗一些,浅露一些,文人词高雅一些,含蕴一些。而温庭筠等花间词派的宫体词,则更华贵一些、富丽一些。因此,此两派之间,可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苏轼词的出现,将使这两种词风由以异为主而变为以同为主。在苏轼关西大汉的顿足高歌里,在铜琶铁板的伴奏下,晏欧派与柳永派将不得不结为有矛盾的同盟,共同结为婉约的阵营,而成为新一派崛起力量的对立面。
苏轼最早的词作,按王文诰《苏诗总案》载, 为熙宁五年(1072)所作《浪淘沙》,词句尚为“绮陌香尘”、“槛内群芳”之类,可说是尚在学步欧晏。翌年所作的《行香子.过七里滩》,已堪与苏轼之诗名匹配,尤其是上下片之结句“过沙溪急, 霜溪冷,月溪明”,“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均令人有目不暇给之感。已可混入欧晏词集了。但仍未见苏轼之人格、性格、词格。后年所作的《虞美人. 有美堂赠述古》:“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堂庑渐大、登临渐高,使用了大字眼、大角度,使用了议论的句式。已可见苏轼豪放洒脱词风的苗头。
真正实现豪放词风创制的,是苏轼随后的知密州时期。其原因有三:首先是经过杭州时期词的创作,为其成熟的艺术作了准备;其次,是地理环境的改变,由小山小水、柔情妩媚的江南秀山丽水一变而为北方胶东那广袤的平野,从而提供了词人那“野性”骏马奔驰的空间;第三点,便是苏轼的性格、人格、文格使他必然地摆脱传统的羁绊,把他笔下的词作塑造成自我形象的写照,而不甘心于混同于他人。这就从根本上决定豪放词的出现。
这一转变,似乎是当词人在赴密的路上就得以实现的。试看其《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溥溥。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元遗山对此织很不以为然,认为“此篇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并指摘“当时共客”以下,“其鄙俚浅近,叫呼眩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其实,若仅从词风而论,还是很难推断此词非东坡所作。密州之前,东坡确无此类“鄙俚浅近、叫呼眩鬻”之作,而当东坡一旦离开江南那柔歌曼曲之地,北国的旷野、风土、豪放的情怀,铁琶铜板似的歌风,未尝不会使这位本来就超脱旷达的豪士为之一变。
此词特点有五:一是多用议论而非传统词作之具景细微的刻划。全词由“世路无穷”以下皆为议论,一气贯下,如此气势,舍东坡其谁也?二是由议论而产生了直露,而非传统词作的含蓄蕴籍。写景物而云“野店鸡号”,抒情怀而云“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此亦确非一般词人所敢写;三是多用典故,以补议论之空乏;四是用大字眼,如“千字”、“万卷”、“千端”等,铺大景致,如“云山摛锦”等;五是全词既有“孤馆灯青”一类景物所透露的惆怅感,又有“袖手何妨闲处看”的洒脱感,形成一种超旷豪逸的总体审美感受。此五者,皆后来“豪放词”之特质。此词作为坡公在词风转折时期之作,其意义在于对传统的某种破坏,而不在新风格之建立。因此,尽管艺术上有不成熟或太过之处,亦不足为怪。苏轼抵达密州之后的词风,基本上沿着上述特质加以发展,终于使豪放词风得以确立。
苏轼随后作了著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身在荒远的北国,思念家乡,梦会亡妻,这无疑是典型的婉约词题材,但一入东坡之手,便绝不似柳七、秦观之作。他将豪迈、洒脱的胸襟溶入令人九曲回肠的题材之中,而使人在“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些表面凄凉的意象之中,感受到某种超旷之美。词人写凄清悲凉,却绝不深入细腻地刻画,而是以“千里”、“十年”、“泪千行”及“明月夜、短松岗”这些大字眼、大景致、大画面来表现,从而化凄清而为苍凉,转婉约而为豪放。可以说,这是一首以“豪放”写“婉约”之作。是苏轼第一首艺术上获得空前成功的豪放、婉约结合之作。
在密州,苏轼创作了那首著名的描写出猎场面、气势如虹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推出了雄浑的第一首豪放词代表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词题一作《猎词》,傅藻《东坡纪年录》:“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苏轼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后果得雨,于是再往常山祭谢。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苏轼另有《祭常山回小猎》诗: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诗与词写同一题材,而艺术效果却不同,其间奥妙,颇值玩味。应该说,这首诗,还是写出了东坡应有的艺术水平。特别是对围猎场面的刻画,形象细腻,“点皂旗”、“出长围”、“跑空立”、“掠地飞”等也都极具动感。但还是不如词的气势、词的形象。此词是东坡的第一首艺术上获得空前成功并产生深远影响的纯豪放词。因此,可以说,从这首词之后,词的世界就打破“倚红偎翠”月牙板的一统天下。苏轼本人写完之后,也异常兴奋。他与友人作书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书》)
东坡此词,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豪放风格呢?约略可归纳如下几点:首先,如前文所述,所写出猎之题材,本身就不与十七八女郎、月牙板相为俦侣,而非东州壮士抵掌顿足高歌、吹笛击鼓为节不足以尽其长;其二,其中的主人公形象自然也非柔肠百曲之士,而是“聊发少年狂”的“老夫”、“亲射虎”的“孙郎”等;其三,以大字眼、大角度、大景致、大笔勾勒,而绝不精雕细刻。如“千骑卷平冈”视野开阔,充满动感,一个“千骑”夸张了阵容,一个“卷”字,使满纸皆为飞扬的尘土;其四,以典故增加豪放疏落中深稳不足的审美感受,如“牵黄”“擎苍”,以当年李斯之叹息不可得,反衬今日词人之自由豪迈;其五,以魏尚自比,有一种惆怅感,失意感,惆怅失意之中,又揉进超脱清旷,如“鬓微霜,又何妨”等。这些因素,不仅构成了此词豪放的总体审美的因素,而且奠定了豪放词的基本构成因素。
密州词的另一座高峰是作于熙宁九年中秋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可以说,此词通篇都是咏月。上片在咏月中蕴含人神之际、天地之间、以及人生道路的迷惘、探寻、追求与苦闷,下片在咏月中蕴含人人之间、兄弟之间,以及人的内在情感的哲理性的审美观照。
此词的艺术特质由几个方面构成:首先是境界阔大雄奇。上自汗漫天宫、琼楼玉宇,下自朱阁绮户、悲欢人间,无不海涵。其次是醉酒骋思、情思浪漫。醉酒是浪漫的催生剂,有了醉意,才有这似醉似醒的朦胧浪漫的境界,才有“明月几时有”的痴问,才有“把酒问青天”的痴举,才有“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痴想,至“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恐已醉深矣!月在当时,本不可登,词人却认真地提出是否登月的问题,月上是寒是温,当时本无可知晓,词人却认真地以其寒而怕登月。在这些如醉如梦、似幻似痴的醉词中,却蕴藏了多少人生哲理之妙趣。第三点,词人以大手笔、大字眼,写大境界,在结构上大开大阖,在情绪上大起大落。如下片先写“照无眠”、“何事长向别时圆”的离愁别恨,愁之深,恨也深,却以“此事古难全”一语解过,并以“千里共婵娟”写“但愿人长久”的期冀。正如王闿运所评:“‘人有’三句,大开大阖之笔,他人所不能。”(《湘绮楼词选》)第四点,是词人所表现出的洒脱旷达的情怀。
《水调歌头》之后,苏轼在密州时期还有几篇作品。先有一篇不太闻名的《何满子.湖州作,寄益守冯当世》:
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东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国初平。 莫负花溪纵赏,何妨药市微行。试问当垆人在否,空教是处闻名。唱着子渊新曲,应须分外含情。
此词以词的载体,抒写时事,抒发政治见解,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熙宁九年三月,官府因筑茂城与羌人引起大规模武装冲突。新任成都知府冯当世实行招抚政策,使边乱得以迅即平息。秋九月,身在密州的苏轼写作此词谈自己的见解。这是此词的大致背景。以词写时事,前无古人,无可依鉴,但苏轼却写得极为成功,比如起句:“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艺术地概括了事变过程。以“见说”和“旋闻”代领,极写其来之迅猛与平息之快捷。以“岷峨”、“江汉”其地代其事,避免了枯燥的叙述,而以“凄怆”代事变,以“澄清”代平定,注入人的主体感受,将词人的主体评价与客体之存在溶为一体。“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气势如虹,露坡翁本色。
“东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国初平”,以“东府最少”对“八国初平”,更见气势,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味道。下片用杜甫、卓文君、王褒等人典故,以古说今,并在典故中溶入情致,此正豪放词风之本色。总之,此词在苏轼密州词作中的位置不可忽视,如果排出四首杰作,此词可视为第四。
纵观东坡密州词作,自《泌园春.孤馆灯青》以下,共计19首,
其中以豪放为主要倾向者计14首,以婉约为主要倾向者为5 首。当然,14首豪放之作中,又可以分为纯豪放之作,豪放婉约结合之作,以豪放手法表现婉约传统题材,以婉约情致反衬豪放情怀等多种类别。从数量上看,密州词正如密州的北国平野一样,显示了与江南水乡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当然,苏轼在认识到自己开创了“自是一家”的词作新阶段之后,仍然时有婉约之作出现。它说明:有些场合、情景、题材只适合以婉约的风格来表现;有些场景,只有以婉约的手法来表现,才会使听者爱听,读者爱看。婉约词风作为词史上一种成功的存在,她已成为了难以取代的存在。
苏轼密州词从艺术上说,首先是题材范围的大突破。其中最明显的三个突破,一是《江城子》以词写出猎场面,二是《何满子》以词写时事,表现边防、治国策略问题;三是以《沁园春》为代表的词作,以议论抒发政治胸怀。以上三者,皆为词史上题材方面的重大突破。
在结构方面,密州词不再以细腻深曲见长,而是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在境界方面,形成豪放超逸、雄浑恢弘的新气象;在语言方面,不再是江南的小山小水,不再是“鬓云欲度香腮雪”,不再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而是北国的大漠长天,是大字眼构成的大画面;而描写手法方面,不仅不是津津于细腻的场景刻画与深曲的内心描摹,而是多使用直抒胸臆的议论;同时,为了弥补议论对传统含蓄美的破坏,又大量使用典故,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使历史化入今天,将情致溶入故实,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意象”构成方式;在总体审美效果方面,不再仅仅是“娱宾遣兴”的工具,也不再令人九曲回肠,凄凄惨惨,而是令人逸怀浩气,如觉“天风海雨逼人”。
有鉴于此,完全可以说,苏轼在密州时期,确已创立了“豪放”词的风格。
第二节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豪放雅词的审美特征
笔者认为,“豪放词”的概念,不足以涵盖苏词艺术的本质,因此,尝试将“雅词”与豪放词结合为一体,姑且称之为“豪放雅词”吧!下面,以前节涉及到的苏轼豪放词作品为基点,再结合苏轼以后的全部词作,似乎可对其“豪放雅词”作以下若干点的归纳:
一、无意不可入:题材的豪放雅格
苏轼“以诗为词”,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开拓了词的疆域。
词至苏东坡,不再仅仅是倚红偎翠、娱宾遣兴的工具,而是“天地万物,嘻笑怒骂”无不可入于笔端。譬如前节已论及的密州时期所写的《密州出猎》的威武雄壮的出猎题材;《何满子》以词写时事、表现边防、治国策略,有“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东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国初平”的气势如虹的佳句;《沁园春》“孤馆灯青”的政治抒怀之作;还有以后徐州时期写的一组《浣溪沙》,以词写乡野风光、田野生活,洗尽铅华、平朴自然,亦为脍炙人口之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日常生活小景寄予哲理之作等等,不胜枚举。苏轼不似范仲淹那样的偶然写过边塞,王安石那样的偶然有怀古抒怀,而是全面的突破,有意识的突破。这就具有了前人所不能并比的地位,并从整体构局上,形成了题材方面的豪放词风。使词成为了如同诗一样可以完美地表现自我各种情感的一种新兴的诗,因而获得后人好评。如刘熙载将东坡词与老杜诗并称:“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艺概》)其实,东坡词之豪放,更应与太白并提,但若单从“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角度,自是老杜更似之。刘辰翁亦评:“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指出苏轼以词表现出自己“倾荡磊落”的自我,从而达到了“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的艺术效果。
题材的开拓,正指示了由婉约而豪放,由“俗”而“雅”的方向。
二、以我观照万物:人物形象的豪放雅格
苏轼词中的主人公形象和角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就形象而言,苏轼之前的词作中,大多是柔肠百曲之士,千娇百媚之态。多为女性形象:花间及晏欧文人词一派多是上层女性形象,柳永笔下则多为沦落风尘的女性,而男主人公也多是“执手相看泪眼”的情郎。而在苏轼的豪放词作里,则或是“聊发少年狂”的“老夫”,“亲射虎”的“孙郎”,“欲乘风归去”的酒徒,“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豪杰等等。
不仅如此,从词人抒情的角度来看,苏轼更进一步把自我推向了词这一艺术舞台的前台。花间词人如同情窦未开的少女,隐在薄薄的幕帷里,显示着含蓄的少女魅力,柳永则如放荡的少妇,向你展示她美妙的胴体。故前贤说,花间妙在“不尽”,而柳永妙在“尽”,但他们“尽”也好,“不尽”也好,词人都如同导演一样,只在幕后;或如同高妙的皮影大师,在台底操作着他们的美人表演。而苏轼则既是导演,又是主人公,他把自己直接推向前台,特别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向世人坦露无遗。
从前文所举的四例来看,两例是词人自我,两例是以古人象征自我。还可以举出几十句表现自我的词句:
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 (《蝶恋花》)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永遇乐》)
我是世间闲客,此间行。 (《南歌子》)
但令人饱我愁无。 (《浣溪沙》)
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 (《水龙吟》)
不仅以我写我,以他人写我,还以天地万物写我。以“我”之目光观照万物,则万物莫不着我的性情。如“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寄参廖子》)。潮卷潮落, 本为自然,东坡眼中,皆因“情”字不同,因而会发出“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的痴想。这种景况,恰如词人所说:“无情流水多情客”(《劝金船》)是也。
三、使用醉酒的道具:摆去拘束以形成豪放雅格
苏轼在词中常常使用“醉酒”的道具,以使其中的人物能更潇洒、更超脱、更能摆脱人类社会的种种理性束缚。
当然,“酒”可使词作豪放,却不一定以酒入词就是豪放词。词本来就是酒宴歌席前的产物,但真正能达到上面所说的作用,还应说是始于苏轼。酒对人的作用、感觉应该说是大抵相似的,但不同的性格、思想的人,在与酒结合后,会产生不同的情怀。柳永之前,写酒之词,尚无名篇佳句,算来也只有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最为有名了。但酒醉使他幻思的却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境界。这自然是典型的婉约情境。再看他的一首以写酒为主要背景的词《御街行》(上片):
前时小饮春庭院。悔放笙歌散。归来中夜酒醺醺,惹起旧愁无限。虽看坠楼换马,争奈不是鸳鸯伴。
“酒”不但不能使他豪放,反而“惹起旧愁无限”,将其低俗的情怀推向了极致。
被视为苏轼豪放先声的范仲淹的《渔家傲》,也不过是“浊酒一杯家万里”,酒不过是解乡愁的工具,而“浊酒一杯”何其少也,“家万里”何其遥也!
柳永也好,范仲淹也好,都未能与酒结为一体,酒还不过是他们的身外之物,不能使他们超越人生社会来一个心灵的解放。而苏轼词中的酒,却使他的野性,摆脱羁绊,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几首著名的“豪放”词里,都有酒的魔力。“酒酣胸胆尚开张”才会有“鬓微霜,又何妨”,才会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放之举、豪放之词。须知,要让“老夫”摆脱种种传统的礼教羁绊,去发一发少年之狂,如同让一位老学究去跳“的士高”,这是何等的不易!
醉酒,真可说是苏轼词作里浪漫的催生剂,豪放上演的舞台道具。
还可例举许多,如: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
(《念奴娇.中秋》)
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
(《水调歌头》)
我欲醉眠芳草。
(《西江月》)
带酒衡山雨,和衣睡晚晴。
(《南歌子》)
夜阑对酒,依旧梦魂中。
(《乌夜啼》)
醉酒不仅使东坡摆去拘束,豪放不羁,而且酒后吐露真言,或者不如说是借酒遮面,来表达正常状态不便表达,甚至不能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譬如《临江仙》的结句,说他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引得州守大惊,以为“州失罪人”,但东坡已先有言:“夜饮东坡醒复醉”,醉后之言,自然就都可以不作数了。
四、以议论入词:表述方式的豪放雅格
传统的词作,以含蓄蕴藉为审美特征,以细腻深入的情景刻划为特征,以传统的意象为主要表达方式,很少直接抒情,更不用说直接发论了。而苏轼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自己的情感、观点和认识,更透脱地表现自我,就将他在诗文中
常用的“议论”引入到词中,从而成为“豪放雅词”的一个艺术特征。
如一曲《满庭芳》,便是全篇发论: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暮高张。江南好,千锺美酒,一曲满庭芳。
“议论”不过是一种表述方式,并不一定以“议论”入词就能写出豪放词。而是要看由谁发论,发什么情感色彩的“论”。易安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其实也是一种议论。“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同上)都是议论而非场景描写,但无疑是婉约之作,它们出自女性之口,写女性柔弱悲苦的内心,表现了一种阴柔之美。而苏轼的议论,却是大气磅礴,宏观鸟瞰,将世俗看得重似命根的名利说成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充满了苏轼特有的狂放野性:“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而在词史发展到后期时的一些词人,叫嚣怒骂,虽然豪放,却粗俗不堪。苏轼“以议论入词”,却达到了豪放与雅格的完美结合。
再看一曲《无愁可解》: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底。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著心里。你唤做展却眉头,便是达者,也则恐未。 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欢游,胜如名利。道即浑是错。不道如何即是。这里元无我与你。甚唤做物情之外。若须待醉了,方开解时。问无酒,怎生醉。
(案:此词选自王保珍著《东坡词研究》)
此词是以词阐述佛道禅理。“生来不识愁味。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底”便是禅宗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别样说法。结句“若须待醉了,方开解时。问无酒,怎生醉”阐述重在于心的解脱而不能倚托于物的哲理。
此外,还有许多,如: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临江仙. 送钱穆父》)
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十拍子》)
五、使事用典:语言构成的豪放雅格
苏轼之前,词中极少用事用典。宋代是个讲究学问,重视学问的时代。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是大学问家,但由于词“别是一家”,词人们都在维持着词的清纯少女的形象,保持着她含蓄蕴藉、要眇宜修的佳人气质,故只将学问典故倾注到诗文中去,写词时要放下学者的身份,只是言情写景。苏轼“以诗为词”,存心要破坏这个传统,他的学者面目也就自然地引入到词的创作中。这一点,已在前节“雅词论”中阐述,此处重在讨论用典与豪放风格之间的关系。
当然,以事典入词,并不一定可以成为豪放雅词,还要看在什么样的背景、情感下用典。以后的婉约派词人,从苏轼这里接受了用典的方法,进一步将婉约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譬如周邦彦、姜白石、吴文英等一派,形成典雅一派,而辛弃疾一派,则将苏轼尝试使用的使事用典推向极致,使典故成为构成豪放词的一个重要特色。
还是首先看看苏轼词的用典。
苏轼在词中用典,首先与前文所说的以“议论”入词有关。“议论”固然可以使词轻灵透脱,深入揭示内心深处的思想、观念,但同时也易于失去词作的含蓄之美、意象之美,流于枯燥乏味。使用典故,正可以平衡这种失重感,使意象成为议论中的形象论证,成为一种新的意象方式。如: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君堪惜。……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今古风流阮步兵,平生游宦爱东平。
(《定风波.送元素》)
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定风波.余昔与张子野……》)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江城子.密州出猎》)
闻道分司狂御史,紫云无路追寻。
(《乌夜啼.送李公恕》)
又如《满江红》:
忧喜相寻,风雨过、一江春绿。巫峡梦、至今空有,乱山屏簇。何似伯鸾携德耀,箪瓢未足清欢足。渐灿然、光彩照阶庭,生兰玉。
幽梦里,传心曲。肠断处,凭他续,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见周南歌汉广,天教夫子休乔木。便相将、左手抱琴书,云间宿。
有时候,苏轼以历史的事件,人物表达自己的心绪、思想、营造出豪放崇高的氛围。如《水调歌头》: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州。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著名的慢词长调《戚氏》,则是用远古的神话传说,营造了一种飘渺的仙境,也是一种以事典写词的方式:
玉龟山,东皇灵姥统群仙。绛阙岧峣,翠房深迥,倚霏烟。幽闲、志萧然,金城千里锁婵娟。当时穆满巡狩,翠华曾到海西边。风露明霁,鲸波极目,势浮舆盖方圆。正迢迢丽日,玄圃清寂,琼草芊绵。
争解绣勒香鞯。鸾辂驻跸,八马戏芝田。瑶池近、画楼隐隐,翠鸟翩翩。肆华筵,间作脆管鸣弦,宛若帝所钧天。稚颜皓齿,绿发方瞳,圆极恬淡高妍。
尽倒琼壶酒,献金鼎药,固大椿年。缥缈飞琼妙舞,命双成、奏曲醉留连。云璈韵响泻寒泉。浩歌畅饮,斜月低河汉。渐绮霞,天际红深浅。动归思,回首尘寰。烂熳游,玉辇东还。杏花风,数里响鸣鞭。望长安路,依稀柳色,翠点春妍。
此外,苏轼还发明了将前人的作品改成合于词调音律的词,这就是所谓“隐括”。这是使事用典的另一种方式。如《哨遍》隐括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应该说,苏轼以事典入词的使用比例,还不是很高,大约占全部词作的百分之八,其意义主要在于开创。它所留下的空间,要由后人辛稼轩辈加以经营扩张。
六、雄奇恢弘的境界:结构的豪放雅格
苏轼常以大字眼、大数字、大气概、大手笔来勾勒大场景、大境景,在结构上大开大阖,在情绪上大起大落等等。而这些方面的特点,又往往与前文所述的五个方面密切结合。
譬如一首《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起首就出之以阔大恢弘的远景:“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
按远景(落日)、近景(绣帘)、中景(亭下)、远景(水连空)的次序推出移去,构图层次有致,景深雄浑,定下全篇豪放的基调。这样,就容纳了以下“窗户”、“平山堂上”、“江南烟雨”、
“杳杳没孤鸿”等由近及远的一系列景物;从色彩来看,有“落日”的余晖,有“青红”的艳丽,有“烟雨”的昏蒙深暗的底色,有“碧峰”、“白头翁”的点缀,可谓怡红快绿,忽明忽暗,配置奇特奔放;在数字上,以“一千顷”的无垠,反衬“一叶白头翁”的渺小,以“一点浩然气”与“千里快哉风”互衬等;此外,“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使用议论、典故入词,“堪笑”“刚道”等语,皆虎虎有霸气。
此外,如:
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
(《归朝欢. 和苏坚伯固》)
旌旆满江湖,诏发楼船万舳舻。……试问伏波三万语,何如?一斛明珠换绿珠。
(《南乡子》)
当然,最全面,最典型的例证要数东坡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是东坡豪放词之代表作。肯定东坡豪放者,以此称之,如《吹剑续录》所载,“有幕士善讴”者,称“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否定东坡豪放词者,亦不否定此词之豪放。如明俞爰:“其豪放亦止‘大江东去’一词。”( 《爰园词话》)。
此词题目为“赤壁怀古”,此四字为两个内容,一是地点,是空间;一是历史,是时间;前者写江山风物,后者写人物豪杰。上片词人紧紧围绕这两点,时合时分。
此词由江山而人物,由今日而历史,由历史至现实,结构上大开大阖,情绪上大起大落、豪放里潜孕着悲哀,清旷里深蕴着凝重,更兼之以词人善用大布景、大空间、大时间、大字眼,跌宕起伏,确乎非婉约秀山丽水、九曲回肠者可同日而语。
起句凭空发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说江水向东而去,本是寻常之事,自然之事,“江”冠以“大”,“东”缀以“去”,“大江东去”四字,遂将江水之浩荡气魄,一挥而出。此三句是江山人物合写。以无垠之空间,借大江之浪淘,推出无限之时间,使千古英雄人物登上舞台。而“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一句“故垒西边”就将那浩荡无垠的“大江”,定格在一个确定的经纬点上,也就是题目之“赤壁”;一个“故”字,又轻轻引示出题目的“怀古”。但苏轼元丰五年所在黄州之赤壁,到底不是历史之真赤壁,东坡自己也未必真相信此地为三国大败曹军之赤壁,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姑且信之吧!一个“人道是”三字,就巧妙地将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学家去考索吧!“三国”二字,传说陈无己见之, 提出“不必道‘三国’”,而东坡也采纳之,改为“当日”( 参见《艇斋诗话》)。但今本还是多用“三国”二字。这是因为“三国”比“当日”来得自然、真实、气势响亮,时间也表现得更准确。一般来说,第一感、第一稿总是要更真实、自然一些。陈无己可以“闭门觅句”,作江西诗派的一宗,却无法成为东坡一类的大文豪,由此也可见之一斑。此句承“千古风流人物”而来,将题“赤壁怀古”点足,下句则回到起句“大江东去”的境界,回过头描绘江山之壮伟:“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先将你的视野引入高空,极写乱石之高耸;再引领你倾听那惊涛拍岸的巨响,炫目于脚下卷起的千万堆浪雪!结句,词人与起首一句呼应,江人合一,总括上片:“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以“一时多少豪杰”结束上片,同时也就开了下片“怀古”抚今的具体内容。是上片的结束又是下片的开端,极妙!
下片具体写“一时多少豪杰”的内容。将一幕幕历史画卷推上了银幕、推上了舞台。“遥想”两字,统领直至“灰飞烟灭”,贯注而下,一气呵成。对于周公瑾的描绘,词人写出了并列的一组意象,每个意象之间,都有着不同的审美风范:“小乔初嫁了”,写公瑾而先写小乔,有烘云托月之妙,并与下面“雄姿英发”的阳刚之美相反相成,阴柔与阳刚,女性之美与英雄伟业组合得完美无间。而“小乔”之韵事,又引人多少遐思,西方荷马史诗中描写了海伦引发的战争,小乔在赤壁之战中,至少在《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第三个意象:“羽扇纶巾”写服饰,“谈笑间”,这是写意态,写儒将风度,“樯橹”句写英雄之伟业。这一形象,自从谢安之后,尤其是李白的一再推许之后,“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就成为了士大夫所倾慕的儒将形象。
然而,无论是如画的江山,还是名载千古的英雄伟业,都无法摆脱词人此时此刻的灰暗心理。此时,苏东坡乃是乌台诗案后死里逃生“魂如汤火命如鸡”的贬谪黄州的要犯。江山的雄伟,与古代的英雄,恰恰使自己感受到自己“奋厉有天下志”的雄心报负的破灭。所以,才会有“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和“人生如梦”的哀叹。东坡元丰二年(1079)遭诗案,至此47岁,早已白发满头。有人曾惋惜东坡这首词的“灰暗的尾巴”,其实,如果没有这个“灰暗的尾巴”,“大江东去”也就不成其为“大江东去”,苏东坡也将不成其为苏东坡!“与其相似而伪,无宁相异而真。”唯其如此,才是封建社会后期黑暗里的真实的苏东坡,也因此才成其千古绝唱!
七、旷达的人生哲理:豪放雅格的根基
在如上文对“人生如梦”的分析中,不难引发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即苏词中所带有的苏轼独特的人生态度,或超脱、或潇洒、或灰暗、或高扬,从而构成豪放的因素。有些学者将这类词纳入另册,名之“清旷”,或“超旷”、“旷达”等。
此方面的代表作当推那首“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之作,试看全词: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贬谪黄州已然两年,从“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的痛苦心境中也已逐渐解脱了,他要买田以终老于黄州:“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稻田以充〖粥耳”(《书买田事》)。这年三月七日,苏轼到黄州30里外的沙湖去买田,归来途中遇雨,时雨具已先被拿走,同行之人举步艰难、十分狼狈、而苏东坡却坦然信步、吟啸徐行,并作了这首著名的《定风波》词。
西方的哲学家、美学家把山水草木看作是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认为在可见的事物与不可见的精神之间有彼此契合的关系。苏东坡此作,颇有一点儿象征主义的味道。它表面上是写这次雨中、雨后的感受,实际上却处处是人生态度哲理性的象征。
从词序所述情况来看,东坡此次所遇之雨,来势不小,然而,词人一起首就以十分藐视的笔调叙及:“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场席天卷地的风雨,被词人“穿林打叶”四字轻轻带过,更兼以“莫听”、“何妨”分别引领,更给人以意态潇洒、悠然信步之感。——这是在沙湖道中的漫步,也是坎坷的人生旅程中的漫游。
这种象征意味在以下几句中,进一步得到深化:“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手拄竹杖,脚穿草鞋,这自然是沙湖道中遇雨的苏轼形象,同时,它也是惨遭诗案恶运流放黄州一隅的词人自画像。然而,胸怀坦荡、任天而动的苏东坡并不以此为悲,他认为,“竹杖芒鞋”比达官贵人的骏马还要轻快自如。“谁怕”二字,既是对眼前风雨的藐视,又是对人生厄运的断喝!而“一蓑烟雨任平生”则更为精采,它一下子就把眼前之实境描写放扩为整体人生态度的光辉写照。它包蕴着不惧风雨、听任自然的生活原则,却又如此形象生动、富于诗意:烟雨迷茫中,走来了“竹杖芒鞋”、“吟啸徐行”的诗人,又渐渐消失在迷蒙的烟雨之中……
上片的实境着重写雨中,下片则写雨后并设想厄运之后再回首反思时的心态。“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料峭的春风伴着雨丝吹醒了诗人的醉意,他感到了几分冷意,突然,雨后天晴了,迎面而来的,是落日山前,一夕晚照。自然界的风雨阴晴进一步启示了他:任何风雨,都必将有其止息之时,那时,你再回首展望,当时咄咄逼人的风雨云烟,早已化为乌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在此之前,曾描绘过杭州望湖楼前的风雨变迁:“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机锋相似,只不过“也无风雨也无晴”, 较之望湖楼前的黑云白雨是更高一个层次的认识。前者是承认其“有”而相信其必将云散,后者则进入视而不见,不觉其有的禅宗式的顿悟。以后,苏轼晚年又有“苦雨终风也解晴”之句,当是此之余音。
八、“以诗为词”:形成豪放雅词
第八,苏轼豪放词既然在题材、结构、情调、形象、内涵诸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窠臼,也就必然引发对词的形式自身的革新。这方面,通常被学者们评为“以诗为词”。
典型的几条资料如:
陈师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而要非本色。”
(《后山词话》)
楼严:“东坡老人,故自灵气仙才,所作小词冲口而出,无穷清新,不独寓以诗人句法,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也。”
(《词林记事》)
叶庆炳:“苏轼对宋词发展的贡献,以诗为词,境界始大。”
(《中国文学史》)
李清照:“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不葺之诗耳。”
(《词论》)
以上论述,或褒或贬,大都是从总体评价,本文此处单举狭义的“以诗为词”。
首先,以“诗序”、“诗题”入词。前人多以词牌为题,不另立题、序。这是因为传统题材窄而似,自不必另立题目。而苏轼词的题材各种各样,特别是他的豪放词作。自然就出现了标“词序”、“词题”的现象,从而把词作置于特定的情景之中,使读者更易产生共鸣。此外,此举还成为提高词的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中进一步解脱出来的标志。以词牌代题,固然是“倚声填词”,声的位置已在于前,而另立词序为题,则表明对声的摆脱,重在表现于题目所规定的内容了。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人们首先关注的已不是“念奴娇”的乐曲,而是“赤壁怀古”的背景和内涵了。
其次,是在句法、字法、音律等方面冲破固有的形式,从而冲破音乐的束缚,逐使词成为宋代以来的一种新诗。
如:“何事长向别时圆”,这就很像一句七言诗,而不作:“向何事,别时长圆”等等。
又如毛稚黄评:
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
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
(王又华《古今词》引)
在“论调”与“论意”之间,苏轼认为“调”应服从“意”,形式应服从思想,因而不惜改调,不惜冒被认为不懂音律的危险。
陆游曾说:“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其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
晁以道是否因为是苏门弟子而为老师辩护,或云即便东坡会唱一曲古《阳关》,也不能说东坡就通晓音律。其实,东坡是否精通音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对词改革的勇气,从此奠定了苏轼词在词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席。东坡不懂音乐,关系不大,因为在他以后若干年,会有个精通音律的人,来开创一个新的词风时代。
何况,即便他懂乐律,他也不耐烦受此羁绊。如晁补之所评,说他“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
苏轼“以诗为词”,正是借鉴诗词的不同之处,以诗之雅改造词的“俗”的属性。这一点,请参见前文的论述。
最后,我们应谈谈苏轼豪放词的审美价值。本章开端处,笔者曾指出,豪放词自张南湖首论,引起后人众说纷纭。其实,苏轼本人不但首创豪放词,而且也颇自赏。除了给鲜于子俊的信外,他还在《答陈季常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东坡续集》卷五)对于“以诗为词”和“豪放”两个方面都分别加以标举,首先是评价友人的词作(实际上是借评友人词以自评)是“诗人之雄,非小词也”。可知苏轼并不以“以诗为词”为诟病,反而明确标举之,以期达到提高词的地位的作用。其次标举“豪放”,并以之作为极高的审美愉悦,特以“如此快活”四字给予高度评价。
其实,“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传统认识本来就有其局限,词与诗的这些特点,本来就是一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他们之间的区别本来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按照他们的分工,各自在自己的畛域驰进,只要合于艺术的规律,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就要开拓各自的疆土。诗、文之间可以借鉴杂交,文学与绘画、音乐等艺术之间也可以杂交,以提高各自品种的质量。为何独独不能允许诗与词这两个同属于广义的“诗”概念里的两个品种、样式互相借鉴呢?
从诗史发展的宏观角度鸟瞰,你会发现,词的种种特点并非平地而生的,她与中国古典诗歌产生初期的特质有着惊人的相似,特别是与未经近体诗格律化的《诗经》与《汉乐府》极为相似。她们都源于民歌,都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都以人类的第一歌唱主题爱情为主要咏唱对象,都以长短不齐的不整齐美为审美特征等等。这正说明了诗歌的内部矛盾运动已经走完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原始的诗歌艺术在经过数百年的文人们的反复琢磨之后,已经日臻于圆熟。当近体格律诗圆熟得不能再发展时,就从身体内部发出了要求破坏的要求,这就一方面产生了宋诗的革新,一方面出现了与原始艺术惊人相似的宋词。
因此,我们还可以说,宋词与《诗经》还有一点相似,他们都是一个时代、一个周期的开端。当然,她们又有极大的不同,她们是不同时代,不同周期的开端。前者是盘古开天,是在远古的洪荒中,开拓出的华夏民族的一方诗的圣土,是很遥远、很遥远,很古老、很古老祖先们一句句唱词的总集;而后者则是华夏民族已经开创了惊人文化财富之后一次休息整顿变革之后的新迈进,是在已经经历了、享受了种种繁荣富贵之后向原始自然的一次回归。然而,她又不可能舍弃那业已创造出来的一切有益的财富,她把几百年来逐渐形成的一切美的音律、节奏、声韵等等溶入了那近似原始自然的歌唱,成为了近体诗的女儿,成为了带有格律美的《诗经》、汉乐府。这就是词的诞生。
而当词在分娩之时,人类社会早已有了更严格的社会分工,歌唱成为了艺妓们专有的行业。词也就在艺妓的母体中伴着凄凄婉婉的恋情,在花丛酒樽间诞生。于是,短视的人们就习惯性地认为,词这个女婴,她也只配做一个艺妓,永远成为人们娱宾遣兴、博君一笑的工具,而忘记了她的远祖实际上也曾有过英雄伟业,也曾登堂入室而光耀史册。
时光一直等到十一世纪下半叶,才等到一位艺术眼光深远而又性格豪迈达观的人出现,在时代深藏的云涛海浪里,吼出了令人震惊的别是一番风味的歌。这就是苏轼豪放词的出现,也是苏轼豪放词在中国诗史上的座标。
对于这一点,苏轼本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与蔡景繁书》中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东坡续集》卷五)认为友人的词作(实际更多寓指自己的“以诗为词”的豪放之作),是“古人长短句诗也”,即是《诗经》、汉乐府一类的作品,这正是笔者此文长篇累牍之所论述,而东坡以一言蔽之之论。实在是要言不烦,抓住了本质。
所以,王灼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而胡寅则在《向子湮酒边词序》中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柳耄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确是经典之论。而诗人陆游以豪放之心胸接受东坡豪放词的雷雨冲涤,感受到“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历代诗余》引)则艺术地道出东坡豪放词的独特的审美意义。
来源:木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