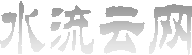木斋《苏东坡研究》
第五章 “天涯何处无芳草”
-- 略论苏轼的婉约雅词
苏轼词是立体的、多样的,既有“天风海雨逼人”的豪放,也有“树上柳绵”一类伤春萦怀的婉约佳作。豪放的苏东坡婉约起来,其委曲不在柳永之下。这方面前人有很多评价,如贺裳在《皱水轩词鉴》里说:“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然而《浣溪沙. 春闺》曰:‘彩索身轻常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 ’令十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张炎也早在《词源》中称道苏词“清丽舒徐,出人意表”的作品,认为后来的婉约大家“周、秦诸人所不能到”。
苏词中的婉约作品,前盖柳、晏,后掩周、秦,此评是否确当,姑且不论。再说说有更进一步持论者,舍苏之豪放而扬坡之婉约。如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此论粗看似创新,实则未能抓住本质。
苏词中的豪放和婉约,哪个方面更是本质?这首先要看其在词史的影响、地位。倘若苏轼没有豪放词,他在词史上的地位,可置身于晏、欧、柳、周、秦之间,是群星中的一颗,而苏轼有了豪放词,他就不再是众星的一颗,而是一条星河的发端,一座河系的座标、标志。尽管他可能被讥为“慧星”。
其次,要看苏轼创作两种词的本意。苏轼之所以在大力营造豪放的天风海雨之外,还要细心的经营柔媚旖旎的江南丝雨,这也许首先就由于大自然本身就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审美境界,而在词人的情感世界里,本身也存在着两种似矛盾又统一的感受。这是前提条件。其次,苏轼生活在柳词一统天下的时代,苏轼不可能完全脱离这种艺术的氛围。苏轼多次将自己词与“柳七”相比,并批评其弟子学柳七,虽然有着明显的敌意,但也正说明了柳词在他心中抹不去的痕迹──他把柳永,看得还是很重的。第三,苏轼创作婉约词,也是对世人对他譬如不讲音律、不懂婉约批评的一个回答。他在告诉世人:谁说我不能写婉约,我要婉约起来,比你更会婉约。只不过我心中有另一种情感要表达,有另一种境界要创造。但苏轼的婉约作品又实在好,以致于使一些后人忘记了其根本。
这样,苏轼的婉约作品,也就在婉约的历史里,有了她的一席之地。
譬如郑振铎所著《中国文学史》,有一段论述:
北宋的词坛,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柳永以前。这是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花间派与二主、冯延巳的影响,尚未能尽脱。真挚清隽是其特色,奔放的豪情却是他们所缺少的。 他们只会做花间式的短词,却不会做缠绵宛曲的慢调。 他们会写:“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莎行》);他们会写:“绿酒初尝人易醉, 一枕小窗浓睡”(晏殊 《清平乐》);他们会写:“山映斜阳天接水,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范仲淹《苏幕遮》)。 他们却不会写:“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沈沈楚天阔” (柳永《雨霖铃》)。 他们更不会写:“便携将佳丽,乘舆深入芳菲里,拨胡琴语,轻拢慢然总伶俐, 看紧约罗裙,急趣檀板,霓裳入破惊鸿起。正颦月临眉, 醉霞横脸,歌声悠!云际。任满头红雨落花飞,渐鳷鹊楼西玉蟾低,尚徘徊未尽欢意”(苏轼《哨遍》)。
苏轼的婉约词,是与柳永共同的创作,他们可以作为此时期的共同旗帜,而且,从“他们更不会写”的“更”字,可看出,苏轼的婉约,更深入、更委曲了,当然,苏轼的婉约词与柳永的婉约词也有质的不同,那就事苏、柳雅俗之间的不同,因此,也可以“婉约雅词”名之。
我们可以分析苏轼的几首婉约词作。
先看《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 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 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东坡在铜琶铁板,高歌“大江东去”之际,忽作一首《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缠绵悱恻,恐又胜柳屯田一头,令世人瞠目。━━据《苏轼文集》卷五《与章质夫》云:“《杨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故知此词作于东坡谪黄州元丰四五年期间。
此词确如东坡所云是“写其意”,即按章词原来的立意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特别是抓住原词以人写花、以花喻人的立意刻意发挥,如首句所云:“似花还似飞花”,故刘熙载评析:“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艺概》卷四)以下描述,均给人一种时而写花、时而写人,写花时又是写人,写人时又未离写花的不即不离之神境。清人黄苏评析:“首四句是写杨花形态,‘萦损’以下六句,是写望杨花之人之情绪。二阕用议论,情景交融,笔墨入化,有神无迹矣。”(《蓼园词选》)以下六句,既写望花人之情绪 ,又将此情移入杨花。而“梦随风万里, 寻郎去处”,一片杨花神魂。如明人沈际飞所评析:“读他文字,精灵尚在文字里面;坡老只见精灵,不见文字。”( 《草堂诗余正集》卷五)
此词写杨花飘落之情状与望花人的幽怨,其背后还隐着一个谪居黄州的坡老词人自我。其天涯沦落之感深寓其中矣!
如果说,《水龙吟》是章质夫给了苏轼一个展示婉约才华的机会,写在黄州初期的另一首《卜算子》,则可说是苏轼主动披露自己痛苦无依的内心世界。此一类词,没有向世人说明“婉约”之意,而纯是由于自己此时的心境当归之“婉约”,也唯以婉约出之,方能表达自己。
试析全词:
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贬至黄州,初寓居定慧院,五月时迁居临皋亭。故此词当作于该年二月至五月期间。王文诰《苏诗总案》将此词编于元丰五年十二月,误。定慧院,一作定惠院,在黄冈县东南。??
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七月在湖州任所被捕入京,八月入御史台狱。这一因写诗作文而致获罪之案,史称“乌台诗案”。当时,苏轼已然作好了身后的安排:“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予以事系御史台狱,……》);诗案之后,苏轼发配黄州,初到黄州,诗人仍惊魂未安:“醉里狂言醒可怕”( 《定慧院寓居月夜偶出》);“忧患已空犹梦怕”(《次韵前篇》) 。这首小词,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写出的。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词一起首,就是一种幽邃静谧的氛围,使人直觉有冷气袭人之感;月偏偏为“缺”,桐偏偏为“疏”,漏已“断”,“人初静”,这几个包蕴了诗人情感的意象组合,极写了幽冷凄清、孤独痛苦的心境。“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诗人又进一步揭示这种心境。 苏轼初到黄州时,多次自称“幽人”,如“幽人无事不出门,偶爱东风转良夜”(同前引文一)。“幽人”,自然有幽闭之色彩,如同其自称“罪人”,同时,也含有孤独清高的味道。词人发问:在此万籁俱寂之境,谁看见了“幽人”在缺月下独自徘徊?似乎是还另外有人,然而,却又无人,只有孤鸿缥缈的身影。也许,此时在夜空里,真有一只孤鸿;也许,这只孤鸿纯属词人臆想,在痛苦孤独的心境里,词人的身躯与灵魂幻化为了一只孤鸿。如果作前一种理解,则词人是主,孤鸿为宾;如作后种理解,则词人与孤鸿本来就是一体,主即是宾。
无论如何,词人在上片里还有分写了“幽人”与“孤鸿”,至下片,却只有了孤鸿:“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毫无疑问,这“孤鸿”即是“幽人”,即是诗人之自我,是诗人主观内心的外化。“惊起”二句,正是乌台诗案后词人痛苦孤独、徘徊忧思的形象写照;而“拣尽”二字,正是词人志高行洁、肝胆冰雪的表白;是词人对自己的过去因独立危行而不见容于世的反思;也是今后将一如既往、我行我素之人格的豪迈歌唱! 苏东坡生活于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开端,他的特殊的遭际,使他较早、较深地感受到了时代的黑暗,从而产生了这先觉者的孤独、哀伤,在这首词里,词人将这种感受艺术地化为了一只孤鸿的形象,它“惊”、它“恨”,却依然“非梧桐不止”(庄子语),宁肯寂寞于凄冷的沙洲。
以后,这只孤鸿又幻化为一只孤鹤,出现在赤壁夜空:“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是苏东坡梦见孤鸿、孤鹤,还是孤鸿、孤鹤化为东坡,诗人已不复分辨了。
这样一首佳作,惜哉!竟为后人作臆梦解。有人说是为王氏女作,如吴曾《能改斋漫录》持此说;也有人说是为温都监女作,如《野客丛书》记载了东坡在惠州的一段韵事:温家之女,年方十六、一见东坡,一往情深,后坡公渡海南行,此女竟卒,葬于沙侧,后坡公返回,因作此词云云;此外,也有人将此词坐实,如说:“缺月”是“刺明微”、“回头”是“爱君不忘也”等等(参见张惠言《词选》卷一)。这些,无疑都是“割裂形象、比附穿凿”。还是黄山谷的评价:“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乃能得其神境!
再看一首名作《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是一首伤春的词。上片写暮春景色:残红落尽,青杏初生,燕子飞舞,河水碧绿,春将归去。苏轼不愧文坛圣手;轻轻几笔,信手拈来,一幅清丽哀婉的图景便呈现于目前。“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更是缠绵悱恻。“柳绵”即柳絮,一年一度,柳絮纷飞,岁岁年年,人却不同,“吹又少”三字,包含多少人生感慨!青青的芳草已遍迹天涯, 预示着短暂而美好的春将要过去。韶光易逝,青春难再。关于此二句,《林下词谈》有这样的记载:“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 秋霜初降),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 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朝云为苏轼爱妾。苏轼一生坎坷,刚正不阿,一肚皮不合时宜,不论是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朝,他都不见容于统治者,屡遭贬谪,最后以60多岁的衰迈之身流放岭南,只有朝云随行。朝云唱此二句,深感其中之味,抑抑惆怅,情不自胜,不能竟之。不久,她便抱疾而亡,病重之时,仍诵此二句而不释口。苏轼遂终身不复听此词。
此词上片写景,是伤春人眼中之景,虽无一字言情,而其缠绵哀婉处自现。下片转而写人,写情。正被春愁困扰的行人,又为高墙之内的笑声所吸引,可惜只闻其声,不见佳人,但这也足以使那行人生出爱慕之情了。大概他已在心里勾勒出理想中的佳人形象了吧!真正不负“多情”二字。 可墙内佳人却全无知晓,舞罢秋千,翩然而去,“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位多情人只有独自伤心了。苏轼在此片,有意反复运用几个词语,使小词既有行云流水般的流畅,又有轻快的节奏,虽是写惆怅的心境,却无沉闷抑郁之感。尤其最后一句,道出多少人都曾有的微妙体验,极有理趣,因而广为流传。
苏轼虽身处逆境,有时不免见景伤情,但以他旷达的胸襟,并不会流于沉沦颓丧。王士祯说:“枝上柳绵,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花草蒙拾》) 此话虽是,但从整首词的格调来看,在哀婉之中, 还透着超然和幽默,并不沉重。朝云“泪满衣襟”是加上了她自己的人生体验,而后人常常将“天涯何处无芳草”作洒脱语,亦是为我所用。一首好词、一句好诗给人的联想和启迪,恐怕就是诗人自己也始难料及的。
苏轼以其旷世之才,开创了一代豪放词风,拓宽了词的境界,但豪放并不是他唯一的风格,他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爽之气,也不乏“似花还似非花”、“枝上柳绵”那样的婉约之情愫,但绝无婉约派中许多人的香软浓艳之气。从这首小词,我们就可看出他清新妩媚的别一风格。
来源:木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