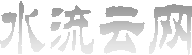木斋《苏东坡研究》
第八章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诗“尚理”论
在探讨了苏轼的“以议论为诗”之后,再来解决苏诗“尚理”的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鉴于长期以来,把诗和哲理一直视为难以相容的对立物,认为哲理会导致诗歌的抽象和枯燥的观点比较流行,我不妨从这一论题入手,陈述意见。
在西方,狄德罗曾说:“哲学思辨导致说教和枯燥的风格。”
(见Rene'Wellek的《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P50,原文是:The Philosophical spirit leads to a
sententious and dry style)在中国,也多有持此论者, 如严羽批评宋人之诗道:
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严羽明确指出“尚理”是“本朝人即宋人诗作的一个显著弱点,并且用以区别于唐诗的特征。在《诗辨.五》中, 严羽有名的格言是:
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虽然他随即就补充说道:“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但是,他的落脚点毕竟还是“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因为,诗的本质在他看来,是“情”而不是“理”:“诗者,吟咏情性也。 ”这样“理”就被视为“情性”的对立物而被排斥在诗歌艺术本质特征的大门之外了。
严羽“尚理”论的批评,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明人更进一步认为,阐发哲理是散文的专利,与诗无涉:“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李梦阳《空同集》五十一)更有甚者,则由此而全盘否定宋诗,认为“宋失之理趣”、“宋无诗”(前者为林志语;后者为李梦阳语:“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空同集》四十七)
很明显,宋诗“尚理”的问题,是中国诗史上的一个十分有探索意义的命题。通过解剖苏诗的“尚理”,对苏诗以致整个宋诗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都是极有裨益的。苏轼为什么要在诗中表现哲理?这种表现与情感、形象、议论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一些问题,则是本章所要着重解剖的内容。
研究一下宋代社会的特点,不仅对于“尚理”问题,而且对于下文所说的“以议论为诗”等问题都有密切关系。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围绕苏轼的“野性”初步披露了宋代社会的概貌,本节亦着重从“尚理”与时代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
总的说来,宋代是一个充满了论辩性的理性化的时代。这一特点,与宋代的危机性、宋人的衰落感有着直接的关联,与整个封建社会从宋代始,走向下坡路有关。宋代的危机,是由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各阶层的矛盾交织而成。这一矛盾的深刻性、超越了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它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
譬如从政治经济上说,宋朝虽然结束了晚唐五代的分裂混乱局面,统一了天下,但宋朝的领土比唐代要小,人口也比唐代少(仅有四千多万人,比唐之六千万少了三分之一)。宋朝开垦的土地,只有汉明帝时代的二分之一,隋炀帝时代的四分之一,唐明皇时代的三分之一。这就是说,土地耕种面积缩小了,可是,他们所征收的赋税收却大大增加了。北宋的征税比唐代重七倍。正象苏轼《鱼蛮子》诗中所说的:“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连立足的地方都要交税了)另一方面,农村的土地,大量地迅速地被大官僚地主所兼并,无地的农民日益增多,也像苏轼所说:“富者地日以益”而“贫者地日以削”,造成农民的大批逃亡,导致了斗争的日益尖锐化。就以宋仁宗这个宋朝的“鼎盛”时期 来说,农民武装起义在五年内就攻破了五十座州城,在此之后,则更加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高压和暴政削弱了宋朝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当然,还由于宋朝整个体制的关系)所以,又引起外族的入侵。当宋王朝刚刚诞生时,就已面临着契丹贵族和党项贵族的威胁,以后辽和西夏的侵扰使宋朝的实力更趋削弱,以致不得不“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资强虏”(苏轼《策略》)。积贫积弱的形势愈益显著。
从政治体制上看,宋太祖鉴于唐代藩镇割据和五代分裂局面的教训,演出了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杯酒释兵权”的一幕,从而达到了加强中央集权━━君权的统治。
在军事方面,赵匡胤提出了一个治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养兵。他认为遇到荒年有叛民不会有叛兵(因为士兵有供养,一般不会铤而走险)到了北宋鼎盛时期的宋仁宗时,光是直辖的“禁军”就有八十二万,再加上地方军队,共有二百多万。全国共四千多万人口,竟养着二百多万军队,这是非常惊人的。如果拿宋仁宗时代和宋朝初年相比,短短的六十年间,养兵就增加了四倍,这也是危机的表现。
宋廷不仅养兵以成“冗兵”,而且养士以成“冗官”。在宋朝,几乎只要读过书的,就一定能当进士。如果十次考不上,就送你一个进士,考到六十岁,还没考上,也送你一个进士,名曰“敬老”。唐时考一次只有二、三十个考中,而宋朝,一次考试竟有一千五百人中进士的,平时也都是三、四百人,比唐朝多十倍。进士一多,官就多了:当时全国共有二百个州,却有几千个州刺史,他们都是些光拿干薪不办事的官僚。全国只有十二个镇,却有八十多个节度使。养了大批的官,俸禄还格外优厚,当时一个官拿四种俸禄,除了油盐酱醋,每天还发酒,另外还发办公费。官僚可以直接从事土地剥削,一个县太爷有七顷地供他收租,宰相则有四十顷,称之为“职田”。不仅这样,官府还发仆人钱。大官僚可有仆人、丫环七十个。
“冗官冗兵”,无疑加重了宋的危机感。
处在这一危机四伏的时代,如何挽救宋朝以及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衰亡命运,就成为当时一切封建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们的中心议题。一些比较正直的封建士大夫也纷纷出来编制理论,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政策方案,并在内部进行着激烈的论争。远在北宋中前期,就出现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之同时,还有李【的“富国”、“强兵”、“安民”的进步主张。当仁宗“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封建专制制度在上述各种矛盾交错的结果下,发生了内外交困的空前危机。王朝内部的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更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诸如韩琦、富弼、欧阳修,一直到苏轼兄弟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富国强兵”的改革主张。在改革派的内部,也由于理论观点的不同,而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斗争,形成了北宋理性化的时代特点。诗歌作为言志、传情、表意的媒介,它自然要适应这种理性化朝代的要求,从而反映出诗人们对时代、社会、人生诸如此类问题的哲理性思考,这样,宋诗的“尚理”,也就成为了现实创作的必然。
哲理的时代,使苏诗必然地具有了“尚理”的特点。但这还不够,如果这些哲理诗违背了诗歌的本质特征,那末,即使它的产生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也仍然是难以生存的,因此,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探讨苏诗“尚理”的艺术特点。那么,苏诗中的哲理,是怎样与意象、情感溶为一体,从而使哲理诗符合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并且,这种含有哲理、情感的意象,又怎样与议论的方式结合,从而在辉煌的唐诗之后,另辟蹊径,重伐山林,树立了新旗帜呢?
苏诗中的精品,大多是哲理、情感、意象、议论这四个要素的结合体。其中哲理和情感,主要属于诗歌的思想内容范畴,意象和议论则主要属于诗歌的表达方式,应该说主要属于艺术的范畴。苏轼是用意象与议论结合的方式来表达深含情感的哲理。其中每两位因素都是对立的:议论是非意象的表达方式,哲理是情感的对立物。苏轼成功地把枯燥的哲理与动人的情趣结合,将抽象的议论和具体的意象结合,把似乎是不可能统一起来的因素,完美地统一了起来。这就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吧!
四者中,情感和意象是诗歌的最基本要素。情感是诗歌的最本质属性,意象是使情感形象化的最重要方式。哲理如果不与此二者结合,势必导致抽象和枯燥。魏晋的玄言诗,宋朝的道学诗,都是由于把诗歌单纯地视为阐述哲理的工具,由于既无情感又缺乏形象,故而“淡乎寡味”而走向失败的。
唐诗,是作为玄言诗和错彩缕金却乏“情”的六朝山水诗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因此,着重强调了情感的作用。“情景交融”是唐诗成功的不二法门。严羽总结了唐诗的成功经验,说“诗者,吟咏情性也”,这是不错的,但是,因此而得出“不涉理路”的结论,却是错误的。苏轼在情感中增扩了哲理,在意象中揉进了议论,证明了哲理不仅可以与情感相融,也完全可以借助意象的表达方式,促进情感、意象的深化。而议论与意象的结合,不但可以指引读者理解意象中深含的哲理,而且增加了意象的动感,开拓了新的意境,增扩了诗歌表“情”达“理”的功能。
苏轼是怎样将抽象的哲理与具体的意象结合起来的呢?可由以下几个方面论证:
第一节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寓哲理于意象,以意象象征哲理
先欣赏苏轼的一首诗: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
这是一幅绝美的泼墨山水画?不!它更象是具有动感画面的蒙太奇。诗人使用迅疾而来、飘忽而去的三个意象━━如同“翻墨”的“黑云”、如同“跳珠”的“白雨”、“卷地”而来的“风”,通过巧妙的剪接,拍摄成了色彩斑谰、寓意深刻的画面。
但是,这是一首哲理诗吗?全诗四句并没谈什么哲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描写了自然界雨前、雨中、雨后的景象。但是诗人为什么要摄取这样的三个意象组成画面呢?为什么要用雨后平静的水面去反衬雨前来势凶猛、不可一世的“黑云”、“白雨”呢?诗人为什么要揭示自然界这种变化无常而又有常的规律呢?
此诗作于熙宁五年的杭州通判任上,正是变法的风雷震撼着夜空之时。苏轼在写作此诗的前一年,曾经两次上书给神宗,提出了与王安石不同的政治见解。王安石姻亲谢景温弹劾苏轼“穷治无所得”,“既无以坐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抑其资,以为杭】”(《林希野史》)。对整个政治局势,苏轼感到“眼看时事力难任”(《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对于个人遭遇则感慨“敢向清时怨不容”(《和刘道原见寄》)。但是,无论是政治的暴风雨还是个人的坎坷,都必然是暂时的,必然要回复到澄清的本原上,这就是诗人在望湖楼前所受到的自然界的启发。“世事徐观去梦寐,人生不信长坎坷”(《送蔡冠卿知饶州》),诗人用三个意象构成的画面,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人生哲理。
再联系苏轼一贯的哲学思想和表达方式,也可以证明此点。如果说,乌台诗案前的苏轼,还是以儒家为主导地位,承认人生道路上的“黑云”、“白雨”为“有”而表示无所畏惧的话,诗案之后的苏轼,则是佛道为主导地位,认为人生风云为“无”而表示藐视的超脱,是“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晚年所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使用了与此诗相似的意象,但由于在前后文中伴有哲理性的议论,使读者更容易发现作者的用意: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月明星散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前四句的景色描写,决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色,而是深含作者情感和哲学思想的意境。这一景色,不仅仅是诗人渡海的具体环境,也是时代的象征,或说是诗人由具体环境而感受领悟到的对时代的理解。“欲三更”正是对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后期社会的概括,但是,诗人仍是达观的,诗人从自然界的变化感悟到对人生社会的认识。“苦雨终风”必将过去,是由于自然界(暗含社会)的本原是“澄清”的。这一点正是“九死南荒吾不恨”这种旷达思想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认识,全诗八句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苏轼寓哲理于意象,以意象象征哲理,意象和哲理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另一方面,二者却分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意象不仅仅是作为象征某种哲理而存在的象征物,而且是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画面;而哲理本身也不仅仅是作为物象象征的思想内容而存在,它使“意象”增加了灵魂,使肤浅的意象变得深刻。
在苏轼笔下,望湖楼前的雨景,本身就是色彩班谰、引人入胜的艺术化境,而“黑云”、“白雨”的意象由于具有黑暗象征的作用,因此,就更具有了令人涵咏不尽的意味。
由于诗人的思辨深含在意象的表象之中,因此,使意象所含有的哲理,具有了“不确定性”。它常使读者从同一个意象中,得出不同的哲理,甚至会超出作者创作的本意。诗人在看到自然界的“黑云”、“白雨”这些物象时,也许并没有将它们升华为某种象征物,而暴雨的过程,也许没有被升华为清晰的理念,诗人的“潜意识”使他朦胧地感到了自然界的风雨与人生风雨的某种相通之处。事实上,不把意象升华为理念,而是按照物象原来的形态摄入诗境,由诗中的意象来提供使读者深掘其哲理内涵的画面,这正使哲理诗符合了诗歌的本质特征。
这种现象,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做了形象的描绘:
我感到
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
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
象是有高度融合的东西
来自落日的余辉。
......一种动力,一种精神,推动
一切有思想的东西,一切思想的对象;
又穿过一切东西而运行。
(《丁登寺旁》)
第二节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理”在“意象”中
上文所说的特点,使苏轼意象中所深含的哲理,常常不易被发掘出来,以致人们一提到苏轼的哲理诗,总是那有限的几首,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理”在“意象”中吧!
事实上,由于苏轼兼诗人、哲人和政治家,宋代又是一个哲理的时代,更兼诗人特殊的遭际,使他从未停止过对社会、时代、人生等重大问题的哲理思考。加上苏轼“万物皆理”、“物我同一”的人生观,使他在观察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花一鸟,就无不具有了理性,甚至日常生活的一举手、一投足,走路、乘舟、饮酒、品茶、送行、春睡等,也往往带有了哲理思辨的性质。
下面,按其所借助的几类不同的意象,试识一下庐山真面。
首先是借助山水风景的意象。
例如著名的《百步洪.其一》, 一般都极赞其对百步洪险景连喻手法的运用: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
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全诗的整个前部分可以用一个“险”字来概括: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
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
......
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
险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
诗的后部分,作者忽然转而谈人生、社会的问题,进行佛理禅观式的思辨: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
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
谈论佛老的时空观,谈论如何使险恶的百步洪变成一泓溪水,那就是能超脱时空的限制:
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
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蒿眼如蜂窠。
但这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达到“无”,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境界:
但愿此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吾何。
(《苏轼诗集》P89)
《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后来南宗又加以发挥:“我此法门,以无住为本”,要人们忘却世间的善恶好丑。苏轼这里用的是此典。
此诗前部分描绘百步洪之险,后半部分集中谈如何对待人生与社会的险恶,从而使百步洪之险具有了人生、社会险恶的象征作用,使意象具有了哲理性。
有些山水意象所含有的哲理内容是极不明确的,如: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夜泛西湖五绝.其四》)
诗人取“月黑”才好“看湖光”这一充满理趣的现象,提供了可供读者深掘的哲理境界。
有些山水意象充满对社会的思考,充满对人生之谜的怅惘。譬如上面所引这组诗的另一首:
三更向阑月渐垂,欲落未落景物奇。
明朝人事谁料得,看到苍龙西没时。
诗人被“欲落未落”的月景所倾倒,但是,却不能忘怀尘世,想到变幻莫测的“明朝人事”,诗人痴迷怅惘,直至天明。对社会、人生深沉的思考,哲理性的思辨,尽在不言之中了。
诗人以哲人的目光审视大自然,于是,日月星辰、山河草木就无不具有了深刻的哲学内容。当它们被作为意象摄入诗中,也就含有了永久的哲理:我是谁?世界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由音乐与色彩底波澜吹送我们如一苇白帆在青山绿水中徐徐地前进,......它不独引导我们去发现哲理,而且令我们重新创造那首诗。
(参见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
试看: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答李公择.中秋月》)
浩瀚的银河成为宇宙总体化身,它无声地,却又是无可阻挡地推转着时光的运转。它推来了美好的一瞬,却又马上就要送走它。诗人多么希望能阻止住飞走的玉盘,使这一美好的时光永存。然而,银汉还是不声不响地、默默地推转着玉盘。唉!“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啊!一缕淡淡的人生哀伤从“清寒”的“暮云”中,从“银汉”的浩渺中,从“玉盘”的金轮中飘溢了出来。
再看《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明星稀”四字》一诗中的几句:
昨夜雨鸣渠,晓来风袭月。
......
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
......
相逢欲相问,已逐惊鸥没。
(《其一》)
我行本无事,孤舟任自横。
中流自偃仰,适与风相迎。
举杯属浩渺,乐此两无情。
(《其二》)
前首使人想起王维“隔水问樵夫”那种禅思境界,后篇则是“景”与“理”的合一。我们会感到分不清诗人是说实境中的“景”,还是说人生之“行”。这种情形有如西方批评家所说:
文学史上有时也会出现极其罕见的情形,那就是思想放出了光彩,人物和场景不仅代表了思想,而且真正体现了思想。在这种情形下,哲学与艺术确实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致性,形象变成了概念,概念变成了形象。
(韦洛克.沃伦《文学理论》)
苏轼还多借助“物”来抒发哲理。
如《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一诗,诗人劝慰锁在“筠笼”中的鸟儿安于笼中生活:这虽不如生活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但却可以免遭鹰隼的袭击而获得生命的最大自由。以此寄托诗人对于人生的某种哲理性认识:
终日锁筠笼,回头惜翠茸;
...
夜宿烟生浦,朝鸣日上峰。
故窠何足恋,鹰隼岂能容?
又如《僧惠勤初罢僧职》一诗,与上一首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曰:
轩轩青田鹤,郁郁在樊笼。
既为物所縻,遂与吾辈同。
今来始谢去,万事一笑空。
前一首陈诉“鹰隼”的胁迫,认为还是在笼中安全一些,此一首又说关在“樊笼”中,“为物所縻”,因而“郁郁”寡欢,一旦罢去职务,才感到轻松愉悦。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诗人对人生的认识。
此外,“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寄托了诗人坚韧斗争精神的人生观;《惠崇春江晚景》中“先知”“春江水暖”的“鸭”;《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中“势与落日争分驰”,“奋迅不受人间羁”,“意在万里谁知之”的“马”;《儋耳山》中“尽是补天余”的“道傍石”,无不以“物”象征了某种哲理。这种哲理与诗人的真实情感交融在一起,形成了感人又耐人深思的理趣境界。
苏轼是一位善于把目睹实见的事物通过奇妙联想以寄托情思的杰出诗人。他常常借助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出人意表地把他内心郁结的各种复杂感情化为可感的意象。进一步可以说,苏轼大部分“景”、“物”诗作,都是“景”、“物”、“情、“理”交融的艺术化境。
那么,“理”是什么呢?苏轼曾说:“物固有是理”(《答俞梏书》),又云:“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上曾丞相书》)可见,“理”是含在大自然客观物象之中的客观规律。诗人受大自然的“山石、竹木、水波、烟云”、“常理”的启发,感悟到人生、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是含在景物意象中的哲理了。
诗人没有把哲理从其所由来的“景”“物”中抽绎出来,做抽象的说教,而是与意象溶为一体。这就使哲理诗具备了诗歌的本质特点,从而与玄言诗、道学诗划清了界限;而其意象中由于含有了哲理,就使仅含“情”的“意象”相形见绌,从而对传统的山水田园诗和咏物诗做了重大发展。
再看苏轼借助日常生活意象的哲理诗。
如果说,以“景”、“物”象征哲理,苏轼还只是在前人基础上给予增扩的话,那么,借助日常生活的意象阐发哲理,则是苏轼的首创。
使用“意象”固然是中国诗歌传统的表达方式,但是,并非何种“物”都可以成为意象。日常生活场景,往往被视为卑俗而不能登诗之大雅之堂,使用日常生活场景抒发哲理,就更少见了。
由于这种传统的观念,遂使山水“景”、“物”的意象发展到唐代,就已臻于成熟、完备。苏轼能在其中增扩了“理”这一要素,已是难中见巧了。但是,苏轼并不满足在这一点上,而是要开拓更新领域,使用更新意象。
就苏轼的人生观念来说,绝不是超尘绝俗的求仙长生,绝不是“看破红尘”的“遁入空门”,也不是远离祭祀世俗生活的那种归隐。尽管这些观念多次萦绕在诗人心头,出现在诗人笔端,但是,苏轼已意识到“隐”、“遁”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也是同样不可能实现的。这就使他更瞩目于自然界和世俗的日常生活,并且将二者统一起来,将自然界的陶醉,溶入世俗生活的“烟火”,而世俗生活的内容中也包含了自然界的物象。二者共同构成了诗人战胜险恶环境、超脱旷达的“野性”生活方式。
因此,苏轼将平凡的日常生活铸入了深刻的哲理思辨。其中或溶进“景”,或借助“物”,或是单纯的生活意象。如著名的《东坡》诗: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诗人描述的是雨后夜中散步这样极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却深含了独立危行的人生态度。诗中用“市人行尽野人行”概括了自己的遭遇和遗世独立的伟大孤独感;用“荦确坡头路”的意象,象征了人生旅程的坎坷;用“自爱铿然曳杖声”表达超脱旷达、苦中得乐的人生观。
塑造鲜明的诗人自我形象,并使之成为深含哲理的意象,这是苏轼日常生活哲理诗的主要艺术特点之一。
看绍圣四年写于惠州的《纵笔》: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诗话载:章子厚见此诗,遂再贬苏轼至儋耳。此诗之所以如此有力地激怒了苏轼的政敌,正是由于它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活画了一位飘逸旷达的诗人自我形象,并蕴含着对权贵及其所造成的困苦境的蔑视。
比上一首稍晚些的《纵笔三首》,《其二》云:“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其一》云:“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也都是以轻快的笔调、平凡的生活画面、鲜明的诗人自我形象,抒发了诗人深沉的人生哲理。试想一位享遗世之伟名,被仁宗称之为“宰相之才”的诗人兼政治家,却在海南天隅的不毛之地,“闲数过人”,年华逝去,功业何成。而这些深沉的痛苦,却又通过“一笑”、“独立”等表情动作,化入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苏轼常常善于把世俗生活事件、名词升华为某种人生的哲理,从而描写出具有哲理意味的画面。如《白鹤山新居,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尽,乃得泉》一诗,记载凿井之艰难,本属日常生活事件,然而,诗人由凿井之难而联想到人生之难,从而使凿井过程的描绘,成为了“人间何处不巉岩”的哲理象征:
弥旬得寻丈,下有青石磐。
终日但迸火,何时见飞澜。
......
山石有时尽,我意殊未阑。
......
晨瓶得雪乳,暮饔停水端。
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
一勺亦天赐,曲肱有余欢。
(《苏轼诗集》P2217)
又如《慈湖夹阻风五首》,描绘出某种“归路茫然”、“柳暗花明”的人生境界: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其二》)
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
(《其三》)
在这种哲理意味的总体氛围中,有些词汇常常就具有了双重含义的性质,譬如“巉岩”在这里,就既有“慈湖夹”的“巉岩”,又成为人生道路的“巉岩”,既是实的,又是虚的,既是形象的,又是抽象的━━寓抽象于形象之中了。这种情况很多,又如《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一诗: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
所致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狂直”的内心与山水之乐关联,而山水之“道路”又反过来与“狂直”呼应,成为既是山水意义的“道路”,又是人生意义的“道路”。而“直造意所便”也同样是既此又彼,“似花还似非花”,既是诗人游乐山水的场景再现,又是诗人“野性”人生观念的表现。
从以上对作品的粗浅分析中,可以看到,苏轼大部分的哲理思辨,都是通过意象表达的。这些意象本身都是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自然或社会生活画面,而其中的哲理性又增加了画面的底蕴。这位双手摇曳着哲理之花的缪斯女郎比只提着一把浅见之草的感情女郎的青春魅力要强大得多,长久得多。这是苏轼哲理诗,对前代的哲理诗和传统的情景交融之作的根本性突破。
第三节 “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江西十八滩”
简议议论在其中的作用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苏轼将哲理与情感、意象紧密结合,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哲理诗。在诗歌的思想内涵上,比唐人发展、增扩了“理”(这里是就主流而言,并非说唐人没有哲理诗)。那么,在艺术构成方式上,是否仅仅简单地继承了唐人的意象呢?否!苏轼的意象是与议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以议论和意象紧密结合的方式,阐发具有情感的哲理。对于“以议论为诗”,上一章我们已经做过专论。现在,再从议论与哲理关系的角度,做一粗浅的探讨。
议论虽非哲理诗所特有,但由于苏轼哲理诗中使用了议论,从而提高了哲理诗传“情”达“理”的功能,提高了哲理诗的审美价值。这就显示了与唐人的不同的审美情趣。
首先,议论是沟通读者和作者的桥梁,是指引读者深入其哲理王国的航标。如上文所述,意象的表达方式固然具有形象性的特点,但如果纯用“意象”,读者就不容易把握作者的主体世界、作者的寄托。因为“意象”具有不确定性,使用直抒胸臆的议论,就可以使“意象”具有“确定性”,使之成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因此,可以说,如果是因为“只缘理在意象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话,分析其议论,则是认识“庐山真面目”的主要途径。
譬如前文所析诸例大多如是。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如果没有“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议论,就很难探讨“参横斗转欲三更”等意象的哲理意味;《百步洪》一诗,如果没有“我生乘化日夜逝”等议论,也很难深掘出“百步洪”险境描写的哲理内涵。
其次,议论有时也可以不借助意象,独立地作为表“情”达“理”的艺术方式。如《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声也》一诗:
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
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如果说,有“意象”的话,也是一种十分概括的意象,从通体来看,基本是议论性的句式,但却十分有名气。此外象《琴诗》等都是如此。我们还可以例举出许多直接以议论谈禅说理的佳篇:
书生若信书,世事仍臆度。
不量力所负,轻出千钧诺。
当时一快意,事过有馀非。
不知几州铁,铸此一大错。
我生涉忧患,常恐长罪恶。
静观殊可喜,脚浅犹容却。
......
(《赠钱道人》)
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
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
默归毋多谈,此理要观熟。
(《安国寺浴》)
这是诗人在屡次遭到打击、贬谪,“致君尧舜”、兼济天下的理想一再破灭后,经过对人生、社会哲理性的思考和认识,所形成的禅宗顿悟式的歌。由于这些诗不是无病呻吟,而是诗人忧患生涯的哲理性认识,因此深警动人。又如在南谪途中经过曹溪南华寺的吟唱: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
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
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
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
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南华寺》见《苏轼诗集》P2060)
在南华寺这一禅宗圣地,诗人重新认识了自我:“我本修行人”,而在尘世中的一切有为之作和坎坷遭际,都是“中间一念失”,是一念之失,是历史的误会。全篇用六祖慧能事迹,化用《坛经》之典,娓娓叙说议论出来,层层深入地揭示了诗人内心的大千世界。
有些直接议论的哲理诗,具有高度凝炼的艺术概括力。比如《冷斋夜话》所记载的,东坡“复官归自海南监玉局观,作偈戏答僧曰”:
恶业相缠卅八年,常行八棒十三禅。
却着衲衣归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衲衣”即纳衣,佛家亦云粪扫衣,意谓为人弃之不顾之贱物,我则缝纳为法衣。东坡自岭南归来,仍着法衣,意在进一步强调其“我本修行人”的人生认识。“五通”:其一为天眼通,为色界四大听造之清净眼根,色界及欲界六道中之诸物,无论远近粗细,无一不照;其二为天耳通,为色界四大所造之消净耳根,能闻一切声音;其三为他心通,得知他人一切之心;其四为宿命通,得知自心之宿世事者;其五如意通,又名神境通、神足通。苏轼所谓“自疑身是五通仙”,等于是说:他仿佛在空门里得到了真正的解脱和自由。这种精神境界终于使他度过了几十年间恶业相缠的苦海。(参见魏启鹏《苏诗禅味八题》,载《东坡讲座丛书》)
苏轼还有许多这类的禅偈诗流传于小说笔记之中。如《冷斋夜话》载:
东坡自海南还,至赣上,以水涸,舟不可行,逗留月余。时过一僧舍浴。其长老魁梧,如世所画慈恩然,
丛林不以道学称之。东坡作偈戏之曰:“居士无尘堪洗涤,道人有句借宣扬。举头但见蝇钻纸,抚背时闻佛放光。偏界难藏真薄相,一丝不挂但逢场。却须更说圆通偈,千眼熏笼是法王。”又尝与刘器之同参玉板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板,欣然从之。至帘泉,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何名?曰:“名玉板。此老僧善说法,要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方悟其戏。东坡作偈曰:“丛林真百丈,法嗣有横枝。不怕石头路,来参玉板师。聊凭柏树子,与问箨龙儿。瓦砾犹能说,此君那不知。”
这两首哲理诗,尤其是后一首,更为幽默诙谐,用庄子“道在瓦砾”及《传灯录》“僧问如何是佛,文殊答:墙壁瓦砾而犹能说之”的典故,阐述了佛法就在你脚下,翠竹碧笋,墙壁瓦砾都无不有佛法在的哲学思想。这正是临济宗义玄所论:“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随处作,立处皆真”的诗化。
又如《独醒杂志》所载的:
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
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江西十八滩。
更是理趣盎然、诗意浓郁的优秀作品。还有《宋裨类钞》所载的作为东坡一生总结性质的哲理诗,那首题自己照容,所作之偈: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更是纯以议论而名闻天下的充满老庄禅悦意味的哲理诗。
此外,如《书焦山纶长老壁》一诗:
法师住焦山,而实未尝住。
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
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
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履。
譬如长须人,不以长为苦。
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
归来被上下,一夜无著处。
展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
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
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
全篇无象无景,只是通过一个“有深趣”的小故事,表达了一种禅思佛理。但苏轼把这个小故事,用诗歌的艺术形式讲述得委婉曲致,妙趣横生,也很有吸引力。所以,王次公在此诗下评注道:“此篇,先生用小说一段事,裁以为诗,而意最高妙。”(《苏轼诗集》P552)
至于《题西林壁》,就更是有名的议论性的哲理诗。而它之所以有名,主要倒还不在于它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抽象的意象式句子,而在于此诗的这两句议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全在于议论得妙,议论得深刻而传之千古。
当然,应该指出,以直接议论的方式阐述哲理,是容易脱离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苏轼也有一些失败的“尚理”之作,就是由于既不借助意象而又缺乏情感,由此滑入枯燥空洞的谈禅说理的泥潭。它们是苏轼在创新实践中所付出的代价吧!
梁宗岱先生在《诗与真. 诗与真二集》中曾说:“哲学诗最难成功”,并分析道:
一提到哲学的诗人,我们便自然而然联想到那作无味的教训诗的蒲吕东(Sully Prudnomme) ,想到那肤
浅的,虽然是很真的诗人韦尼(Alfred deVigny),或者,较伟大的,想起歌德底《浮士德》第二部━━他们都告诉我们以冷静的理智混入纯美的艺术之危险,使我 们对于哲学诗发生很大的怀疑。
又说:
哲学诗底成功少而抒情诗底造就多者,正因为大多数哲学诗人不能象抒情诗人之捉住情绪底脉博一般捉住
智慧的节奏━━这后者是比较隐潜,因而比较难能的。因为智慧底节奏不容易捉住,一不留神便流为干燥无味的教训诗(Pidactic)了。所以成功的哲学诗人不独在中国难得,即在西洋也极少见。
梁先生对哲学诗的这两段分析颇为精彩。诚如之所言,哲理诗确实难于成功,而其之所以失败者居多的主要原因,就是未能处理好哲理与情感、形象之间的关系。而苏东坡的“尚理”,其成功之处,也正是由于他善于将三者有机地结合。如同梁先生所称道的法国象征主义大师梵乐希一样,苏轼也常常以“极敏捷的手腕去捕住那微妙而又倏忽之顷的━━在这灵幻的刹那顷,浑浊的池水给月光底银指点成溶溶的流晶:无情的哲学化作谴绻的诗魂。”(同上)
梁先生说:成功的哲学诗人“在中国难得”,这如果说在宋之前━━更确切地说,在苏轼之前,应该说是对的。王维诗中的禅境、陶潜诗中的道境,都富于哲理思辨的意味,然而,毕竟都未能形成一个时代的美学潮流。而苏东坡,却以其数量丰富,艺术成功的“尚理”之作,影响了整一个时代。当然,这里面还存在其它的因素,如前文所析的时代的因素,也还有诗歌内部发展的要求等。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西方的许多批评家和中国古代的批评家们如严羽等,都还未能认识到,哲理之对于诗歌,并不是排斥的关系━━他们都着重指出了哲理入诗(如果使用不好的话)的危害,而未能认清哲理对于诗歌的重要性。未能认清对于诗歌:
人们要求的是在极短的时间里突然领悟那更高、更富哲学意味、更普遍的某个真理。这可以是诗人感情的
果实,也可以是理性的果实。诗没有果实,只有“精美的外壳”(词句、描绘),是一个艺术上的失败。
(郑敏《英美诗歌戏剧研究》P45)
所以,与其说哲理是诗歌的对立物,还不如说,哲理是诗歌不容易获得的,然而又是最重要的果实和内核。它比情感更为深邃、更能引起读者的深思,并从而产生吟咏不尽的艺术效果。或者进一步可以说,它也是情感之一种,是高度升华而理性化的情感。当然,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就会成为产生“非诗”、“非艺术”的原因。但是,如果在艺术大师,譬如在苏东坡笔底,就会成为保持永久艺术魅力的源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苏东坡的“尚理”名句,使人想起泰戈尔“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飞鸟集》)那具有永久魅力的哲理艺术境界。
正因为“尚理”对诗歌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在苏东坡之后,诗歌“尚理”才成为有宋一代的审美风尚。我们读杨万里的《过松源晨炊漆公店》: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读叶绍翁《游小园不值》:“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读朱熹那有名的《观书有感》:“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莫不是以“尚理”取胜。
因此,我们说,苏诗的“尚理”特点,具有时代的里程碑作用,它奠定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美学潮流及其发展的趋向。
来源:木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