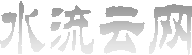木斋《苏东坡研究》
第九章 “信手拈得俱天成”
苏轼“以才学为诗”论
如果说,对苏轼诗歌的其它特点,如“以议论为诗”、“尚理”诗等,还是毁誉参半的话,那么,对“以才学为诗”的评价,就近乎是完全的否定了。
古人批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指斥其背离了从《诗经》到唐诗以来的诗歌传统,背离了诗歌的“本色当行”。因为传统诗歌的方式是“咏物”、“言志”,即诗歌要托之于象,而这种意象又要寄托诗人志趣,要反映社会民生等重大问题。
今人批评苏、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从内容决定形式,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等观点推衍而生的。
那么,究竟“才学”与诗歌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苏轼等为什么要“以才学为诗”?它是否违背了诗歌的艺术思维规律?这些无疑都是诗史上尚未解开的谜。因此,探讨一下苏轼的“以才学为诗”,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不笑所以深笑之也”
“以才学为诗”产生原因的探讨
同“以文为诗”等一样,“以才学为诗”也同样是多方面因素的产物,是由历史的进程、民族文化心理、审美思潮的纵向发展及诗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交汇而成。
历史、文化、美学等所具有的两重性,使受之影响的一代诗歌,成为了一个对立统一体。“以文为诗”和“以才学为诗”,正是宋诗及其代表苏诗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众所周知,宋代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有危机感,自安史之乱以来封建社会的衰落、自北宋建朝以来的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状况等等,构成这种危机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尽管塞外金戈铁马、狼烟不熄,尽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战频仍,士大夫却仍可以倚红偎翠,仍可以闭门觅句。
危机感客观地促进了“以文为诗”的革新:时代要求诗歌表达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更深刻、更复杂的认识,因而,借鉴散文的章法、句法、字法及不借助意象的表达方式等等就应运而生;而稳定性恰正是“以才学为诗”赖以生存的土壤。两宋可以说是一个文人的时代。文人地位之高、学术文化研究之讲求、科学文化之繁荣,实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高峰。杨万里《诚斋诗话》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东坡尝宴会,俳优者作伎万方,坡终不笑。优突出,用棒痛打作伎者:“内翰不笑,汝犹称良优乎”?对曰:“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盖优人用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云:“非不治也,不治所以深治之也。”
当时为“下九流”的俳优尚能如此幽默诙谐,使事用典如此灵活巧妙,北宋文化之普及、之高卓,可见一斑。这是一个知识的时代。没有这种高水平的文化普及,苏黄“以才学为诗”就不会被读者接受,更谈不上风行天下,楷模后世了。
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不但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宋文化,而且,至北宋时期,逐渐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心理及审美思潮。
唐以前,诗歌是传统文化的王冠,诗人们虽然也都博览群书,但学问家和诗人往往不能得兼。学问家很少在诗坛上有成就,诗人的着眼点则在诗而不在学问或其它学科、其它艺术。
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学术、散文成就独步千古,而诗歌却默默无闻;班固虽有五言诗、赋,但不是一流诗人;哲学家何晏之流,学问很深,但所作玄言诗却“淡乎寡味”;艺术家如王羲之、顾恺之,均是书法、绘画世界中的宙斯,于诗也无所成就。
反之,诗人如屈宋、曹刘、陶谢、王孟,直至李杜,在诗歌领域,都“各领风骚数百年”,而在学术、学问上却未能独树一帜。(当然,其中也有逐渐向诗人兼学者演化的趋势)诗人们博览群书,其意不重学问本身,而是求其意趣而已。陶潜“好读书不求甚解”可以为这种现象作注。大诗人曹植幼时“诵读诗论辞赋数十万言”,然有所成就者,诗赋而已。
至唐王孟、李杜一代,就已呈现了转机:一方面,多数诗人如王孟、元白、高岑等,与前人相似,“诗而已”;另一方面,一些诗人如王维,兼画家、音乐家,尤其是其绘画艺术,为一代之宗师;杜甫则更明确地提出了“才学”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影响极为深远。
身兼大诗人、大散文家的韩柳,则更进一步阐发了杜甫的命题。韩愈在《进学解》中,通过他人之口,介绍了自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学习情况,同时提出了“闳其中而肆其外”的著名命题。所谓“闳其中”,正是要“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要“上规姚姒,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须得作者先“闳其中”,而后才能“肆其外”,喷发出作品来。而“才学”自是“闳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面。
柳宗元也阐发了相似的理论,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了“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的著名命题:“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参之《谷梁》以厉其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韩柳所论,虽然主要是从散文创作角度讲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广义的文学创作命题。特别是“以文为诗”的韩愈,把此命题的精神早已引入了诗歌创作的领域,从而成为苏轼“以才学为诗”的先声。进一步说,是王、杜、韩、柳的总和,构成了由唐至宋“以才学为诗”转变的中介,透露了时代审美潮流发展趋势的信息。
宋代以后,诗歌不能独称艺术王国的宙斯,其它艺术形式迅速发展,对学术学问的讲求也日益成为风尚,从而呈现了诗歌与其它艺术形式并进,艺术与学术并驰的趋势。
诗人们不再单纯是诗人,这就势必影响到诗歌作品的构成因素和构成方式。诗人的才学势必要表现和反映到作品中来,而读者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也反过来要求诗歌具有才学性,要求诗歌不仅要具有才学的气质,而且,要具有更多的知识性,更浓郁的趣味性。这就是苏轼“以才学为诗”产生的历史土壤。
宋代大诗人多兼学者,多才多艺是他们共同的向往。象欧阳修,苏轼曾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居士集. 序》)其实,欧比韩有过之而无不及。欧阳子不仅作诗填词,是散文大师,而且还是历史学家、金石学家、文艺批评家等等。
苏轼更是如此。不必说他在诗、词、散文方面的成就,单在书法绘画上的修养就不同凡响。他居宋四大书法家之首;绘画艺术方面属文人写意画一派,所画竹石等具独到之处;他的绘画理论,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在美学理论上,他是从司空图到严羽一派的中介,他发现并大力推崇司空图的理论,大力推崇陶潜平淡自然的诗歌,从而在我国美学史上占有了不容忽视的位置。苏轼还是史学家,上百篇《策论》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造诣,《史记》、《汉书》等都是他了然于心的著作。晚年贬岭南之后,《汉书》是他每日必修的课程,据说他可以从任意一字背写起。苏轼还是哲学家,对儒、道、释三家都有较深的研究。《庄子》以及一些佛学经典,对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晚年他承父志,完成了《易经》、《论语说》等哲学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学者。
在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内,苏轼也都有一定造诣。他对水利、农业、医学都不乏研究,并且对造酒、制墨、烹调等也有兴趣。如果生活在今天,宋代的许多诗人,尤其象欧、苏这样的大家,就不仅是诗人、作家,而且还是身跨社会、自然两大科学领域的学者。这种诗人学者化的特点,势必影响到诗歌创作。诗人们习惯于将才学溶入诗行,而欣赏者则从典故和音韵、学问和才情的和声中感受到美。“才学”与“情性”组成新的审美客体而被时代所接受。
严羽认为苏、黄是“作奇特解会”,其实,他未能看到“以才学为诗”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自然形成的,是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领域里的投影。
苏轼“以才学为诗”也是由于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致,特别是应“以文为诗”的要求所致。从广义上来说,它也可以说从属于“以文为诗”,把当时人们认为是散文范畴的才学纳入了诗歌创作的领域;从狭义上来讲,它们又弥补了“以文为诗”非意象方式的不足。“以文为诗”使诗歌摆去拘束,“以议论为诗”在传统的具象方式之外,又开拓了直接抒发议论的新路,这些无疑都有利于随心所欲地表情达意。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易于使诗歌失去诗的特质,显得松散、不含蓄,而“以才学为诗”恰是从另一个方面平衡了艺术形式的这种失重。
第二节 “艺之成败,系乎才也”
“以才学为诗”的理论探讨
从诗歌的艺术规律看,是否允许“以才学为诗”呢?书本、知识、才学与诗歌创作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说,才学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就是说,有才学不一定就有诗,但写诗则须有才学。古往今来,鸿才博学而无诗流传后世者大有人在,而大诗人不博学鸿才者却也少见。诗人要有才学,而仅有才学却不一定能成为诗人。钱钟书先生有一段分析颇中肯綮:
王济有言:“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性情可以为诗,而非诗也。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必成诗也。艺之成败,系乎才也。......虽然,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学者。大匠之巧,焉能不出于规矩哉。
(《谈艺录》)
此段文字分四层逐步深入,首先是“文生于情”,而情又不是诗本身,此其一;“诗者,艺也”,但是,掌握了一定技艺去“持其情志”,“可以成诗,而未必成诗也”,此其二;“艺之成败,系乎才也”,此其三;“才”是成败的关键,但“才”的产生又主要依赖于“学”,“未有能而不学者也”,此其四。就是说,有情感、有诗艺,仍不能成诗,还要有才,而“才”又靠“学”的后天努力。这样,就逐层深入地论证了才学在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进一步说,“情”、“艺”、“才”三者虽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却也都有赖于“学”。广学,可以使人有才;掌握艺术技巧也需要学习借鉴;而人的情感固然有待于外界事物的触发,然而更需要诗人自我内心所固有的气质、审美力、情感的敏锐和深度等等。这些,无疑都与人的才学修养有极密切的关系。对于一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来说,西风残照、明月小桥、姹紫嫣红、春兰秋菊都不会具有很多的审美价值,自然也难以触发其情思感怀而产生出好诗来。
另外,才学之外,还要有“识”,要有对事物的深刻认识和远见卓识。因此,所谓的“才学”,应是“才”、“学”、“识”三者的统一。有“才”而少“学”,就会使诗人艺术修养欠缺,使作品显得单薄。苏轼批评孟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而少材料”,其实是说孟韵高而学短,学短则使诗人缺少一些表现方式,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方面,有才而少“识”,就难于提出高论。苏轼也曾感叹贾谊“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论》),正是注意到了“识”的地位。
有“才”、“学”、“识”,才能有不同凡俗的艺术修养,才能“宏其中而肆其外”。当然,学识不仅从书本上来,还要从生活实践、艺术实践中来。游历名山大川与博览经史子集,同样可以提高人们的才学。人们有时容易强调“社会生活实践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而忽视书本知识及教学的重要性。其实,任何一个大作家、大诗人无不要吸收前人创造出的优秀成果。攀登在时代巨人的肩上,才有可能超过前人,而书籍则是攀登时代巨人之肩的最重要阶梯之一。
可知,“才学”不但不与诗歌等文学创作相矛盾,反而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在苏、黄等宋人诗作中,“才学”比前人表现得更广泛、更深刻而已。然而,它们并没有走出诗歌艺术王国宽广的领域。
第三节 “用之如何在我耳”
“以才学为诗”的理论和艺术实践
苏轼非常重视“才学”,充分注意到才学与诗歌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曾论述道:
吾闻诸夫子,求益非速成。
譬如远游客,日夜事征行。
今年适燕蓟,明年走蛮荆。
东观尽沧海,西涉渭与泾。
归来闭户坐,八方在轩庭。
......
为学务日益,此言当自程。
(《张寺丞益》)
他是在以远游譬喻“为学”,只有广学博识,才能笔下有神,所谓“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是也。
在《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中,苏轼更是明确地标举了“以才学为诗”旗帜,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一理论。在前二首中,他主要说明了此诗写作的由起,以及“以才学为诗”关键在于如何用的问题:
羡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使儿。
......
世间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满千家墀。
(《其一》)
路旁拾得半段枪,何必开炉铸矛戟。
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当令君丧魄。
(《其二》)
“集古诗”是“以才学为诗”的一种。此种方式正确与否姑且不论,苏轼是在借孔毅父集古人句而发表他对“以才学为诗”的看法。
首先,他对孔借鉴使用前人的诗句表示了赞许:前人的好句应该共赏,它就象是当空明月,自然会照耀千家。如果前人的诗句已经很好地表达了读者自己的内心情感,又何必重新“开炉铸矛戟”呢?
其次,他还指出了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前人之诗:“用之如何在我耳。”继承要为创新服务,借他人之酒杯浇我心中之块垒,要“指呼市人如使儿”,要“入手当令君丧魄”。
在后三首诗中,苏轼进一步阐发了“以才学为诗”的产生以及如何使用才学的问题:
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
......
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
前胜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其三》)
诗人雕刻闲草木,搜抉肝肾神应哭。
不如默诵诗千首,左抽右取谈笑足。
(《其四》)
痴人但数羊羔儿,不知何者是左兹。
千章万句卒非我,急走捉君应已迟。
(《其五》)
诗人首先指出了“以才学为诗”是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致。我国诗史经六朝至唐代以后,借助山水物象的方式已盛极而衰。诗人们与其“搜抉肝贤”、“雕钻草木”、苦吟寒唱,“不如默诵诗千首”,以“才学”作为新的审美客体艺术表达方式,“左抽右取”,表情达意。这一主张正与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命题遥相呼应,暗示了杜甫在“以才学为诗”方面的宗师地位。再者,诗人进一步指出了如何使用才学的问题:一是要用得巧、用得活,不伤天全,用典使事如从己出,要“信手拈得俱天成”;二是要抓灵感。在创作过程上,就是要熔铸才学于胸中,一旦诗情迸发,需火急捕捉,“急走捉君应已迟”;表现在作品中,则要溶铸才学情感于一炉,就象左慈逃入羊群中,曹操“遂莫知所取焉”一样,难以界定。(苏轼用此典出自《后汉书.左慈传》)
苏诗二千余首,无不浸入了苏轼的才学。毫无疑问,它们是苏轼“平生五千字”、“堂上四库书”的折射,并且,其中大多数诗作又是对苏轼这种理论的艺术体现。它们合于“信手拈得俱天成”的审美要求,是才学、情感、技艺等诸因素的统一体。在用典使事的广泛程度上,可以说是天文地理、奇闻野史、音乐绘画、儒经佛典、三教九流无不“曲承其意”,供他“左抽右取”,真可谓“指呼市人如使儿”。
譬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的有名诗句:“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就是分用儒、道两家的两个典故:“空余”句用《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之意;“粗识”句用《庄子. 天运》记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一事。诗人由渡海北返,想起了孔子的喟叹;由波涛声联想起庄子笔下的黄帝奏乐之声,从而揭示了儒道二家思想在他自己思想体系中的对立统一。又如黄州时期所写《侄安节远来夜坐》中的一句:“遮眼文书原不读”,则是用佛典《传灯录》:“有僧问药山惟俨禅师:‘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为什么却自看?’师曰:‘我只图遮眼’。”苏轼反其意用之,说自己连“只图遮眼”的书都不读了,从而揭示了他在乌台诗案后的痛苦心情,暗示了他对当时黑暗政治及专制文化的抗议。
如前文所析,苏轼“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常使诗歌松散、直露,“以才学为诗”使事用典则是以另一种方式浓缩情感、提供意象,从而弥补了“以议论为诗”等的不足。
试看苏轼《和刘道原见寄》中的两句:“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前句用西汉汲黯事。《汉书. 汲黯传》载:“淮南王谋反,惮汲黯,曰:‘黯好直谏,守节死义,至说公孙弘等,如发蒙耳。’”后句用伯乐故事,韩愈云:“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送温造赴河阳军序》)诗人通过说汲黯、伯乐之事,表达了对刘道原的赞美。又如有名的“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用塞翁失马和贾昌斗鸡两个典故,披露了其峥峥傲骨,深蕴了不屈精神━━使事用典,无疑起到了浓缩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意的作用。
又如这样一首小诗:
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
全篇用典。首句用《庄子. 田子方篇》:孔子见老聃曰:“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吁。”第二句用《庄子. 秋水篇》河伯“望洋向若而叹”之事。前二句以典故描写了钱塘江潮“东来气吐霓”的宏伟壮观的气势。三、四句用吴王夫差“尝以弓弩射潮头,与海神战,自尔水不近城”之事。然而,“三千强弩射潮低”,这又是何等壮观的气势、何等宏伟的场面!这是人与自然角斗的历史画卷,是惊涛雷鸣、天风海雨逼人的交响乐!它是历史,也是现实,是诗人想象中的现实。这种“以才学为诗”,不也同样震撼人的心弦,使人产生丰富生动的想象,从而具有了永久的艺术魅力吗?
有些直接议论之作,使事用典的艺术方式使其平添了几分含蓄性。诗人的情怀感思、感慨怅惘凝聚在历史的故事中,欣赏者则从典故中,与诗人共同缅怀历史,俯仰古今,从而也具有了含蓄的特质。试看苏轼《戏书吴江三贤画像三首》中的两首小诗:
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
却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
(《其一》)
千首文章二顷田,囊中未有一钱看。
却因养得能言鸭,惊破王孙金弹丸。
(《其三》)
(《苏轼诗集》P564)
前首缅怀范蠡,但又不单是忆范。短短四句议论,追溯的却是一个漫长悠远的历史时期,是丰富多彩、耐人寻味的社会历史画卷,含纳了两个故事:
一是春秋时,楚臣申公巫臣(即屈申)曾谏止楚庄王娶夏姬,及楚共王继位,共王又欲娶夏姬,并以申公为使,申公却“以夏姬行,遂奔晋”,在楚杀巫臣之族后,“巫臣乃通吴于晋,教之射御战阵,吴始伐楚。”(《左传. 成公二年》)这是吴楚战争之始,也就是诗中所说:“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
二是吴王夫差遣伍子胥等征楚讨越,称霸中原,渐次骄奢,“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司马迁《史记.淮南传》)预言了吴必亡于越, 就是诗中所说的“却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从而引出了越臣范蠡辅助越王勾践,打败夫差,功成身退,“取西施,乘扁舟游五湖而不返”(东史《环宇记》)的第三个故事。
诗人四句诗讲了三个故事,容量不可谓不大,这是一种意义上的含蓄;诗人由此欲引发出何种教训,得出何种结论,也没有直说,需要读者从历史事件本身,及诗中提供的“笑”、“怜”等含有较多主体情感因素的字眼去思索玩味,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含蓄。
后首是讲唐末大诗人陆龟蒙之事。前两句直接叙述,但也深含了诗人的不平之意:陆龟蒙之“千首文章”,才华横溢,与其“两顷田”的贫困如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后两句讲了一个幽默故事:陆有斗鸭一栏:“一旦,驿使过焉,挟弹毙其尤者。龟蒙曰:‘此鸭善人言,见欲附苏州上进,使者奈何毙之?’使者惧,尽与囊中金以窒其口,徐使问人语之状,龟蒙曰:‘能自呼名耳。’”(《苏轼诗集》P566)风趣诙谐,令人哑然失笑。诗人的情意也就寓于这一怒一笑之中了吧!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概括说,与唐相比,唐人情思含蓄凝聚于意象,宋人情思含蓄凝缩于故实。前者更接近大自然,后者更靠近人类社会;前者具有自然之美,后者更具知识美。尽管艺术方式不同,美感特质不同,具有审美意义却是共同的。在宋人那里,情思和美感通过故实来交流;诗人的思想等凝聚在典故中,同时也能引起读者广泛的想象。读者读懂这些典故之后,那些曲折丰富、引人沉思的故事情节,就会翩然而至。读者根据这些故事、人物、情节等,去把握诗人的弦外之音,从而感受到愉悦和美。知识,在这里成为交通桥梁、共鸣的谐音!
使事用典,常常会改造意象这一艺术方式,使之翻新出奇,摇曳生姿。如《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这是一首论茶品茗之作。此题材易写得平淡无奇,至多是以茶喻人。而苏轼却以人写茶,以人的典故写茶:
纵复苦硬终可录,汲黯少戆宽饶猛。
其间绝品岂不佳,张禹纵贤非骨鲠。
用直言忠谏、被汉武帝评为“戆”的汲黯,和“奸犯上意,自刭北阙下”的宽饶(《苏轼诗集》王次公注),来比喻建溪茶的“苦硬”;用“虽有学问,细行谨防,终非骨鲠之臣”(《乌台诗案》)的张禹来比喻“荣茶”的“无赖空有名”。
再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知道,建溪茶和荣茶又分别象征着当时的两种人物:直言忠谏之臣和妥协求全之辈。以人比茶,又以茶喻人,翻转了两个层次,却不露用事之痕。故纪晓岚评:“将人比物,脱尽用事之痕,开后人多少法门。”
使事用典,不仅使诗歌增加了含蓄美、凝炼美,使之富于趣味和知识,发展了诗歌表达的艺术方式,而且,化用前人诗句,也是继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如写夜阑赏花之作,白居易云:“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惜牡丹花二首》);李商隐又云:“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苏轼《海棠》诗则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不是简单地借鉴和化用,而是发展和升华。“只恐”句把审美客体的美通过自我审美意识折射出来,形成物我无间的统一体;“红妆”暗喻的运用,则又比“衰红”、“残花”更曲折、更生动、更形象、更富有审美价值。全诗由一个单纯赏花惜时的场景,升华到富有哲理禅思意味的艺术境界,因而也就比前人之作更深刻、更富有魅力。
苏轼不仅化用前人诗句,还化用当代人的,甚至化用自己的诗句,“用自己诗为故事”(《优古堂诗话》)。如《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云:“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用十五年前所作《望湖楼醉书》:“白雨跳珠乱入船”之意。苏轼故地重游,十五年沧桑,多少往事、多少感慨、多少人生的苦乐,都蕴含在“跳珠”这一形象“故事”里了。这是任何古人之词、他人之句都无法替代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严羽所说“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其中确有些偏颇。
首先,“多务使事”固然是苏诗的一个艺术特点,但是因此就说他“不问兴致”,却不尽然。从苏轼的总体美学观来看,决不是主张内心无情感就写诗的,“有为而作”是苏轼著名的文学主张。从本文所举诗作看,也大多是有感于心而借典表意的。
其次,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本身就是一种夸大。苏诗中无来历、无出处而或凭借物象、或直接抒发以成诗者亦不在少数。人们对于大诗人、大学者之作往往喜爱寻求其字词的来历、出处。其实,杜甫也好、黄庭坚也好,他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构思时,一定不会在那里苦心积虑地寻找什么“来历”、“出处”。只因他们博学多识,所谓“来历”、“出处”都装于自己胸中、深入诗入魂魄,成为诗人情感思想的一部分:历史的成为现实的,他人的化为自己的,才会产生“信手拈来俱天成”、“左抽右取谈笑足”、“指呼市人如使儿”那恣意挥洒的“以才学为诗”。只有这样,才可能既是使事用典,又如行云流水而不见斧凿雕琢痕迹。
欧阳修曾称赏青年苏轼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诚斋诗话》)我们可以借此语说,苏轼善读书、善用书,遂使苏诗在我国诗史发生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变革后,“独步天下”。
来源:木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