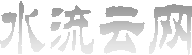木斋《苏东坡研究》
第十章 “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
苏轼“以文字为诗”论
同“以才学为诗”相似,对苏轼“以文字为诗”的评价,也近乎完全的否定,而且,此二者常常被并提或混用。如前文所引张戒语:“苏黄用事押韵之工。”“用事”,实际上主要讲“才学”问题,“押韵”主要是讲“文字”问题。“押韵”的对立面是“言志”,即要求诗歌反映严肃的社会民生等重大问题。因此,张戒所论,乃是批评苏黄“押韵”之作,以“文字”为游戏,违背了我国《诗经》以来的“风雅”、“言志”的传统。
严羽所论,也近似之。所谓“以文字为诗”,“终非古人之诗也”,“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道何在”,命意也同样在此。 对“以文字为诗”批评的另一方面,是指斥其“次韵”等方式,破坏了先秦以来逐渐形成的追求自然天全的审美情趣和风格。如元代王若虚批评道:
次韵实作诗之大病也,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者多矣。
(《滹南遗老集》)
现在学术界对苏黄“以文字为诗”的批评内容更为广泛、尖锐。如有的学者说:“严羽的‘以文字为诗’,则主要指的是宋代诗风的两个不良倾向,一是雕琢文字游戏音韵,一是‘点铁成金’”,认为“‘以文字为诗’是宋诗的主要弊病(形式主义创作倾向)之一”。在“以文字为诗”的内容方面又进一步批评道:
“苏黄诸大家胸中学问有余,不免矜矜然玩弄音韵,游戏文字。......苏轼单和陶潜的诗,便做了一百二十
首。诗人间酬韵征逐、互相唱和,琐屑而频繁,有多至来回八、九遍的。至于游戏文字,以“戏题”、“戏赠”为题的诗,内容大都揶揄不经,等而下之又有什么回文诗、谐隐诗、人名诗、神智体、集句诗、谜语诗,种种不一。苏轼好做回文诗,动辄几首一组,神智体亦是他
的发明。
(参见《河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
笔者认为,苏轼的“以文字为诗”同他的“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一样,自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况且也并未脱离开诗歌的本质特征,更谈不上是“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因此,
重新探讨苏轼的“以文字为诗”,对于苏诗甚至整个宋诗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都具有重要意义。
刘克庄《后村诗话》云:“元【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似将“以文为诗”和“以文字为诗”分属苏、黄二公。而在宋诗里,后者似比前者更为明显,影响似乎也更为深远。因此,在评价苏、黄何者更能代表宋诗的本质特征时,人们多投黄山谷的票。实际上,苏诗不仅“句律疏”,而且也兼具“锻炼精”的特点。因此,重新评价苏轼的“以文字为诗”,也兼能回答这一问题。
第一节 “奈这事须当归”
简议苏轼“以文字为诗”产生的原因
“以文字为诗”同“以才学为诗”是一对孪生姊妹。因此,上一章“以才学为诗”产生原因的诸多探讨,同样适宜于“以文字为诗”。北宋时期相对的稳定性,不但是“以才学为诗”产生的土壤,而且也滋生了“以文字为诗”;北宋文化的高度发达,不但直接造就了时代的才学性,而且也直接培养了时代的“文字性”。所谓“玩弄音韵,游戏文字”、“酬韵征逐”等等,一时之间成为了时代风尚,成为了当时士大夫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诗人们不仅以笔为“文字”之戏,而且以口为“文字”之乐。
《朝野遗记》载:
刘贡父觞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刘调之曰:“幸早里且从容。”子瞻曰:“奈这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
药为对。
刘贡父所说三果为:杏、枣、李,一药为苁蓉(为草苁蓉和肉苁蓉的统称);东坡所说三果为:柰(柰子,为苹果的一种)、蔗、柿,一药为当归。
曾敏行《独醒杂志》载:
坡、谷同游凤池寺,坡公举对曰:“张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答云:“柳屯田之妙句,哪更重来。”时称名对。
可知,出口成章、成“对”,乃是时代之风尚,如果一时之间“仓卒无以答”,竟会“终身以为恨”。这种习俗,成为诗人们锻炼才思敏捷的极好方式。同时,诗人们也在这种口头创作的“文字游戏”中,得到美的享受。
苏东坡才华横溢,且又具有谑弄戏浪的“野性”性格,就使他在这种时代风尚中,更是如鱼得水,放浪纵姿。很多诗话都记载过东坡以“毳饭”待客的轶事:
东坡曾和刘贡父说他自己在“习制科时,曰享三白”,所谓“三白”,即“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于是,当东坡到刘家作客时,刘就以“三白”待客,东坡于是请刘贡父到家中吃“毳饭”,当刘“如期而往,谈论过食时,贡父饥甚索食”,东坡告诉他:“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非‘毳’而何?”“毛”在当时与“没”同音,故曰:“毳”。(参见朱弁《曲洧旧闻》)
东坡的性格与其才华结合在一起,就使之成为了一个极大的幽默家,成为时代“文字游戏”的佼佼者。诚如钱穆父所赞叹:“子瞻可谓善戏谑者也。”(《高斋漫录》)
《渑水燕谈录》载:
贡年晚年苦风疾,鬓眉皆落,鼻梁且断。一日,与子瞻数人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子瞻戏贡父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噱。
读后使人不禁哑然失笑,东坡真可谓幽默之伟人,戏谑中巨子。
当然,苏轼“以文字为诗”的产生,也是由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致,特别是应“以文为诗”的要求所致,(同“以才学为诗”相似)同时,它又从另一个方面弥补了“以文为诗”的不足。 “以文为诗”使诗歌摆去拘束,这固然有利于随心所欲的表情达意,但是,诗歌自身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却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正如西方诗人所说:
形式越难驾驭,
作品就越加
熠熠生光:
诗、玛瑙、珐琅、大理石全都一样。
不需要无谓的束缚!
但是
你啊,为了笔直地前进,
缪斯,
请把舞靴系紧。
(法.戈蒂耶《艺术》)
苏轼“以文字为诗”中的和韵,就可以说是这种难以驾驭的“舞靴”,它从一个方面平衡了宋诗艺术形式的失重。
第二节 “和韵而似原韵”
苏轼以“以文字为诗”的艺术实践
按照前文所引一些同志的批评,苏轼的“以文字为诗”大约可分为“和韵”、“戏题”、“回文”、“谐隐”、“人名”、“神智”、“集句”、“谜语”等,那么,就按照这个线索,对苏轼“以文字为诗”的艺术实践,作个粗浅的巡礼吧!
一 、 对“和韵”的探讨
首先看“和韵”。
据金人王若虚的统计,苏诗“集中和韵者几三之一”,不可谓不多,然“害于天全”却又未必。恰恰相反,在和韵的“舞靴”里,苏轼创作了大量的杰出之作。著名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就是出自《和子由渑池怀旧》;“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也是出自《次子由韵》。又如《次韵张安道读杜诗》:
地偏蕃怪产,源失乱狂涛。
粉黛迷真色,鱼暇易豢牢。
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
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
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
(《苏轼全集》265)
诗人在和韵的“舞靴”里,酣畅淋漓,心情抒发,提出了中国诗史上的一些著名命题。在命意、遣词、造句方面也都不乏新意。如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六批云:“主宾(指杜甫和李白)判然,疏密相间,于排比之中,寓流走之法。面目是杜,气骨是苏,非杜不能步步为营,非苏不能句句直下。其驱遣难韵,若无其事焉者,不知何以凑泊至是,而杜排无此难作诗也。”纪晓岚亦评曰:“字字深稳,句句飞动,如此作和韵诗,固不嫌于和韵”;“难韵巧押,腾挪处全在用比”。
又如《次韵吴传正枯木歌》:
天公水墨自奇绝,瘦竹枯松写残月。
梦回疏影在东窗,惊怪霜枝连夜发。
生成变坏一弹指,乃知造物初无物。
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
龙眠居士本诗人,能使龙池飞霹雳。
......
东南山水相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
尽将书画散朋友,独与长铗归来乎!
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五评此诗曰:
因吴诗而及李画,因歌枯木而及画马,轩然而来,翩然而往,随意所到,总入元(玄)微。
“轩然而来,翩然而往,随意所到”,确实是苏轼这首“次韵”诗作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苏轼大多数次韵诗作的共同特点。不仅如此,诗人在这些次韵诗作中,还能经常出人意表地迸射出天才的火花,写出传诵千古的绝句。象此诗的“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上首的“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都是非常著名的文学命题。
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评苏轼的《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韵,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其实,苏轼的许多和韵之作,都可说是“和韵而似原韵”的。与苏轼的这些和韵诗相比,原作往往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甚至多有原作不传者。如上文所举《次韵吴传正枯木歌》,纪晓岚评曰:“吴诗不传,不知原唱之意,亦遂不甚解和之之意。”可知,吴诗在清代时已不传了,而苏诗却高悬日月,垂辉至今。
诗人们相互之间酬韵征逐,唱和互答,时而确乎有些“琐屑而频繁”,某些唱和之作,也确乎流于形式。但是,即便是这种多次的往来唱和,在天才诗人苏轼的笔下,也仍然不乏妙篇和佳句。
譬如元〖六年,苏轼在做过《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之后,又做《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此十首不仅比杨公济原作精彩,而且,比之东坡自己的前十首也更为出色。试看二绝:
人去残英满酒樽,不堪细雨湿黄昏。
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风流楚客魂。
(《其四》)
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
盈盈解佩临烟浦,脉脉当炉傍酒家。
(《其五》)
如果用西方现代派的某些理论来分析这两首诗,可以说,诗人是混用了“意象”、“移情”、“通感”等多方面的手法,创造了美好的艺术境界。前一首的“梅花”,时而幻化成“穿花蝶”,在细雨黄昏中翩翩起舞;时而又转变成风流客魂,幽然悄至;其中一个“湿”字,更把诗人的深沉的感受挪移为器官的感受,十分精警动人。后一首的梅花,与整个自然同时幻化为美人,它与“抱山斜”的“芳草”,共同构成了美人的“裙腰”,袅袅娜娜,亭亭玉立,有如当年脉脉当炉的卓文君。
苏轼不仅与当时诗人酬韵唱和,使情感在相同的节奏音韵中得到共鸣,使艺术技巧互相补益,而且他还酷爱和古人之诗,单和陶渊明诗就有一百二十首。但是,无论和今,还是步古,从主流上来说,苏轼都没有脱离开现实生活,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是在借鉴他人、古人成功的艺术形式,来抒发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强烈感受;是在学习他人、古人的艺术风格中,熔冶铸炼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譬如熙宁五年时,苏轼在梵天寺读到此寺僧人守诠曾做过的一首小诗,诗云:
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
松扉竟未掩,片月随行履。
时闻犬吠声,更入青萝去。
苏轼读过,十分喜爱,于是次韵和之:
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
幽人行未归,草露湿芒履。
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
(《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
此诗十分明显地与苏诗的总风格不太一样,它是苏轼学习前人风格的产物。正是这种和诗次韵,才提供了苏轼向前人学习借鉴的途径,从而使苏诗组成了自己的风格多样、博大精深的艺术体系。
再看和陶诗,如《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虽曰“和陶”,写的却是诗人自己在惠州游白水山的感受:
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
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
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
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
这是对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的和诗。诗人在“稀、归、衣、违”的韵律中舞蹈,却如出天然。这里不仅有“新沐感发稀”那老年人的亲切感受,也有“有约吾敢违”的真情抒发,还有“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这样新警动人的名句。足可抵挡“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之原句。而且,全诗深得陶诗之神韵,如纪昀所评:“极平浅而有深味,神似陶公。”
苏轼还常和自己的诗韵,这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创作情感的惯力。当构思、创作了一篇佳作之后,感到余兴未尽,诗情还继续兴奋在音韵节奏的旋律里时,诗人的舞步就会不自觉地再向原来的韵律踏进。于是乎,一和再和,兴尽而已。如在熙宁时期,诗人去孤山访二位僧人,写下著名的《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此诗在苏诗中亦堪称上乘之作,如纪晓岚所评:“动合天然,不容凑泊”,特别是结句,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文学灵感的命题,足资借鉴。但是,苏轼的随后几篇唱和之作,也都并不“见绌”: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笞环呻呼。
......
人生何者非蘧庐,故山鹤怨秋猿孤。
......
岁荒无术归亡逋,鹄则易画虎难摹。
(《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原韵答之》)
前四句表达了诗人的“野性”人生观念;中二句更是富于哲理意味的佳句,与“天涯何处无芳草”,可谓异曲同工;结二句用典:“言岁既饥荒,我欲出奇画赈济,又恐朝廷不从,反似画虎不成类狗也。”(《乌台诗案》)
此诗之后,诗人余兴未尽,又作《再和》诗:
东望海,西望湖,山平水远细欲无。
野人疏狂逐渔钓,刺史宽大容歌呼。
......
穷多斗险谁先逋,赌取名画不同摹。
《再和》之后,诗人又作《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虽然诗人的步履由访孤山而至“游灵隐”,诗人韵律的步履却复踏在原来的旋律上,于是诗人写道: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
......
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
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
......
归时栖鸦正毕逋,孤烟落日不可摹。
此诗在三次唱和之后,仍然豆蔻年华,楚楚动人。“溪山”二句,更是千古绝唱,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结句也创造了一幅“孤烟落日”的绝美画图。
苏轼在唱和诗中,取得了令人惊诧的成绩,如晁以道所评:(苏轼)“和人诗用韵妥贴圆成,无一字不平稳。盖天才能驱驾,如孙、吴用兵,市井乌合,亦皆为我臂指,左右前却,在我顾盼间,莫不听顺也。前后集似此类者甚多,往往有唱首不能逮者。”(见朱弁《风月堂诗话》)
和韵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天才能驱驾”,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镣铐”无力桎梏缪斯的神翼。相反,诗人常会踏着镣铐的节奏,御其风而飞行。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就是诗人在必然的艺术规律中获得了创作自由。这没有渊博的学识、雄厚的生活基础,是难以达到的。事实上,唱和的艺术形式自两宋盛行以来,“唱首不能逮”的情况也甚多。前文所析有原作不如东坡唱和之作者颇多。而东坡自己的原作也时有不如别人唱和的事例。譬如黄山谷的“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就超过了东坡。这其中的奥妙,很值得玩味深思。
二、对所谓“戏”字的考察
其次,看一下所谓“游戏文字,以‘戏题’、‘戏赠’为题的诗”。
在苏轼诗作中,以“戏”字为题的诗作,确实为数不少。但是,如果进一步深入考察,就会感到,东坡之所谓“戏”,多是欲哭无声,怒极反“戏”之作。可以说是寓庄于谐,寓严肃深刻之主旨于戏谑放浪之外形。
譬如《戏子由》诗: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
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
......
读书万卷不知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笞。
......
此诗名为“戏”,实际上却是“庄”。一开始就为当时正为学官的子由报不平,极写其住所之小之陋,然后,用东方朔和优旃的典故,进行“含泪的微笑”的渲染。《前汉.东方朔传》曰:“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史记.滑稽列传》载:
优旃善为笑言。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盾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居有顷,殿上求寿。优旃临槛大呼曰:“陛盾郎,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盾者得半相待。
苏轼反其意而用之,说子由有如雨中而立的陛盾者,然岂肯为“雨立”而求之于优旃?在这个玩笑中,东坡寄寓了深刻的同情和庄严的赞美。而“致君”、“平生”二联,更是严肃的政治命题和深刻的人生反思。
又如《欧阳晦夫遗接离琴枕,戏作此诗谢之》:
携儿过岭今七年,晚途更著黎衣冠。
白头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须花缦。
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
见君合浦如梦寐,挽须握手俱〖澜。
(《苏轼全集》2372)
此诗是东坡晚年遭贬岭南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人描绘了“白头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须花缦”的诗人自我形象:一位“九死南荒”而仍然情思浪漫、胸怀豁达的老人,他一生名扬四海,现在却赤足黎装,俨然是一个土著老叟的模样了。这当然会使人捧腹倾倒,故称“戏作”。然而,“携儿过岭今七年,晚途更著黎衣冠”;“见君合浦如梦寐,挽须握手俱汍澜”,这又是怎样悲惨难堪的遭遇呵!“食芋啖水”、“一夕三迁”,七年流放生涯的痛苦回忆,都化入在这一“戏”字之中了!这种情形,有如朱光潜先生所说:
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入了至性至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P31)
苏东坡的所谓“游戏之作”,大都属于此类。这些不仅不是苏诗的弊病,反而是苏诗“独有千古”的标志之一。清人方东树《昭味詹言》评苏诗云:
杂以嘲戏,讽谏谐谑,庄语悟语,随事而发,此东坡之独有千古也。
可谓确评。黄彻《砻溪诗话》更进一步指出道:“大体材力豪迈有余而用之不尽,自然如此,......坡集类此不可胜数。”
由此可知,苏轼的所谓“以‘戏题’、‘戏赠’为题的诗”,不仅在内容上并非“揶揄不经”,且在艺术上反而独具特色,不同凡响。
再譬如《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一诗,从题目所透露的背影看,似乎是诗人在“肩舆”中坐着睡着了,梦中得二句诗,然后“戏作”凑此一篇。实际上,这一“梦中得句”,却正体现了诗人的苦心构思、精心锤炼之工。因此,全诗虽题“戏作”,却实属上乘佳篇: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
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
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
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
幽怀忽破散,咏啸来天风,
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
......
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
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
全诗堪称精美绝伦、脍炙人口。正如汪师韩所评:“行荒远僻陋之地,作骑龙弄凤之思,一气浩歌而出,天风浪浪,海山苍苍,是当司空图‘豪放’二字。”(《苏诗选评笺释》卷六)
三、对“回文诗”、“神智体”等的思考
最后,再谈谈所谓“等而下之”的“回文诗”、“谐隐诗”、“人名诗”、“神智体”、“集句诗”、“谜语诗”等等。
这些诗,名目虽然繁多,然究其实,都不过是文艺的游戏性和娱乐性的产物。反过来可以说,这些诗体,集中体现了文艺的娱乐性质。譬如《侯鲭录》曾记载了一个东坡在韩绎(子华)家宴会上做人名诗的故事:
子华新宠鲁生,舞罢为游蜂所螫,子华意甚不怿,久之呼出,持白团扇从东坡乞诗。坡书云:“窗摇细浪鱼吹日,舞罢花枝蜂绕衣,不觉南风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归。”上句纪姓,下句书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厮赖,故云耳。”客皆大喜。
东坡即兴所作此诗,首句是“鲁”字的字谜诗,或称人名诗:“鱼吹日”者,鲁也。次句云鲁生被蜂螫之事,后两句则是此游戏的生发。全诗本没有什么严肃的题旨,却洋溢着幽默的欢娱,给人以艺术的快感和美的享受。
“回文诗”,苏轼也确实作了一些。如《次韵回文三首》:
春机满织回文锦,粉泪挥残露井桐。
人远寄情书字小,柳丝低日晚庭空。
(《其一》)
红笺短写空深恨,锦句新翻欲断肠。
风叶落残惊梦蝶,戍边回雁寄情郎。
(《其二》)
羞云敛惨伤春暮,细缕诗成织意深。
头畔枕屏山掩恨,日昏坐暗玉窗琴。
(《其三》)
这些诗,如此反过来看,仍然是好诗,如前两首,我们翻转一下:
空庭晚日低丝柳,小字书情寄远人。
桐井露残挥泪粉,锦文回织满机春。
(《其一》)
郎情寄雁回边戌,蝶梦惊残落叶风。
肠断欲翻新句锦,恨深空写短笺红。
(《其二》)
翻转回文,不仅仍说得通,而且不乏机警之处,如“低丝柳”的“低”字,“满机春”的“满”字,“恨深空写”的“空”字等等,都是富有动感的传神之笔。大诗人天才横溢,知识渊博,偶而搞一点诸如此类的文字游戏,也仍然显得卓然不群,不同凡响。这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
“回文诗”并非苏轼的发明,而“神智体”却是苏东坡之首创。
据宋人桑世昌《回文类聚》载,苏轼曾作《晚眺》诗云:
长亭短景无人画,老大横拖瘦竹筇,
回首断云斜日暮,曲江倒蘸侧山峰。
苏轼当时并没有把诗这样写出来,而是“以意写图,令人自悟”,那么,各位读者,你能猜得出,这个文字图是什么样的吗?
据载,苏轼写此诗是为了难倒北朝使者。使者当时自以为很懂诗,但看图后竟不知所云,极为惶愧,声言:“自后不复言诗矣。”
此外,苏轼还有所谓“集字诗”,如《归去来集字十首. 并引》,《引》云:“予喜读渊明《归去来辞》。因集其字为十诗,令儿曹诵之,号《归去来集字》云。”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字,重新组合成诗,这就更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而且是束缚得异常紧的“镣铐”。然而,苏东坡却表演得非常出色,达到了他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的目的。如:
......
云内流泉远,风前飞鸟轻。
相携就衡宇,酌酒话交情。
(《其一》)
矫首还傲世,委心还乐天。
农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其四》)
觞酒命童仆,言归无复留。
轻车寻绝壑,孤棹入清流。
乘化欲安命,息交还绝游。
琴书乐三经,老矣亦何求。
(《其七》)
寄傲疑今是,求荣感昨非。
聊欣樽有酒,不恨室无衣。
丘壑世情远,田园生事微。
柯庭还独眄,时有鸟归飞。
(《其十》)
《其七》和《其十》二篇,全篇都极富境界。如第十首的“柯庭还独眄,时有鸟归飞”,意与境合,大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格调。第七首的“轻车寻绝壑,孤棹入清流”,使人想象,似乎不是陶渊明而是苏东坡自己轻舟孤棹,陶醉在大自然的绝壑清流之中。
第三节 “笑谑也占一个重要的位置”
小议文学与游戏、娱乐的关系
以上诸多诗体,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游戏性、娱乐性为其特征。那么,这种游戏性、娱乐性,是否违背了诗歌的本质特征了呢?
对于艺术本质的理解,以前似乎过于狭隘。文学艺术当然可以有功利性,但也应该允许有非功利性的一面。笔者并不认为文艺的全部属性就是游戏,因此,也不赞成西方文艺游戏说的理论;但是,文艺的游戏作用,或寓教育于游戏之中,或在游戏中熔铸欢欣乐观的情怀,从而使人产生艺术的愉悦和美感享受的作用,这一点,也应有其一席之地。
朱光潜先生认为:
凡是真正能引起美感经验的东西都有若干艺术的价值,巧妙的文字游戏,以及技巧的娴熟的运用,可以引起一种美感,也是不容讳言的。
并且引用托尔斯泰的观点加以论证,说:
托尔斯泰以为艺术的功用在传染情感,......在他认为值得传染的情感之中,笑谑也占一个重要的位置。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
国外的美学家、理论家也多持此论。如爱笛生在《论洛克的巧智的定义》中说:“凡是新的不平常的东西都能在想象中引起一种乐趣,因为这种东西使心灵感到一种愉快的惊奇。”韦洛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则说:
整个美学史几乎可以概括为一个辩证法,其中正题和反题就是贺拉斯(Horace)所说的“甜美”(dulce)和“有用”(utile),即诗是甜美而有用的。
上述的每一种看法,孤立起来看,都不可能通过,如果说诗是“游戏”,是直觉的乐趣,我们觉得抹杀了艺术运思和锤炼的苦心,也无视诗歌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可是,如果说诗歌是“劳动”或“技艺”,又有侵犯诗的愉悦功能及康德所谓的“无目的性”之嫌。
因此,文学一方面是严肃的、功利的,一方面又是游戏的、非功利的,这就是文学艺术本质上的对立统一,或说是“二律背反”。
以上所析苏轼的“以文字为诗”,也同样是由这两个大的对立因素组成。一方面,所谓“和诗”,所谓“戏作”,其本质常常是严肃的政治命题,如朱光潜先生所说,这种作品大多是诗人“看出人生物态的不圆满,因而表示惊奇和告戒”,所以,它常常是“沉闷艺术中一种解放束缚的力量”(《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另一方面,苏轼的“人名诗”、“集句诗”、“字谜诗”、“神智体”等,又都具有非功利性的一面,称之为“游戏文字”。
“游戏文字”,一方面由于它也能“引起美感经验”,因此,其本身也具有艺术价值,具有审美意义;另一方面,这些“文字游戏”也是一种提高诗歌艺术水平、锻炼诗歌艺术技巧的方式。诗人们在这个巨大的文字娱乐场上驰聘,有如在练兵场上练习枪法,一旦真上战场,就会武艺超群、身手不凡,左抽右旋、无不中的。关于苏轼锻字炼句的艺术,可参见前章“以文为诗论”中的“字法”一节,此处可再举出两例,以做补充:
王元龙,名安国,字平甫,介甫之弟,与东坡交。尝自负其《甘露寺》诗:“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水卷苍藤”,坡应之曰:“精神全在卷字,但恨飞字不称耳。”平甫请易之,坡遂易以“翻”字,平甫叹服。
(《苏诗施注》)
东坡为王元龙改诗,易“飞”以“翻”字,境界顿出。苏轼自己在《记王平甫诗》一文中,后来也记载了此事,并且评论说:“大抵作诗当日锻月炼,非欲夸奇斗异,要当淘汰出合用字。”如此警语,大抵也可视为苏东坡“以文字为诗”的纲领之一吧!
又唐庚《语录》载,苏轼的《病鹤诗》,在写出了“三尺长胫瘦驱”六字后,“阙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盖‘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
可知,刘克庄所谓“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的概括,并不是十分严谨的。苏轼的诗一方面固然是“波澜富而句律疏”,具有“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一面;另方面却又蕴含着“锻炼精”等“以才学为诗”的另一个侧面。黄山谷突出强调了“锻炼精”的方面,苏东坡则要“锻炼精”为“句律疏”服务,要用“以文为诗”统帅“以文字以诗”,要求后者服从于意的表达。张耒《明道杂志》载:
苏长公有诗云:“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黄九云:“初日头。”问其义,但云若此僧负喧于初日耳。余不然,黄甚不平,曰:“岂有用白对天乎?”余异日问苏公,公曰:“若是黄九要改作‘日头,也不奈他何!”
黄山谷认为用“白”字对“天”字不好,因此,坚持将“白”字改为“日”字。苏轼则认为如此改法,则要以文害意了。从这则笔记中,似乎可以看出苏、黄区别的个中消息。
结束语
综以上所述,可知,社会时代的发展,美学思潮的变迁,诗史内在矛盾运动的规律,与东坡巨鱼纵壑的“野性”、天才横溢的诗才等诸多因素相结合,才诞生了苏轼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和“尚理”之作,从而在灿烂辉煌的唐诗之后,另辟蹊径、重伐山林,踏出了一条与
前人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崭新道路。宋诗的体制,在苏诗这里,应该说是已经确立了。
苏诗,确实是个海涵地覆,博大精深的艺术宝库。它几乎囊括了宋代诗歌的所有的主要艺术特点,以后的江西诗派等,不过是从苏诗的某一点上突出强调,并走向极端而已。从这一点上说,严羽指出了苏、黄是宋诗体制产生的质变点,“至苏、黄始自出己意以为诗”,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苏诗,完全可以成为代表宋诗艺术的里程碑。
有人会说,“以文为诗”、“哲理”、“议论”等都并非始于苏轼,何以将此功绩归于苏轼呢?笔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量变和质变的不同,就诗史发展来看,只有当某人的诗歌特点成为足以影响时代的潮流,从而成为一代诗歌的特点之时,我们才可以说,他是诗史发展中的质变点。
苏轼的前辈们如欧阳修等人,虽然对“哲理”、“议论”等都作了积极尝试,但从数量上、质量上都还不足以影响时代的风尚。明人陶望龄对此曾有过天才的猜测:“永叔诗虽好,终不如子瞻,盖子瞻如海,永叔如三山。虽仙都所灵,终是大海中物。”(《歇庵集与袁六休书》)因此,可以说欧阳修等前辈,还仅仅是为苏轼实现飞跃而铺垫道路的量变。
苏诗这一哲理诗的王国,固然是应时代之运而生的。反过来说,哲理的时代也反过来促进和扩大了其影响,使之成为立刻被普遍接受、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末期的审美潮流。
事实上正是如此,无论批评家们怎样批评苏轼的这些特点,苏轼之后,还是产生了大量成功的议论诗、哲理诗等。以苏诗为旗帜的宋诗主流,正是这样在唐诗“山重水复”之后,使诗歌的发展“柳暗花明”,而苏轼以议论驱遣意象的方式,以散文的方式、才学的方式做诗,也成为了宋诗及后来诗歌的主要艺术表达方式。
从以上诸章理论方面的探讨中,我们初步论证了苏轼“以文为诗”等诸特点,不仅仅是必然的产物,而且是必要的革新,它不仅不违背诗歌艺术的本质要求,而且还是对诗歌艺术领域的开拓。那么,既然苏诗的艺术成就如此辉煌、意义如此重大、影响如此深远,为什么会受到张戒、严羽以来的批评家们如此尖锐激烈的批判呢?这确实是一个中国诗史的司芬克斯之谜。要想解开这个千古之谜,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也非本书力所能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猜测。是否可以这样考虑: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苏诗的里程碑意义,正在于它不仅标志了宋诗的开端,而且揭开了诗歌新的历史时期的序幕。就是说,唐宋之分,不仅仅是两个朝代之分,而且是诗歌两个时期的重要分水岭。
是否可以这样说,以盛唐为代表的唐代诗歌,是古典诗歌的代表,它是自《诗经》以来的传统艺术方式的光辉总结;宋诗则是一个新历史时期的开端,它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并一直影响到现代诗歌的诞生。
这个时期与以盛唐为代表的前一个时期固然是有联系的整体,有着许多共性,但是,也应看到二者之间确实有着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称前者为古典时期,称后者为近代时期。
近代诗歌虽然保留了古典时期的某些形式,但确已开始具备了现代诗歌的许多要素。前者的内涵本质是言志抒情,后者则进一步增扩了“理”;前者的表演舞台主要在自然山水,后者则主要在世俗的社会生活;前者的主要艺术方式是传统的“比兴”、“意象”,从而创造了“物境”,后者则主要是“议论”,从而创造了“情境”;前者是诗人之诗,后者则是文人之诗、学者之诗;前者典雅端庄,后者则更追求散文化、通俗化;前者要求风雅比兴,要求反映重大的社会民生,后者则进一步增扩其娱乐性、游戏性以及文字的锻炼性等等。总之,二者确实是属于两个不同特质的艺术领域。
当然,两大历史时期特点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始终互寓互存的。笔者只是从总体上、本质上做粗略的划分。我们知道,任何划分都只能是相对的,因为事物之间总是充满着联系。诗史的进程也同样是一个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统一体。后期上升为主导地位的特质,在它的前期胚胎中其实早已出现了萌芽。但二者之间毕竟还是有着主导与非主导、本质与非本质之别。其中中唐晚唐可说是两个时期演变的中介。杜诗的锻炼性、议论性,韩诗的散文性、白居易的通俗性(甚至更早的王梵志的白话诗)、贾岛的锤炼性等等都可说是后一时期的滥觞。
可知,宋音之逐渐代替唐调,正是我国诗史内部矛盾的双方易位的结果,而近代时期批评界的反宋,也正是诗史的一种反思:人们期望回复到以盛唐为代表的古典时期,然而,诗史的车轮,毕竟还是按照苏、黄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着,因为,苏、黄的道路,代表了诗史前进的方向。朱自清先生说:
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输入了西洋的种种诗文观念。宋人的诗文分界说,特别是诗的观念,即使不和输入的诗文观念相合,也是相似的。
(《论〈以文为诗〉》)
苏诗的诸特点,无论是其议论性、散文性、哲理性,还是其才学性、文字性,都确实很有些现代人的味了。
苏诗以来的诗歌,日益向近、现代新诗迈进,这说明苏诗的出现,代表了诗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反映了我国古典诗歌日益向近、现代诗歌迈进的必然趋势。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新诗,一方面固然是“输入”的“西洋的种种诗之观念”所引起的革命,同时还应考虑到,它也是其内在矛盾斗争的产物。就是说,新诗也是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产物。而苏诗的意义,恰恰正是从古典诗歌向近、现代诗歌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质变点,一个中心枢纽。中国诗歌正是在这里结束了过去,走向了未来。
张戒、严羽等批评家们,还不可能摆脱时空的桎梏,他们还不可能俯瞰诗史变迁的长河,因而还在用古典时期的审美标准来要求新的历史时期的诗人。这是批评家们的悲剧所在。元好问说:“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而我们则可以借用其语而反用其意说:
谁说沧海横流尽,
李杜之后更苏黄。
来源:木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