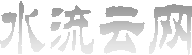木斋《苏东坡研究》
第四编 苏文研究
第十一章 “驰骋翰墨,其文一变”
苏文论
苏轼的诗词在中国诗词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他的“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等,开创了与唐诗抗衡的宋诗体制,他的豪放雅词的创立,则标志了词体进入了柳永之后的一个新时代。诗词方面的领异标新,足可堪称一个时代的开端。
苏轼在散文方面,丝毫不亚于他在诗词方面的成就。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散文数量大,体裁样式繁富,而且在于他在散文里表达了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表现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知识分子对于人生、社会、时代的富于哲理的深邃思考,表现了审美情趣方面由以客体为描摹对象,到以表现自我为中心的转移,表现了宋代以来由以追求奇险到转向追求平淡自然的这一带有近代审美心理的转变,也表现了文学日益向日常生活迈进的审美思潮,并由以上种种内在的变化引发体裁、题材、语言、表现手法等种种艺术形式方面的变化。
对于苏轼在中国散文史上的这种里程碑的地位,远的不必比较,只在所谓唐宋八大家作一鸟瞰就大致可知。而八大家中成就最高者,又可以进一步推出四大家,即韩、柳、欧、苏。此四大家可以说是删繁就简,领异标新,代表了唐宋散文时代的四座高峰。
李涂在《文章精义》中,对四大家曾有著名的比较,说是:“韩如海,浩瀚恢宏;柳如泉,澄澈隽永;欧如澜,容与闲逸;苏如潮,奔腾倾注,波澜层出。”这一比喻很形象,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不足。它只是形象地显现了几位大师的风格的某些方面。譬如说“韩如海”,只是指明了韩文浩瀚恢弘的气势,并未能指出他对奇险的审美追求,也未能指出他的古典主义风范。
若想探明每位散文大师的地位,首先应该把他们还回到散文史发展流变的长河里,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第一节 “吏部文章日月光”
韩文论
中国的散文,发展到韩、柳的古文运动时代,大致已经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这一点,只消探讨一下“古文运动”的内涵及其性质,就可得知。
所谓“古文运动”,是以恢复先秦两汉散文传统为旗帜,旨在反对六朝浮靡文风,提倡书写自由的散文革新运动。
陈幼石在《韩柳欧苏古文论》(P1)中,对于韩愈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作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归纳和表述:
首先他是一个划时代的文学理论家,他关于“道”、“文”(广义的文学)统一的学说,给曾经统治了几个纪的极端形式主义的骈体文敲起了丧钟,吹起了文学启蒙的新时代的号角。其次,他创造了一种散文体,这种文体他自己当时称为“古文”,而从此以后这种文体就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传统典籍中经典的正统的文体。第三,作为一个散文艺术家,他的主要贡献是把这种文体提高到真正的文学境界。在他之前,散文大都用于实际或功利的用途,自韩愈之后,散文就被公认为是一种文学形式,作家自觉地把散文当文学作品来写,批评家也自觉地把它当文学作品来批评。最后,即第四,在中国思想史上,他是孔学复兴运动的奠基者和倡导者,这个运动大盛于宋代理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范了此后中国文化的全貌。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以下推断,中国散文的历史,自先秦而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先秦两汉是真正意义上的“古文时期”,孔子的“辞达而已”是其旗帜,其文风也古朴,其宗旨在于实用和政治功利性,如所谓的“春秋笔法”,《史记》的“实录”精神等,都是明证。因此,中国的散文文学在此阶段,尚未实现其自身的审美境界。
六朝骈文的兴起,是对这种功利主义的一次反动。它由楚辞为滥觞,以汉赋为中介,至于六朝而大兴,“采俪竞繁,而兴寄都绝”。这一阶段,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天然的合理性,不能仅以“形式主义”目之。没有这个阶段的冲决,就没有以后韩、柳文,特别是欧、苏文的诞生。但是,六朝骈文在追求形式美、追求文学自由的道路上迷失了路径,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异化,他们为美而美,成为了一位只注重外在装饰而无内在修美的女性,从而失去了对于美的拥有。
韩、柳的古文,实质上是他们在新时代创造出的一种新文体,是可以比较自由地表现唐代士人生活、心态、思想的新文体,但他们要想获得成功,得到承认,并最终战胜时尚的、美丽的骈文,就势必要打出“复古”的旗号,试图将文学重新纳回“载道”的功利主义的战车。
就宏观而言,如果韩愈的散文不过是“载道”的工具,比之骈文的唯美追求,这将意味着某种倒退。然而,就韩柳的散文实践来看,并非如此;另一方面,韩、柳创造了一种散文体,却又命名为“古文”,这就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古典主义者,使他先天地有着学古、仿古的倾向。这样,“师古圣贤”和“务去陈言”就成为他的两大理论支柱,而“奇险”则成为他的散文实践的主要风格特征。这就会造成今与古、平与奇的内在矛盾。
譬如他的名作《平淮西碑》。此文为宪宗治下的著名的淮西战役而作,但韩愈却在文中故意贬低李〖的战功,因而最后以记述失实而被驳回。韩愈为此而受审,碑文被下令从碑上剔除,并命段文昌另撰新文。韩愈之所以会有失实方面的错谬,并非有意歪曲历史以邀宠于裴度。其中的隐衷就在于韩愈虽然是在记载现实,却要恪守儒家的传统风范。儒家碑铭的规则,按照汉代碑铭大师蔡邕的话来说,就是:
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记功,大夫称伐。
(蔡邕《铭论》,《后汉书》严可均编第74 卷P4-5)
所以,韩愈的这篇碑文首先要强调宪宗的“天子令德”,其次,就是记载相当于诸侯的宰相裴度的功绩,最后,才是相当于“大夫”的李〗的实际“称伐”活动。
虽然与事实颇多不合,但韩愈之文仍然不失为妙文。苏轼曾有诗为评:
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
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临江驿站小诗》
(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P22)
此事例极为典型地写照了韩文的历史地位及其内在的矛盾。这一内在的矛盾,必然地引发与外在形式方面的矛盾:韩愈一方面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范绍述墓志铭》见《韩昌黎文集P312》),另一方面,又要“师法古人”,所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李商隐《读韩碑》),写出“周《诰》、殷《盘》,诘曲聱牙”(《进学解》见《唐宋散文精选》P55)的仿古文字。
这是韩愈无法在自身体系中克服的矛盾。
第二节 “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柳文论
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二者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区别,这也合于事物的普遍规律。譬如花间派中的温、韦并称,他们的相同点使他们共同成为花间词的奠基者,但温代表了花间词的香软词风,韦则代表了源于早期文人词的风范。韩、柳并称,是因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和先秦诸子遗产中所提陈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共同核心的,同时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们也都对把古文作品凝聚为散文传统这一点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P84)
韩比柳虽然只小几岁,但柳的意义却更多地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理论方面,譬如在“道”的涵义方面,已有一些学者指出了柳的“文以明道”的“道”观与韩的道统观念之不同,指出他在《报崔黯秀才书》中的“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其内涵与韩愈的孔孟道统的不同,指出“文以明道”四字以柳宗元的思想体系来说,不在“道”而在“明”。“明”就是“澄清”、“阐明”,其目标是“定其是非”。柳不承认圣人有“道”的垄断权,而认为“道”是“为文者”的士大夫的共同目标,并指明柳之重“道”的自然和“道”在历史中的演绎变革。这样,柳的“道”的观念,就与韩愈的道统观念产生歧义,给古文领域带来了自由、解放的一面。
柳也同样指出学习《六经》的重要,这很容易让人感受到韩柳的共同之处,但柳的推崇《六经》,其着眼点更多在于现实,有些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古为今用”,或说是“六经注我”。他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著名论述: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中国历代散文选》P117)
从“本之”、“本之”、“参之”、“参之”的语式中,不难得出结论,学习《六经》,是为了服务于现实的创作,即“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这样,在柳的散文实践里,就少了韩的古典主义的风范,而更多地拥有了唐代中叶的现实生活,特别是更多地表现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的情趣、心态,从而标示了以后从苏轼到明小品到现代散文的发展脉胳。
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韩更多的意义是传统的结束,柳则更多地代表了未来。
柳的《永州八记》不仅仅是一种山水游记体式的奠定,而且我们能从“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倏而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的景物描绘中,感受到轻松的富有近现代气息的审美愉悦,能从景物中感受到作者主体的情感、心态。“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其中不仅仅在于人在景物中,而且,所有景语皆情语,其景其物,皆为从主体窗口透视熔炼后的自然。这种重“意”的品味,预示了苏轼及其以后审美思潮的趋向。
第三节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欧文论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韩、柳、欧、苏等唐宋八大家为一体,唐宋散文自然也应该是一个阶段,特别是明人茅坤编辑的文选以“唐宋八大家”为题,这一名称也就成为了一个至今不衰的概念。事实上,韩、柳文虽然在中唐时代取得极大的成功,但韩、柳特别是韩愈的身体力行的奇险高古的文风,不是一般士子所能效法的。因此,晚唐、五代直至欧阳修之前,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统治散文文坛的,实际上是所谓的“时文”。时文以唐代宫廷表章的“四六骈文”为源头,讲究词藻的华丽,因此,这一时期是可以视为韩柳与欧苏之间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从主流而言,是对韩、柳的反动,是对六朝骈文的发扬。当然,其中也有对韩、柳的继承,譬如时文讲究使用典故,就与韩愈古典主义有着某种血缘关系。
时文的势力还是很大的,譬如出于韩门的著名诗人李商隐,就是这种时文的大师之一,到了宋初文人手里,更发展成为尊李为鼻祖的“西昆体”。这种情形,一直到欧、梅的时代,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譬如,梅、欧作为主副考官,苏轼、苏辙兄弟等为考生的嘉〗二年的考试时,仍是追奇求险,“俪偶格律、绮缛淫靡”的文风为一时之风尚。欧、梅拔擢了苏轼等人,对这一风尚的扭转也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时,如同后来苏轼发现了陶潜,加以塑造一样,欧阳修从故纸堆中发现了快要被人遗忘的韩愈,从而开始了散文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对这种情况,欧阳修本人亦有描述: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 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 以礼部诗赋为事......因怪时人之不足道,而顾己亦未 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 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
(《记旧本韩文后》,《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十三》)
当然,欧对于韩,也并非只是“量”的延续与对沉寂的高扬,而是既有承续也有变革。与整个宋代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潮流相关,欧阳修变韩之“奇”、“险”而为“平”、“易”,即所谓的宋人变唐人的高山深谷而为平原旷野,使散文成为明白晓畅、平易近人,易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这一变革,正自欧始。
首先是关于道统与文统的问题。道统的观念,起于《孟子.尽心》所说,由尧、舜到汤、文王、孔子一个统序。韩愈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传焉。”(《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韩愈. 苏询卷P7)这就是韩愈等提出的“道统说”。 “道统说”实质上是汉民族的儒家政治、哲学代代承续而成一统的认识,此处之“道”,乃儒家之“道”也。此外,韩愈又在《送孟东野序》中从庄周、屈原到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到唐代陈子昂以下的作家勾出了一个文学的传统图,这就是以后所说的文统了。
在欧阳修的散文理论及实践中,比之前人的“载道”、“明道”的观念,又进一步强调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他提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的命题。这个命题,大致相若于现在强调文章首先要有思想、有内容,与韩愈的“气盛言宜”说有着一贯而下的关系,但从总体角度来说,又不同于韩愈将“文”视为“载道”的工具。欧只是说“道胜”才会“文至”,落足于文,韩则强调文学服务于儒家道统的功利目的。
同时,欧阳在此文中批判那些学道而溺于文的士子“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可知其所谓“道”的具体内容,是现实生活中的“百事”。这就与欧阳追求平淡的主张找到了内在的联系。
关于对平淡自然的推崇,更多的开始于梅尧臣的论诗,譬如著名的“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的论述。欧阳修亦引梅尧臣的话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以后至王安石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集》),就使平淡自然之美,成为北宋的一种思潮。
当然,“平淡”自然,也要注意防止“语涉浅俗而可笑”的弊病,如《六一诗话》引梅语:
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耳,而说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也。
从欧阳修的散文实践来看,一方面,他淡化了散文的“道统”面孔,而将目光更加关注于现实生活,其中可以有政治风云,也可以是山水景物,日常生活等等,从而使散文日益由社会关怀向自我关怀转化。
其次,他要将散文由韩文奇险的险峰深谷一变而为平原旷野,就要使散文具有一种摇曳畅达曲折之美,以弥补平淡的先天缺陷。
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对欧阳修的散文艺术特点与韩文作了一次比较性的论述:
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 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
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
执事之文,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 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 苦之态。
(《中国历代散文选》P218)
苏洵以一个大散文家的切身体会,指出欧文之变韩文之奇险万怪,而为“条达疏畅”、“容与闲易”,同时,又具有“纡馀委备,往复百折”的曲折摇曳之美。
譬如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
景〖三年(1036),范仲淹与权相吕夷简发生冲突,结果以范失败被贬放饶州结束,时任左司谏的高若讷趋炎附势,公然声称范当黜。欧阳修时任“馆客校勘”,出于义愤,写下此文。虽为义愤,起笔却从容忆旧:
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 识足下姓名。......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 不 知何如人也。
此为第一层,忆高对自己的第一印象,肯定中带有怀疑。
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 ...... 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
第二层,通过友人尹师鲁之口给予高度评价,虽然自己仍有疑惑。趋向是印象越来越好。
自足下为谏言来,始得相识。......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
(《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欧阳修卷P156)
此为第三层,将高若讷的评价提到最高点:“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但其中已是“绵里藏针”,只是说“论前世事”,那么,论及关系本人切身利益的当朝事又怎样呢,这就为下面的论述打下伏笔,断然推出“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决”字,更见出欧文的“急言竭论”的本色。
这篇文章本意在于批判高若讷,却以生平三次对高之印象,以“三疑”层层铺垫,将其置于最高点,然后陡然跌落,典型见出其“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之特色。
第四节 “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
苏轼的散文理论
苏轼的散文,正是由韩而欧这条线索中产生的重要一环,是这一发展潮流中的产物。他对韩、柳、欧,从理论到实践,都给予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
譬如在“道”的系统中,他是其中具有某种质的变化意义的一个阶段。许多学者指出了他由前人的“载道”、“明道”的正统而转上了崭新的“贯道”。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六篇)中首先指出:
三苏论文便与欧曾迥异。其所由不同之故,即在其 对文学的态度......盖道学家及柳穆欧曾诸人,其所以学古人者,乃所以求其道。即使于道无所得,表面上总 不敢象苏洵这样大胆地宣言为文而学文......所以孔孟荀扬韩诸人在道学家以之建立道统者,在他(洵)却以之建立文统......他只是论文的风格,不复论及文的内容......这便是三苏论文重要的地方。
明此,才可知三苏论文,本不重在道,即偶有言及 道者,其所谓道,也是道其所道;非惟不是道学家之所谓道,抑且不是柳穆欧曾诸人之所谓道。同一道的观念,在道学家说来觉得朽腐者,在古文家说来便化为奇。
又一步指出苏轼所论之“道”的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
东坡之所谓“道”,其性质盖通于艺,较之道学家 之所谓道,实更为解脱透达而微妙。
“道”已由儒家的政治的、哲学的“道”,改变为审美的、艺术的“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革。它标示了散文──这一中国最具传统、最为保守的文学体裁之一,也在日益从古典向近代演进,标示了由功利境界向审美境界的嬗变,标示了由客体关注到主体内心表现的潮流之所向。
在苏轼早期的论述中,譬如在《南行前集叙》及《凫绎先生诗集叙》等文中,苏轼还停留在欧阳修的时代,显示了他对师辈的一灯相传的关系。如: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 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於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
尝敢有作文之意。
(《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苏轼卷P746)
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 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苏轼卷P738)
要求文章要“有为而作”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必可以疗饥”,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这无疑是对六朝及宋初时文唯美主义倾向的宣言,其理论尚在功利也。
若看苏轼元丰时期以后的论述,则显然有着从“道”向“艺”的转变,更进一步来说,则如钱钟书所说:“在苏轼的艺术思想中,有一种从以艺术作为中心转变为以探讨艺术家气质为中心的倾向。”
试看其论: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 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 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 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
(《苏东坡全集》下册P359)
《答谢民师书》中的这段论述,表现了他反对雕琢,崇尚自然的观点,表现了他主张打破艺术格套,一切随表达事物的情况而变化的审美理想,所谓“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是也;所谓“文理自然”,就会自然而然地达到“恣态横生”是也。
在《文说》中,他进一步对自己的散文特质作了评价: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 虽日行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 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P114)
这些,无疑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第五节 “痛陈其胸前一片空阔了悟”
苏轼散文的艺术实践
从苏轼的散文实践情况来看,基本上表现了他的这些艺术主张。
首先是“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自由挥洒,不拘一格,对于传统形式的冲决与个人风格的建立。当然,对传统的破坏首先源于他对传统形式的精熟。在苏轼所受到的教育里,散文是他的第一课程。这首先是因为科举考试的原因。宋代科举已不是唐代的以诗可以考取进士的时代。科考的内容以文章为主,特别是谈史议政的论文,这是考取进士的铁门槛。苏洵虽为散文家,却终生蹉跎科场。这样,对苏轼兄弟这方面的训练,就成为最为重要的课程之一,苏轼在少年时的一些习作,甚至可以比肩于他成年以后的作品之。其次,苏洵以散文跻身于八大家之中,而很少赋诗填词,因此,这种专攻也势必对苏轼兄弟有着极大的影响。
苏轼青少年时写了不少这种论文,有相当一部分是泛泛而谈、大而无当的科场文字,显示了他当时所受战国纵横辩术之风的影响。苏轼自己后来也深以为悔:“向在科场时,不得已作应用文,不幸为人传写,深可羞愧”(《答刘巨济书》);“某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与王庠书》)。 其中,也有一些成功之作,表现了他推崇“贾谊陆贽之学”阶段的成果之作,当推作于嘉〖年间应制科时所作的《进策》,共为25篇。是一组有系统的宏文巨制,论述他对当时国家“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的政治观点。表现了他的散文艺术尚处于“社会关怀”的阶段,在艺术上则是陆、贾之风的延续。
随着苏轼科考时期的结束,随着他踏入仕途,走向社会,他的散文就日益显露他的“自我”个性,日益显示他对前人格套冲绝的本色。
从作于凤翔时期的《喜雨亭记》,到密州时期的《超然台记》,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代表。
“记”这种散文体裁,始于记事,春秋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本属应用文字,所谓“叙事识物”、“记事之文也”。《尚书.禹贡》篇一般被视为记体之祖。 汉代扬雄有《蜀记》,尚未具有记体的文体意义,至陶渊明有《桃花源记》,却实为诗序,尚非独立成篇之作。直到唐代韩柳的创作,记体散文方成一体。但也正如叶适所指出:“‘记’虽愈及宗元尤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其变态。”(《习学记言》卷四九)其中,又尤以苏轼为最。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苏轼记体散文数量最多,为63篇,比之韩、柳共计42篇的总和还要多出三分之一,体现了对于前人的飞跃;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发生了飞跃。
苏轼之前的记体散文,基本是叙事、写景、议论的三段论的模式。著名者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结构,首先交代作记缘由:“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属予作文以记之”;然后,描绘楼外景色:“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以寥寥数语交代而过:“前人之述备矣。”作者着重描写的是“迁客骚人”,“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因此,他着重描写由主体窗口透视出来的自然,描写作者或登临者所感受到的景物:“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之叹;描写“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愉悦;最后,更进一步推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哲理命题。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记体的另一名篇,表现了人回归自然的乐趣。但在总体格局上,仍然尚未脱离先叙事、次写景,后议论的唐人模式。
苏轼首先彻底突破模式,将叙述、描写、议论穿插运用,灵活多变。譬如《喜雨亭记》开端就议论:“亭以雨名,志喜也。”从“古者”“周公得禾”“汉武得鼎”说开去,意在说“喜”;第二段叙述“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再述:“既而弥月不雨”,分述“亭”、“雨”二字;第三段则将“喜”、“雨”、“亭”三字合一。结构如清代的吴楚材所析:“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写、合写、倒写、顺写、虚写、实写,即小见大,以无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穷,笔态轻举而荡漾,可谓极才人之雅致矣。”(《古文观止》卷十一)
其次,是苏轼散文内蕴的深刻。
如果说,《喜雨亭记》标志了对前人三段式模式的突破,作于密州时期的《超然台记》则标志了苏轼把深刻的哲理与浓郁的诗意融合在一起的独特风格。明人杨慎引:“吕雅山云:此篇不唯文思温润有余,而说安遇顺性之理,极为透脱,......真能超然物外者矣。”(《三苏文苑》)姜宝云:“此记有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脱出尘寰之外之意,故名之曰超然。此东坡之所以为东坡也。”茅坤也同时指出,此篇“与《凌虚台记》,并本之庄生。”这大概就是苏辙在为其兄所作《墓志铭》中所叙及其兄所受《庄子》影响的阶段了: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 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苏轼在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洗礼之后,又经历了黄州的贬谪生活,他的思想境界及散文的艺术境界,都发生了飞跃。他进一步由“对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了对内心世界的阐发,亦即由‘对人世的关注’转变为‘自我的抒解’”(崔承运《论苏轼的艺术哲学》北京大学学报1995.6.)。
从此,他的文、赋,旷达奔放,天马行空,壮浪纵姿、汪洋恣肆而又深寓他对人生、社会、时代的哲理思考,对生命本体意义的阐发,对生命情结的抒解。
写于乌台诗案前夕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表现了他在黄州之前的最高水平,表现了他对欧阳修曲折摇曳之美的发挥达到了极致。
这本是在极为悲痛心境下写的怀念表兄文与可的悼念文字,作者却以“‘笑’与‘哭’生游戏。”(明人杨慎语)曲曲折折,摇曳漾出。起首,平平淡淡论说了一段文与可的画竹理论: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蚹,
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 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 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 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 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
第二部分由画论自然引到与可的“画竹”,写出与可人品、画品之高,写出表兄弟之间诗画往返,失笑喷饭的往事:从与可的“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到苏轼答以:“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再到“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曲曲折折,细致婉曲地道出种种生活的细节。结处却以: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 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苏东坡全集》P369)
陡然跌落,戛然而止,令人笑未及掩口而悲已从中来矣。读者读至此处方知,前文一切笑谈皆为悲语也,作者本是睹物思人,“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却压抑沉痛,从种种快乐的往事回忆中娓娓道出。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是也。
代表苏轼散文的最高境界的作品,当属写于元丰五年(1082)的《赤壁赋》,此时距乌台诗案恰好三年,贬谪黄州也已两年半了。人在经历生、死一类的大的磨难之后,往往会引发对人生,特别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苏轼经历的乌台诗案百日,可以说时时都在死亡的门前徘徊,到黄州一段时间之后,“长江绕郭知鱼美”的风光时时抚慰他心灵的创伤。此时,痛定思痛、反思人生,面对长江风光与假想中的“一世之雄”,忽觉辩博无碍,达到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
作为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文人,大致会有几个方面的情结,需要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加以渲泄开释: 首先是作为一个社会上的人,建功立业的欲望,儒家式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之志,这种“趋优心理”,或说是忧患意识,是士大夫的基本精神品格。
其次,是文人作为在文化方面的角色,产生对文名的忧虑,希冀通过文学作品来达到生命的延续与声名的传播,所谓“文章千古事”,是也。
第三点,即是对生命短暂的无奈。此三点,就本质而言,可归结为两点,即一是客体的、外在的,用“功名”二字可以概括,二是主体的、内在的,是相对于“身外之物”的生命本身。
前、后《赤壁赋》的千古永存的艺术魅力,正在于他对这些哲学问题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它不同于以前的譬如《超然台记》等文章对人生哲理的理性认识,这是苏轼在经历一场生与死的磨难以后对人生、生命、功业的顿悟,是人生境界升华的产物,他将这种顿悟的深邃哲理与诗意的境界、无垠绵亘的时间长河,与浩渺茫然的空间四维,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获得了空前的艺术成功。
试看,在这篇名作中,人类个体在其中是何等的渺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然而,人类在浩茫宇宙中却又是主宰万物的主体:“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都是为“我”所“取”,为“我”所“用”:“而吾与子之所适。”
两赋中的景、物、人等一切物象,几乎都是含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从而构成了一幅具象而又抽象的画图。试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是何等美丽的情景,主客诵诗歌章,又是何等的欢愉,“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似乎这世界,这人生真是这样美好,这样无忧无虑。然而,这只是人类生命世界的表层现象,很快,这种欢愉就被客人的洞箫与客人的发论引入了悲哀的深层内心世界。
苏轼借对箫声的动人描写,将主客一同引领入另一个世界:“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此时,不惟“苏子惟然”,恐怕每位读之者也都要“正襟危坐”,为之动容了。
然后,作者借客之口阐发士人的悲哀。“客”既是一个客体,又是作者的一个化身,是另一个苏轼,或说是苏轼的另一个侧面。你可以考证出他是杨世昌,是位道士。但他实际上也是苏轼人生观念的另一个侧面。主客既是二,又是一,“客”的阐发不仅是他个人的思考,更是苏子的内心深处的忧虑与思考。主要内容有三:
一是“‘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二是当年曹孟德“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三是“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而“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羽化登仙”的梦想终不可得,故而“托遗响于悲风”,排遣出一番心胸的郁闷。此三点,恰恰是古代知识分子人生观的最根本性的忧虑。即对功业、文名与生命短暂的迷惘。而苏轼经历了对生命理想幻灭的切身体验,故尤为深切,而于文赋之中写出诗境、理境。
如果说,客人的悲哀,代表了苏子在诗案前后的灰暗心境,是从前之我,而苏子的正面阐发人生妙理,则代表了他对生命、功业认识的升华,是今日之我,是面对此时长江万顷,清风明月而胸中一片了悟的“自我”。这种了悟的核心,就是要享受生命。使生命与整个自然、整个宇宙结为一体,从而得到“无尽”。
首先以水、月为譬喻:水不断失去,但又并未失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月似乎不断盈、虚消长,其实也并未消减:“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这就要看你是从“变”与“不变”的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从变的角度来看,则生命、万物都是短暂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若从“不变”的眼光审视世界,则生命与万物在世界里都得到了永恒:“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正如水与月一样,水似乎每天、每时都在不断地失去,但是江河作为一个总体,却依然存在,而且似乎是永恒的存在;月也在不断地盈虚消长,似乎今日之月明日就不复存在了,但月还是永恒地照耀在天空。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个体的生命,自其诞生起,就已经开始了向死亡的倒计时,死亡是他必然的归宿,就象水的流逝与月的盈虚,但人类作为总体,却生生不息地繁衍着,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其中的链条,他的肉体、精神作为某种物质,就成为了永恒的存在,就如同不停流逝的水与不停盈虚的月一样。这就是苏轼对生命的深沉思考所给予我们的启迪。
而这种深刻的哲理,却是以高妙的艺术手法写出的。清人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五评:“游赤壁,受用现今无边风月,乃是此老一生本领,却因平平写不出来,故特借洞箫呜咽,忽然从曹公发议,然后接口一句喝倒,痛陈其胸前一片空阔了悟,妙甚。”
清人余诚《重订古义释义新编》卷八:“起首一段,就风月上写游赤壁情景,原自含共适之意。入后从渺渺予怀,引出客箫,复从客箫借吊古意,发出物我皆无尽的大道理。......而平日一肚皮不合时宜都消归乌有,那复有人世兴衰成败在其意中。游览,一小事耳,发出这等大道理。遂堪不朽。”
今人郭预衡先生则从散文史的宏观角度,论述了《赤壁赋》的艺术价值及其地位:
苏轼写得自由随便的作品,还有赋体之文。两篇《赤壁赋》都打破了赋之常体,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可以说是游记,也可以说是杂文。其中有叙事,有抒情,有问答,有议论,而且或韵,或散,不拘格套,既不同于骚体,也不同于俳体。......这样的文章发展下去,就是明代公安派的小品文了。
(《中国散文史》中)
此等文字,不仅是对传统的总结与发扬,而且是宣示了一个新的散文时代的到来,不仅寓含了深邃的哲理,而且对散文体裁的艺术形式方面,给予了从结构到语言诸方面的冲决,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故其弟苏辙的感觉是对的:
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
(《东坡先生墓志铭》)
不仅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感到“瞠然不能及”,而且令一切后来者感到难以为继:苏轼已经超越了八大家的群体,成为下一个散文时代的开山。
来源:木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