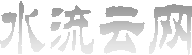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
孙基林 ◇
中国第三代诗歌后现代倾向的观察
这个世界并非总是如人们所预置或愿望的那样,按照某种观念亦或假定的逻辑,不言自明地成为现实。相反,它充满着诸多偶然性、不定性甚至难以预期的非理性机缘。直至在某一天,它会不期然地降临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生命中一片陌生乃至不情愿面对的奇异所在。后现代主义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所在,一个精灵,它让你不得不面对它,却又让你难以进入它、接纳它。它的命运与你的命运共同遭遇在这个时代,你又能作何种言说呢?
事实就是这样不容置疑:我们无法拒绝后现代主义的侵入。诚然,我们的社会形态并没有进入如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但是,后工业社会形态绝不是后现代性的唯一理由。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在产生着某些后现代因素,比如经济形态、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呈现出的多元拼贴性,非中心化观念形态特点等等。而且,在80年代的中国社会,也确有一种新的情感和文化因子在悄然滋长。正如每一位历经文化大变革的当代美国人都不会忘记60年代一样,当今的中国青年又有哪个能忘记80年代的文化变革呢!《伊甸园之门》的作者曾这样描述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个夜晚的情景:当美国著名的摇滚歌星迪伦以他那吵哑、咆哮而又哀鸣的声音,“演唱了其最佳新作中的一首《永远年轻》时,时间好象停止了。音乐会接近尾声时,全场到处亮起了火柴和打火机——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不朽点燃了一支蜡烛——随着迪伦演唱《象一块滚石》,彬彬有礼的人群怀着同代人团结一心的激情向前涌去。……人们沉浸在一片狂热中,经历了一次罕见的充满自发激情的时刻。”①我们这一代中国青年是否也曾经历过“一次罕见的充满自发激情的时刻”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在80年代中期,同样也是一个夜晚,地点是北京的首都体育馆,当万人合着崔健那同样嘶哑、咆哮而又哀鸣的声音齐声高唱《一无所有》时,此情此景,恐怕也不亚于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那个夜晚。这就是一代新文化人的狂热。这种新的情感、新的感性运动,在美国,酿成了漫延整个世界的反文化的后现代风潮;而在中国,一种带有后现代倾向的新文化和新情感同样也在四处弥漫。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后现代批评家们开始注意到中国实验文学的后现代因素,但不无遗憾的是,第三代诗歌的后现代倾向,却始终未在后现代权力话语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这里仅陈述一点个人的观察,对此作些初步的探索和阐释。
反文化:第三代诗歌的缘起
反文化,或许是主流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所特有的价值指涉。任何文化,都是人类既有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确定性形态和秩序,它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到特定阶段时仅存的硕果。作为精神形态的文化,它潜在地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等。卡西尔把人定义为“文化的动物”,意在阐明生存在文化之中的人所必然具有的文化本性。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原则,科恩的“社会个体”概念,旨在强调人的文化归属性。就如先锋诗人蓝马所说:“现代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传统的模具中‘成长壮大’的。受到‘文化的预制作用’的严重影响,现代人在来不及自己处理自己之前,毫无疑问地就已经被‘订做’成了地地道道的传统的人了。”
②由此可见,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份世界,原来早已是被文化、理性秩序化、绝对化、中心化了的宇宙程式,个性乃至生命都只能在被置放的那个位置上,执行着文化所规定、所赋予的那部分功能。因此,任何渴望生命的自由及创造性的边缘人,都将必然地反抗作为权力话语中心的传统文化。美国60年代兴起的“新感性”运动,就是这种“反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由此带来了生活方式、美学观念及艺术形式的根本变革。如果说早在30年代的达达主义者,此类反叛行为还只是在较小的圈子内弥散,那么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则已成为整个社会普遍滋长的情绪和行为。他们不仅反抗传统文化、现实文化,而且也反抗使这种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现行体制及一切表现形式,这自然也包括美与艺术。就如马尔库塞所言:“今天对现存现实文化的反抗,同样还反抗着这种文化中的美,反抗着这个现实文化中所有过于升华、分割、有序、和谐的形式。今天的反抗中对自由的渴望,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这就是一种在方法上的反升华。”③于是,反升华、反超越、反英雄、反高雅、反理性就成了这场反抗运动最为直接、日常而平凡的生命姿式。嘻皮士式的亚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颠倒杂乱、大哭大叫的黑人音乐,披头士飘举的长发,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以及垮掉派诗歌、黑色幽默小说等,都参与了这场旨在颠覆和反抗文化的“新感性运动”。它主张生活本身即艺术,因而它无限量地释放马尔库塞所谓爱欲潜能及感官享乐情绪,重体验、重感性,反解释、反智性。正如桑塔格所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艺术的生活欲望,而不是艺术的阐释学。”④在她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逃避解释”,这与现代艺术总指涉一种隐于字词背后的意义,因而必须得到解释与理解不同,后现代主义不指涉什么,它仅仅是生命的直接体验本身。而阐释必然会把人导向抽象的智性层面或既定的文化语义,这与生命不相连属。因而,重生命、重体验,反理性、反形而上学、反文化就必然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标识。
当80年代的中国,在经济生活还相对贫弱的土壤上,却渐次生长出这种反文化的后现代观念形态时,我们确乎为之惊异。当然,我们不会将此简单地归因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所致,也不会把美国60年代文化看作这种反文化倾向的直接背景。事实上,它是在一种相对隔绝的情况下产生的,就如当年李亚伟及莽汉主义者并不知晓美国有金丝伯格和嚎叫派诗歌那样;韩东在写作《有关大雁塔》时,恐怕也并非模写美国反文化运动的精典文本:“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诗人显然是拒绝文化,拒绝解释,并从根本上消解大雁塔背后所指涉的文化语义,而将此还原为一个有一定高度的物体,我们登上去,只不过亲身体验一下观览四周风景的心境而已。这无疑表现了一种重感受、重体验,反解释、反文化的叛逆姿态。至于这种姿态的最初动因,应该说首先是基于诗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堪重负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当时文化寻根诗盲目归趋的一种反拨,当然也与诗人生命意识和诗歌本体意识的觉醒有关,由此便进一步产生了对历史与文化的深深怀疑及反抗情绪。诗人们后来之所以能够自觉地接受或表现出某些后现代倾向,我想大概是与这种新的感性基础分不开的。⑤揭示或呈现存在的后现代倾向
生命与诗歌本体意识的觉醒同对文化的怀疑几乎是同步共生的。当朦胧诗人个人意识的觉醒最终导向一种认识论或主体性时,后期朦胧诗人又将个人纳入一种文化或传统的既定秩序之中。这时,新一代的先锋诗人们便预感到一种危机,一种“存在无异于失去”的个人生命与诗歌本体意识的危机。于是,便纷纷寻找某种可能的语言实体,寻找那个“不变形”的本来世界,企图“归真返朴”到所谓“前文化”之中。因为只有这个“永远不被文化的世界”,才是真正的生命和诗歌本真的栖息之所。这时,文化、生命和语言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已成为第三代诗歌冲突的核心。在诗坛呈现出短暂的对抗状态之后,许多诗人便一古脑儿弃绝了文化,而回到生命与语言的原生之乡,并在此达成了生命与语言的同构共生性。
生命意识的觉醒即是以揭示或显现本真的生命状态为旨归的,这是第三代诗的基本走势之一。在他们的诗中,我们随处都可能感受到原初的生命存在状态或行为过程,它是对“自在”生命、事物及其姿势的一次发现、揭示和命名。它通过生命瞬间感觉或行为过程的显现与描述,将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以及常人难以发见的隐秘揭示、显现给人们。在此过程中,第三代诗学始终在企图确认一种关于“事物”本身的思想方法,即事物就是事物。人作为能感觉的客体,只不过与事物同在而已。这种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倾向,表现出客观事物存有的“自在性”观念,它在那里存在着,自身显现着自身,自身表现着自身,就如于小韦笔下“不断向前”的那列火车:“它走着/象一列火车那样。”我们再也无须寻索事物背后那隐藏的意义或认识论“自我”,因为这个“自我”已悄然远逝了,置身面前的只是一些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甚至包括“我”在内,也不过是一个与万事万物平等共存在那里的“物”。他们不仅仅“以物观物”,而且还要“以物观我”,“我”自然被消解在这一片物的世界之中。
随着物的“自在性”而来的,便是它的“此在性”,就如诗人本身一样,他也是一个在此时此地存在着的生命体,“此时此地”是他安身立命的生命之源、存在之根。正如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韩东所说:“那怕是你经历过的时间,它一旦过去,也就成了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了……”⑥历史的“‘根’是没有的。这是对往事的幻觉,一种解释方式。对未来,我们真的一无所有。”⑦“此在性”不仅指时间上的,而且也是空间上的,即“现时”的“在”与“现地”的“在”。这种“现在感”与“此岸感”,具体表现为一种生命的“过程意识”。在历史上,大凡宗教文化或理性精神居主导地位的时代,诸如此岸/彼岸、现实/历史、现在/未来、感性/理性等二元对立的哲学文化概念,前者均被视为即将过去的短暂过程,扮演着地地道道的灰姑娘角色。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生的哲学”、过程哲学,它标志着一个新的价值时代的开始。尤其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更是视人生存在的过程为生命的本质意义。“存在”一词,按本义解释,即指“突然冒出来或走出来”的意思,这实际上是指一种短暂的瞬间即失的过程。存在哲学家们真正唤醒了人的本真的生命意识---一切都将逝去,不存在任何永恒超验的生命形式。生命真正地存在于他“现在”的感觉及行动中,无数瞬间即逝的过程构成了真实的人生,所谓“存在主义”,也即“过程主义”。与这种生命过程论哲学相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与文学艺术,也愈来愈注重过程⑧,从而使艺术诗学由哲学认识论的阐释学变为生命过程的本体论。第三代诗学同样与这种世界性的过程哲学和生命本体论诗学相呼应,表现了一种注重“此在性”的过程意识和生命本体论观念。当然,这与中国独特的历史人文背景也不无关涉。长时期以来,似乎我们的生命始终深陷于对过去与未来的双重幻觉之中,既失却了“此在性”作为根性,只好别无选择地被抛置在无时空凭附的荒原之上,这显然是一种虚假的生命状态、病态的心理范式。第三代诗人毅然告别了“在某个时代(往昔的或未来的)、某个不为人所知的地点存在着的某种‘美好的日子’”,而回到今生今世“只有一次的人生”⑨,回到“此在”的生命过程之中。正如于坚《在旅途中不要错过机会》所告诫的那样:“假如你路过一片树林/你要去林子里躺上一阵
望望天空/假如你碰到一个生人/你要找个借口 问问路
和他聊聊”,因为你只有抓住眼下每一个可供感觉栖息的时刻,才能真正去体验“此时此地”的生命过程和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之旅。
美国著名的后现代文艺思想家威廉·斯潘诺斯(William
V·Spanos),曾于70年代提出了存在主义的后现代诗学概念。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最早应追溯到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释学,更是成了他存在主义后现代诗学的基石。海德格尔现象学认为:“现象”意指“在自身中显现自身的东西”,其中“在……中”充分表明现象原是从自身存在的潜在状态中“被揭示或呈现出来”⑩。尽管这种“被揭示或呈现出来”的存在的潜在状态,在斯潘诺斯的后现代话语中被称作“解释”的结果,但这种“解释”已与传统的阐释学有了根本的分野。因为这种现象学的阐释学不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本体论的:“此在”要被当作“存在”(Sein)的显现自身来观照,而“存在”又是一切事物的存在之因。所以,这种现象学的“理解”不再是一种认识方法,而是“存在”的存在方式本身。海德格尔这种以语言显现生存的结构方式,似乎称作“生存现象学描述”更为恰切。面对这种描述而显现的生存现象或某种潜在状态,已经没有必要甚至也不可能象现代主义者那样去寻求描述背后所谓“未变更的绝对意义”了。因为它期待你的不再是阐释和追寻,而是生命的感受形式;不再是认识论的或形而上的概念,而是本体论的生命体验过程。存在主义的后现代诗学既然是一种生命过程本体论,“瞬间过程”在本体论上居于优越位置,那么,它对行动和过程的强调自然就大大高于某种形而上意义的符号形式或终极结果。在这种意义上说,它又是行动本体和过程本体。而作者作为文学本体之维,他本人已从“世人的瞩目中悄然隐退。他在无比消极冷漠的距离之中,在一种客观性的呈示之中,漠然地修剪他的指甲”⑾。这种“客观性的呈示”,表明作为本体之维的作者,已不再是那种全知全能的“明察秋毫者”,居高临下的创世“超人”和“训诫者”,作者已失去了主体性权力地位,而变成一个与其它任何平凡之人一样,存在于这个同样日常平凡的世界之中,他与生命过程及行为同在,与日常感觉及客观存在着的物同在。由此可见,第三代诗人的“自在性”或客观性显现、“此在性”的存在状态和生命过程意识,无疑与斯潘诺斯的存在主义后现代诗学倾向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相似性。
当然,我们也不会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差异性,比如,斯潘诺斯尤其强调文学与世界的历史性对话,因此“历史意识”就成了他后现代诗学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他把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等排除在他的后现代范围之外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新小说”和反文化运动完全与历史无关,是一种“超越历史的取向”,“结果,后现代主义文学想象最初的冲动的存在主义源头便黯然失色了,这样也就危及到二次大战后的冲动……即试图使文学代表现代人的真正历史意识的恢复介入世界的本体论对话”⑿。在斯潘诺斯看来,后现代作家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无论他说些什么,他都在与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话,并且烙上文化的印记,受其历史条件所决定所制约⒀。尽管斯潘诺斯所谓“真正历史意识”,始终与当下现实和个人的生命存在紧紧相连,但与新小说和反文化艺术拒绝历史深度的后现代倾向还是有着不同的质素。正是这一点,第三代诗学与存在主义的后现代观念产生了分歧,斯潘诺斯所拒绝的文学形态和诗学观念,第三代诗歌却恰恰给予了相当的认同。比如杨黎给新小说派大师罗伯·格里耶的献词《冷风景》一诗,就明显地表现出与法国新小说相类似的客观倾向;而那种拒绝意义、拒绝解释、拒绝任何深度神话的反文化诗学,更是第三代诗歌所遵循的基本走势。其中,对历史意识的消解和拒绝,显然构成了第三代诗歌反文化、反传统的最初动因,而韩东那首著名的《有关大雁塔》,就是拒绝和消解历史意识的范型作品。或许历史的重负对这一代人来说显得过于沉重,新一代诗人便纷纷从历史的生存范式中回到“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时间流转一体的整体感消失了、断裂了,人们开始获得了一种只关注当下体验的时间意识。由此可看到,第三代诗学一方面受到了海德格尔、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纳了被人们称作反文化、反历史的某些后现代观念。在斯潘诺斯的后现代概念里,两者本来是截然异趣、水火不溶的诗学思想,但在第三代诗学中却达成了整然化一的融合,表现出独具特色的“揭示或呈现存在的后现代倾向”。
文化或符号解构的后现代倾向
后结构主义是西方后现代主义重要的思想基础,其中尤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后现代艺术影响最大。所谓“解构”,自然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的。结构性、整体性、中心化是结构主义的核心之所在,它认为,就文学对象而言,整个系统结构是单个作品意义的根据或来源,而单个作品又是一个系统、一个结构、一个整体,它始终有一个意义中心在统摄、支配着每一个组成部分,各个部分只是和谐地联系着,成为这个意义中心的影像或折光。恰恰相反,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却彻底否认文学作品存在着任何内在结构或中心,他认为作品本文就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它既没有什么确定性意义,也无终极意义。对此,巴尔特曾有一个形象的描述,他说文学作品就象一棵葱头,从表面上看来它似乎是统一的,其实它有许多层构成,里边到头来并没有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原⒁。为此,解构主义者常常面对传统的本文,通过拆解、颠覆所谓的“系统性结构”,或揭示内在结构存在着的矛盾性、差异性,从而消解其中心意义,呈现出本文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特征。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典籍那无标符、无句逗的耗散结构形态,应是解构主义者理想的范型本文,比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然而,这在传统阐释学的经典释义中,却被给出了一个所谓本原的终极的确定性意义,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面对范型本文及其确定性结构,“非非主义”诗人周伦佑曾经进行过较为典型的解构式操作实验,他在大型组诗《自由方块》中曾这样写道:“---可以这样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这样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这样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这样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当然还可以再解。作者通过反复移植句逗的位置,使其本来就弥散不定的语词在一次次的重组中,呈现出意义的游移性和不定性,从而还原和揭示了经典本文的非确定性和多义性的存在状态,并且从根本上消解了所谓的“系统性结构”以及传统阐释中的确定性意义。这种写作方式的另一种效应,还在于消泯了传统观念中不同文体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使诗体写作事实上已成为一种消解式批评,这同样也是典型的后现代特征之一。
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时,曾以“词义向心说”(logocentrism)这一概念,指称和描述自古至今所产生的一切思想方式。他认为:“以柏拉图为最先范例的西方哲学,一般都以这么一种假设为前提,即语言是从属于语言以外的某种观念、意图或所指的”。⒂因而,作为“媒介”的语言,总是被当作某种东西的传播工具,这种东西既与它分离却又从外面制约着它。不仅西方的语言观念如此,中国的语言观念也同样具有这种“词义向心说”的倾向,如“文以载道”说,即是将语言和文学形式作为某种封建道统的传播工具而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可说将这一观念凝定为一种形而上的概念形态,因为符号概念本身,说到底就是一种结构、一个统一体,按照传统观点,符号就是一种观念或东西的工具或替代物,尤其当它一旦被分解成能指和所指时,能指就必然地成了所指的替代。因此,在符号学观念看来,文学作品本文的形式和语言,一定是指向它本身之外的某种观念或某个东西的,这显然与德里达所谓“文本以外不存在任何其它东西”或“不存在什么外部的文本”之类思想相抵触。因而,以消解本文之外的意义为目的、对符号结构的拆解与颠覆,或者如弗·杰姆逊所说符号学深度模式的削平与抛弃⒃,就必然地具有了解构主义的后现代倾向。第三代诗歌对符号结构所进行的消解式实验,就是这一后现代倾向的基本表现形态。要指出的是,这一实验绐终是与文化的消解这一根本目的息息相关的。对文化的怀疑必然导致对文本之外的意义的怀疑和清算,于是诗人们便纷纷弃绝思想、弃绝意义而回归本体,回到语言和生命。这一步实验以净化、纯化语言开始,结果淡化了文化对诗歌本体的干预和渗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消解文化的目的。当然,若从符号角度分析,这种回归语言的实验,主要是以清除、弃绝语言之外负载的文化价值因素为旨归,从而中断了语符中能指与所指系统的必然关联,甚至抛弃了表现深度的所指而回到能指本身,就如韩东笔下的“大雁塔”,已消解了它与传统历史文化的某种象征或隐喻性关联而回到自身一样。当然,即便如此,它依然在执行着一部分符号功能。对此进行更进一步实验甚至彻底解构和颠覆符号学深度模式的要算是“非非主义”的代表诗人和理论家,比如周伦佑、蓝马。在他们的诗学观念里,语言不仅往往负荷着它自身之外的某些文化价值因素,即使它本身,依然体现着或代表着某种文化价值形态,尤其那些形容词,如伟大、崇高、光荣之类,本身就是某类深度和文化价值的评判者、所有者。因而,他们要彻底反文化、反价值,自然就必须彻底解构和颠覆语言符号,弃绝所指甚至能指,淡化和抛置形容词,解构、颠倒或重新组合新的语言关系,甚至自铸新词,以便真正解除有效的文化语义运动,使之发生偏离、中止和丧失,最终产生他们所谓“超语义”的“语晕”现象⒄。这或许就是他们到达真正的生命栖息之地----“前文化世界”的必由之径。比如作为诗人兼理论家的蓝马,他在《九月的情绪》一组诗中,一再向世界裸露出无色透明的“白”来,不仅仅是雪山、白云、大海、阳光……即使“鸟”,也是“看不见各种颜色的鸟”;而“晚风”呢?更是“行星上一无所有/树梢上一无所有”。他似乎要在解构符号的所指、掏空事物的意义之后,将整外世界真正还原到单纯、透明的“前文化”之中。再如他的《世的界》、《的门》等一类作品,同样进行了更为彻底的符号学解构式实验,甚至标题都已拆解成符号的碎片,不仅所指已消失,能指也随字词的溃散而终被消解。
当然,这种实验似乎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种困境始终是与诗人的语言历险分不开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真正地面对实验,只有它,才能充分揭示生命的自由和诗歌的创造性意义。这也是我们从第三代诗歌不断拓展可能性的实验中所获得的启示。
1993、5
注:
①Morris Dickstein著《伊甸园之门——美国六十年代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86页。
②蓝马《走向迷失》,见《作家》1990年第10期。
③马尔库塞《审美之维》127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④引自佛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19页。
⑤可参阅拙作《文化的消解:第三代诗的意义》,见《青年思想家》1990年第6期。
⑥见《诗刊·青春诗话》,1985年第9期。
⑦引自韩东给作者的一则诗话。
⑧参阅滕守尧《走向“过程”的现代美学与艺术》,见《上海文学》1987年第2期。
⑨于坚语。参见《当代青年》1988年6期。
⑩参见王岳川《后现代主义诗学品格》,载《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1期。
⑾斯潘诺斯语。转引自王岳川《后现代主义诗学品格》。
⑿引自王宁等译《走向后现代主义》,25页。
⒀参阅王岳川
、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250页。
⒁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7月版,159—160页。
⒂安纳·杰弗森等著,陈昭全等译《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版,122—123页。
⒃参阅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8月版,162页。
⒄蓝马《语言革命——超文化》,见《百家》1988年2期。
【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