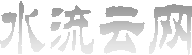木斋《苏东坡研究》
第二编 苏词研究
第三章 “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 -- 苏轼“雅词”论
对苏词的评价,或称其“豪放”,或称其“婉约”,而对其影响,也多认为直至辛出,才有回响。而“豪放”词派,相对于“婉约”正宗而言,只是一个偏支。这似乎是一个奇特的斯芬克思之谜,即一方面苏轼为两宋词坛之重镇,一方面又未能将他列入宗主的位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囿于传统的“豪放”、“婉约”之论。
笔者认为,苏词的本质意义是他以“雅”实现了对“俗”的改造,并确立了苏轼之后词雅化的基本走向。对此,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予以青目。如秦寰明《宋诗的复雅崇格倾向》(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4.)论述了宋人在诗域里的雅化;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也对苏、周、李等词的“雅”化予与述及。但对两宋词特别是苏词雅化问题的全面论述,尚未得拜读。
鉴于“豪放”、“婉约”之说,统治了中国学坛长达数百年之久,笔者将首先论证东坡词的本质是“雅词”,是他以雅词对俗词的改造;再论述雅词与豪放词的关系,并以“豪放雅词”总名之;最后,再论及他的“婉约雅词”。
第一节 “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
苏词的本质是对词的雅化
一、苏词的本质是对词的雅化
如果能抛开传统的“豪放” 、“婉约”之分,而以“雅”、 “俗”的更高一个层次的矛盾范畴来审视词史长河的变迁, 当会豁然醒目地看到,苏前苏后之词,并非“婉约”的铁板一块。柳词与晏欧词不同,秦、周、姜、吴等与柳词及晏欧词也不同,虽然他们被区分在“婉约”的同一个派系里。应该说,词体自其出生时起,就开始了“俗”与“雅”之间的消长演进。
词产生于花间樽前,诞生于歌伎乐舞的母体里,诞生在一个日益走向近世文化的时代。这就使词先天地具有了“俗”的属性。滥觞时期的词体民歌,散发着浓郁的“俗”的气味。随后的文人词,虽然是在仿效民间词作,却也对民间词风自然地进行“雅”对“俗”的改造。他们或吟咏江南美景,或歌咏归隐高蹈。词当此时,尚未成为“艳料”之专利。温飞卿与花间词的出现,标志了词体的真正诞生。他们以文人身份而倾力于词,实现了上述两个源头的一次小的整合。但却以民间词之“俗”为父,而以文人词之“雅”为母,温为正而韦为副。奠定了词为艳科,香软柔媚的基调。
南唐冯延巳、李后主为代表的词以及柳永之前的晏欧词应该说比之花间词之俗是一次小小的雅的反拨。其中李后主遭家国之变,因而写出“以血书者”之作,是词史流变历程中的意外事件。如无社会特殊事件的外力,则此时期词当如冯延巳之作。故论者多指出其对苏以后词之影响。如王国维评其“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龙榆生认为冯“影响北宋诸家尤巨”。(《唐宋名家词选》)吴梅认为南唐词人“不独为苏黄秦柳之开山,即宣和绍兴之盛,皆兆于此矣”。(《词学通论》)此三论有过奖之嫌,而本质意思将南唐词风视为两宋雅词之先驱,则无疑是对的。而其地位之推许,移至苏词,庶几近乎?
柳词、苏词的出现,是北宋词史上的两次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都是渊源有自的。柳永实质是温飞卿的继续和发展:温、柳其人,都是传统道德的叛逆者,温、柳其词都以艳情为第一主题,柳比之温,走得更远。从做人来说,温被说成是“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柳则主动向传统宣战,有着由被动到主动的变化。从作词来说,温笔下的还是贵族女性,而柳已把市井歌伎作为第一描写对象,写出了富于市井情趣的词作,从而标志了近世文化的发轫。柳永及其词作,在中国文化由古典向近现代演进的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意义非在“婉约”而在具有近世文化的某些特征。但近世文化的嬗变,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范畴,故柳词的意义及其影响要在元明清的曲中显现,并远远地辐射到五四时期的现代通俗文化。如况周颐所指出:柳词“为金元已还乐语所自出”(《蕙风词话》)。总之,柳词上承敦煌曲词,下开金元曲子,这应是对柳词地位的正确评价。
苏词的意义,从本质来说,是对柳永俗词的反拨,并奠基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雅文化的殿堂。与其说,豪放的风格是苏词的贡献,勿宁说是苏轼将以柳永为代表的娱宾遣兴、倚红偎翠为格调的俗词注入了文人高雅的品格,特别是注入了东坡式的超旷、飘逸、野性、哲理,注入了词人自我的思想情趣和精神节操,从而使词体从“词语尘下”情调卑俗的里巷青楼,勒回到高雅的士大夫胸襟怀抱。而这种雅的品格,在词史发展中,尚属一种新兴的、极具发展潜力的因素,并深深契合着时代的审美思潮。这就是苏轼之所以能成为苏轼,苏词之所以为两宋词史流变之枢纽地位的原因。
二、“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
况周颐对苏轼词的雅化,曾有明确论述:“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惠风词话》)明确标举了苏轼在词艺中“提倡风雅”与“为一代山斗”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资料中,很难查到苏轼对“提倡风雅”的理论阐述,但从苏轼自身的美学思想、苏词的构成、以及后人的评论中我们仍可缕析出苏轼在词艺中对雅趣的追求。
在苏轼的美学思想体系里,存在着对柳永“从俗”倾向的批判意识,并有意识地欲建立与之抗衡的“虽无柳七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的词,而这种词不是用“豪放”所能概括得了的,它应是一个比“豪放”风格更高更大一些的概念。这就是“雅”。
在有关苏轼“豪放”和“以诗为词”的几个经典性资料里,我们应该不仅如前人那样,能看到苏轼对“豪放”词风的追求,更应能看到他对“雅”格的追寻。苏轼批评秦观“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以“某虽不学,亦不至是”。东坡指出其词句:“‘销魂当此际’,非柳七句法乎?”(参见《花庵词选》卷二)此段资料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明确标示了苏与柳的对垒意识,与问幕士“我词比柳七如何”的资料可相对照;二是秦观否定自己学柳,透露了秦观在总体上亦即在“雅”与“俗”的分野上,还是从苏而不学柳的。这一点很容易为后人所忽略;三是苏所指摘的学柳之句是“销魂当此际”,此五字之下还应包括:“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悻名存。”此五字连带以下数句是典型的柳词风味:男女艳情,情调趋俗,手法直露。当然,秦观此词还是相当精彩的,如“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等均饶有情致。东坡举“销魂”五字而未及其他,说明并不是以“豪放”而反对其“婉约”,而是在以“雅”来批评他此词其中的“俗”。这一点读者可细细体味。
苏轼另有一次读秦观的《水龙吟》中的“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批评说:“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
(俞文豹《吹剑录》)案此两句少游是学柳的铺叙手法,而此种铺叙手法近似民间风味。以后的戏曲,小说多用之。其特点是不似传统小令或唐诗那种精炼含蓄的手法,而是展开铺排,因而明白晓畅。这正是从手法上的一种近俗表现。此段资料说明了苏轼对学柳不仅从格调上批评,而且也从艺术手法上加以批评。
此外,关于苏轼赞赏“以诗入词”的资料也很多,兹举二例:
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
(《与陈季常书》)
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
(《与蔡景繁书》)
可知,苏轼是将词视为诗之一种,从而要打乱原先已经界定的诗词分工。
三、苏轼提倡“风雅”的内涵
诗自三百篇以来,一向以“雅”为正声,而以“郑”(俗)为亡国之音。即便在诗中已经有了的情爱之作,也被训释为比兴寄托。如《关雎》释为“咏后妃之德也”。认为“言志”为雅,而“言情”为俗。词一出现,就以“艳情”为宗旨。这样,就确立了诗庄词媚、诗雅词俗的分野。这一分工,给了士大夫一个发泄情欲的孔道,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反封建性。因此,自词之诞生,直至柳永发挥到极致,“词为艳科”的俗的属性也就这样天然合理地存在着、发展着。但如果任其从俗、媚俗地发展下去,势必为士大夫精英们所不满,甚而毁掉这一新兴的诗歌体裁。
因此,苏轼“以诗为词”,标举词是“古人长短句诗也”的倡导,并非要抹煞词的特殊审美趣味,他只是要用诗之雅来改造词之俗,提高词的品格,使之能达到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因此,他在与柳词俗化的较量中,也曾指出柳词的雅句,标举其“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之句,说:“此语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苏对复古的热心,并非真要使词回到三百篇的时代,只是要以复古为旗帜,“提倡风雅”而已。正如后人也曾以《诗经》比附苏词,如元人叶曾为《东坡乐府》作序,说:“公之长短句,古《三百篇》之遗旨也……乐章数百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真得“六义”之体。”这一评价,也充分指出了苏轼“以诗为词”和提倡复古所得到的“雅词”的属性。
当然,也应指出,苏轼提倡“以诗为词”,提倡以“雅”治“俗”,其“诗”非古人之诗,(此点上文已述及)其“雅”也,非传统观念之“雅”。“雅”的观念,也是个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着的观念。唐之前“雅”的观念,主要是“正”的意思,也就是儒家的“思无邪”、“诗言志”、“诗者,持也”等要求诗服务于政治教化的意思,具有极强的社会功利性。当然,其中也有着内涵的嬗变历程。《诗大序》解释“风、雅、颂”之“雅”是: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到郑樵释“雅”,已初步从“雅”“俗”之衍伸义来论述:“雅出于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扬顿挫,非复小夫贼隶妇人女子所能道者,故曰雅。”但以“正”释“雅”的传统内涵,在唐之前仍为统治地位。到李白的“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其本质意义仍然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诗言志”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诗歌的风格要有“风骨”。
苏轼“提倡风雅”,其中也包括李白时代的观念。他主张文章要“言必中当世之过”,而“诗须要有为而作”。词诗一体,词也就自然要有骨力。苏轼“以诗为词”的大量词作,特别是后人标举为“豪放”词风之作,正是这种美学思想下的艺术实践。
但是,苏轼提倡之“风雅”还不仅是这些。随着唐宋之际的社会发展,随着市井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的两极分化,雅的内涵与处延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非常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界定,试标举其一二:
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唐之前以儒家的进取为雅而演化为以退隐为雅。唐之前虽然有魏晋六朝的隐逸风度,但却被视为旁支。直至白居易的诗论,都以服务于天子为诗之雅道,崇尚功名进取为士人的第一人生选择。有宋以来,形成以退隐为士大夫之首要抉择,即便为谋生之计,不能实现肉身之归隐,也要“对床夜语”,在精神上追求归隐。“归”成为士大夫灵魂深处永恒的企慕。随着这一潮流的兴起,原本地位平平的陶渊明,成为宋以来士大夫顶礼膜拜的偶像。陶地位的提高,与苏轼的重塑陶渊明形象密切相关。他在词中也曾隐括陶的《归去来辞》。
这一变化,引发了士大夫对很多事物“雅”“俗”的重新界定。譬如唐人之国花的牡丹,象征雍容华贵,而宋人则喜爱梅花,以梅为雅,而以牡丹为俗。两宋以来,自林逋“梅妻鹤子”并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之句来,又引发多少文人骚客折腰礼赞!
苏轼“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提倡,是与追陶思潮相关联的另一“雅”的内涵。因而,自然界中,凡能表现那种超凡脱俗、傲霜孤姿品性的,都成为士大夫雅文化的审美对象。
总之,由对归隐人生方式和“高风绝尘”的士人风度的追求,引发宋代士大夫人生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官场为俗而山野为雅,仕进为俗而归隐为雅,富丽为俗而平淡而雅,功名为俗而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为雅。这样,日常生活中的琴棋书画、诗酒唱和、品茗煮茶、赏玩金铭、采菊登高、踏雪赏梅等就构成了士大夫雅文化的主要内容。将这种题材、境界、情趣表现在词中,就是在词学艺苑中以雅对俗的改造。当然,内涵与表现手法密切相关,在前者的改造之中,也就势必影响到艺术手法,语言方式的变革。
因此,是否可以这样概括:苏词的本质并非“豪放”也非“婉约”,而是一种以“雅”对传统之“俗”的革新。这种“雅”的内涵,不是传统的“诗言志”的社会功利性,恰恰相反,它要求表现宋以来士大夫以归隐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的雅趣。
苏轼的雅词,可以包括题材、境界、情趣等内涵,也包括艺术手法、语言方式等形式。
第二节 “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
苏轼雅词的艺术实践
上文,我们通过苏轼“以诗为词”等主张,初步探讨了“苏长公提倡风雅”的命题,在《东坡乐府》三百多首的作品中,我们将可以看到其“风雅”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到其词作的题材之雅、境界之雅、才学识的情趣之雅、语言之雅等。
一、题材之雅
传统的说法是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
如刘熙载评:“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艺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全面,因其未能指示出坡词开拓疆域的方向。
笔者认为,东坡词开拓的方向,是进一步表现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特别是表现作为宋代士大夫杰出代表的东坡自我的襟怀抱负,日常生活。它的基本走向是弃俗从雅,当然,也不排除“以俗为雅”。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将词体从“词为艳科”的樊篱中予以解放。以柳永为代表的艳词,本身就是对“诗言志”社会功利说的一次解放,但如将此视为金科玉律,势必就又成为另一种禁锢。苏轼并没有使词回到服务政治的传统老路,而是要以词全面地反映宋以来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新的审美情趣。因此,举凡怀古、讽时、悼亡、送别、说理、咏史、宴游、述怀、出猎、戏谑、煮茶名茗、山水景物等,无不可歌之咏之。
其次,是柳永之前的词家,大多是“男子而作闺音”。这一命题除了说明表现情爱主题之外,还说明词人大多是以女性代言人的角色揣摩女性之心理、感受,如欧阳修之作“庭院深深深几许”,偶然为之,并无不可,染以为习,终沦俗调。坡词则以自身的生活为第一表现对象,其词中总是或明或隐地有着东坡之自我。明者如其词反复出现的“我”字:“我欲醉眠芳草”,“我欲乘风归去”,“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满江红》),“知君为我新作”(《水调歌头》),“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满庭芳》)“无情流水多情客,劝我如相识”(《劝金船》),“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水调歌头》),据台湾学者王保珍先生统计,约有56处左右。此外还有一些暗含“我”的角度,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不思量,自难忘”等,也有二三十处。大量抒写自我,而“我”的情调品格又远远雅于青楼歌妓,这无疑就从题材上提高了品格。
第三点,是“以俗为雅”。譬如坡词首创农村题材。描写乡村风光,当然是一种大众化的、通俗性的题材。但东坡所写,仍然是从士大夫“我”眼中所观照、审美的乡村,特别是结合北宋以来以归隐、平淡、雅趣为内涵的文人心理,这也就成为了一种“以俗为雅”的艺术表现。他所着意表现的是“牛衣古柳卖黄瓜”的乡野风光,“敲门试问野人家”的漫游奇历,“轻沙走马路无尘”的高洁以及“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元是此中人”的文人雅趣。
二、境界高雅
只有题材的拓展,尚不能说完成了词的雅化,更重要的是考察其表现的境界。
在苏词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吟咏歌伎或描写女性之作。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指出苏轼生活在一个歌伎盛行的时代,苏轼也不能免俗。以词写伎,表现了他从俗从众的一面;其次,应该指出,同样写伎、写女性,在东坡笔下,显示了高雅的情趣和境界。如《洞仙歌》写后蜀国主孟昶与宠妃花蕊夫人的一段艳事,却写得不仅有“冰肌玉骨”的外在形象,而且暗寓了人世沧桑的深沉感受:“试问夜如何?……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永遇乐》词写张建封的爱妓盼盼:“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先之以清雅的景物,绝人俗念,继之以“寂寞无人见”、“觉来小园行遍”,将历史与今天,他人与自我合为一体,赋予了深重的人生惆怅感。而“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更为雅致高妙。
苏词境界之雅,可分为两个方面论述:
首先,是创造了一种超凡脱俗,高风绝尘的艺术形象、艺术境界。比如写王朝云的“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刘熙载《艺概》曾标举《定风波》的“尚余孤瘦雪霜姿”与《荷华媚》的“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认为“‘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并说“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无疑正指出东坡雅词的这种特质。用东坡词句作题,可说是“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贺新郎》)。
这种“高风绝尘”的形象与境界,实质上大多是词人自我人格理想的寄托。词人也时有不作寄托,直写自我之作,如《卜算子》:“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读后只觉身在冰清玉洁之澄澈世界。山谷评曰:
“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真东坡之解人也。云此词为某女子艳情作者,无异说梦。
其次,坡词境界之雅,是由深刻的思想内蕴、高卓的才学识见、启人心智的人生哲理构成。没有思想内蕴的人或作品,往往流俗,或只能附庸风雅。
苏词中的思想深度,恐怕两宋词坛无人可以比肩。论者往往为其毫光四射的豪放气概所吸引,因而忽略了对其内涵的探索。其实,深邃的思想、深沉的情感正是豪放词不可或缺的基石。东坡后人之所谓无人学坡,非豪放技巧难学,盖无东坡之独特人生遭际与思想深度耳!前文所引东坡赞扬蔡景繁、陈季常“以诗为词”“豪放”等语,说明东坡词在当时就有人仿效。稼轩后人学苏辛,也终沦入叫嚣怒骂之流,正可佐证。
试看苏词名篇《念奴娇》,人们只被“大江东去”那天风海雨的气势所倾倒,其实,此词之归结,正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和“人生如梦”的沉重。其意义之深刻与影响之深远,足可另行著书论证。
《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意义,固然是题材的开拓, 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放里却埋藏着深深的悲哀:其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词人的“民本”思想不和潮流,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使他“聊发少年狂”。但“聊发”二字里有多少深意?故下片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希冀是沉痛多于豪放的。其实,这沉痛正是豪放的奠基石。正如他在《念奴娇》词里,要以“小乔初嫁了”来衬托“雄姿英发”的周郎,只不过江山美人是表层的衬托,而悲伤的内心与超旷是深层的意蕴。
在“超旷”一类的作品中,也大多寄托着词人的深遂思想,特别是旷达的人生哲理:如《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神宗读之,发“苏轼终是爱君”之叹,而笔者读之,却认为是其“野性”的典型表现,是进取与归隐矛盾心境的艺术写照。“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则更是对人生哲理的高度概括。
再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里的“雨”与“吟啸且徐行”的词人自我,既是一种实境,又是一个人生象征因而虚化了的境界。自然界之“雨”与人生政治的风雨,人的行走与人生旅途之跋涉,相为表里,互为对应。“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不仅是目前足下的风雨阴晴,而且更是词人人生形象的传神写照。这就使词作的境界既在此,又不在此,引发读者无穷之想象。
苏词境界的思想深度,不仅表现在所谓“豪放”词、“超旷”词里,也同时表现在前人所划分的“婉约”一类词作中:如《定风波》写与王定国侍儿寓娘(柔奴)的对话:“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深寓佛理禅趣。而写给王朝云的“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其中深寓的哲学理趣,又令人有多少回味!无怪朝云“歌喉将转”便“泪满衣襟”,说此正是“奴所不能歌”者。
苏词境界内涵的思想深度,哲学深度,正是构成其词高雅不俗的基石。
三、艺术手法高雅
最后,探讨一下苏词艺术手法方面的高雅因素。可以分为语言的清新素雅,用典使事的风雅,议论超卓的高雅等三个方面。
(一)、语言的清新素雅
苏词的语言特质是清新素雅,不假雕饰,用他写给王朝云的《西江月》可为象征:“素面常嫌粉★,洗妆不退残红。”──对于自身修美,气质高雅的丽人来说,施粉抹唇反而会弄脏自身的玉体,反而会显得俗气;对于“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的苏词来说,其深邃的思想、高雅的情趣,引人深思的哲理,“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艺术风格,足以使人倾倒。故东坡无暇、无须作太多的辞藻修饰。华美的辞藻,大多属于那些无病呻吟者。苏轼之前的花间词人, 之后的吴文英一派词人,比之苏词, 都要华美得多,这是由于其情感内蕴方面底气不足所致。这方面,苏、柳倒是一体,但同中有异:柳以朴素语言写市井题材,反映市民情趣,而苏以朴素语言写士大夫生活,表现高雅境界。
宋代是一个文人的时代、学者的时代。在传统的诗的领域里,自西昆之后,使事用典,蔚成风气。至苏黄时代,更演变为“以才学为诗”,并提出了“无一字无来历”、“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理论。黄山谷成为了“江西诗派”的实际创始人。其影响直达南宋。“词”被词人们视为“别是一家”,是专写“情”事的载体,学者们大可不必在此表现你的学问、才气与识见。故大学者如欧阳公写词,也全不见其才学。直至王安石,才开使事用典,咏怀思古之先河。但在词史中使事用典的里程碑人物,仍非东坡莫属。这首先由于苏词使事用典非偶然现象,而是大量地使用。打开《东坡乐府》开篇《水龙吟》即是:“古来云海茫茫,道山绛阙知何处?……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第二首,也有“中郎不见、桓伊去后”,“绿珠娇小”等;第三首,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字面无典,但“莺呼起”处却暗用金昌绪“啼时惊妾梦”典。自第四首以下数首,分别用“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归去来兮,吾归何处”(用陶诗),
“全胜宋玉,想象赋高唐”,“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
等典。而“安石在东海”一首,则起首结处均用典,以“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作结。前5页12首词,至少有九首用典, 这一抽查比例不知能否反映苏轼全部词作的比例。
(二)、用典使事的风雅
苏词的典故,不但不给人以“隔”感,而且达到借他人之酒杯,浇自我心中之块垒的艺术效果。苏词中所标举的历史人物,往往或是自我写照,或是对照自我。如咏“三国周郎赤壁”的周郎,《密州出猎》中暗喻的魏尚等。当然,也应该指出,坡词中的历史人物,已非李白笔下的“谢安”、“姜尚”,“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壮志,早已化为了“归去来兮,吾归何处”的陶渊明式的咏叹。苏词是面对往昔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满庭芳》)的喟叹;是“曹公黄祖俱飘忽”(《满江红》)的佛老禅境;是“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同上)的对魏晋风度的追思和今古时空的惆怅。
苏轼作词,虽未达到“字字有来历”,但也经常以史书经典为依托。如“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分用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和宋玉《风赋》;“破帽多情却恋头”(《南乡子》)则反用晋人孟嘉重九登山帽子被风吹走之事,极富雅趣;《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则分用杜甫、刘禹锡、《晋书》、《世说新语》、李益、白居易、韩愈、皮日休、元稹诗文典故。读后让人有“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的幽古清雅之美感享受。
词中用典,与词作境界的雅俗是否有关联,只消想想李清照批评秦观“少故实”的一段话就可明白:“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将“乏富贵态”理解成“乏雅致”就是正解了。
其实,作诗吟词,不必“字字有来历”。但学者之词与民歌之词即使同样都不使事用典,其中也自有雅郑之别。学者之词,其使用的语言,经历数千年文化的积淀浸泡,即便是“信手拈出”,脱口而来,其中也常有着文化传统的内蕴。这一特点,到李易安臻于极致──不必使事用典而文化素养、高雅情趣尽在其中。这当是“字字有来历”的正解。
(三)、议论超卓的高雅
苏轼以词来表达深邃思想,以至哲理,也就不自觉地改变了词的表达方式,由前人的“小山重叠金明灭”的描写句式引渡到议论的句式。试思前文所举各类例句,多为议论,譬如“人生如梦”、“此事古难全”等名句,其实都是词人的发论。这对词的演变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来源:木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