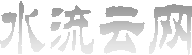第三代诗歌发生的诗学语境
80年代初叶,我们曾经历了“朦胧诗”第一次浪潮的洗礼,可就在这之后短短的时期里,不甘驯服的诗的精灵并没有就此安顿下来,一个新的无论就人数还是地域都较前更加广泛的诗歌实验潮流,又悄悄地诞生和崛起,以至最终形成了被人们称作
“第三代” 或 “新生代”诗的诗歌新潮,实现了对朦胧诗的又一次超越。从朦胧诗到“第三代”是一个纵向的流变过程,这不仅构成了“第三代”诗的一种深度背景,而且也为我们了解新诗内部发展的自律性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示和契机。
作为新时期第一只报春的乳燕的朦胧诗,在1981年左右达到了它的鼎盛期。以后的几年间,年轻的诗人们虽各自仍保持着一定的创作高度,但作为一个流派却已渐趋式微。北岛象一个孤独的智者,在遥遥的地平线上依然艰难地跋涉;舒婷一搁笔即是三年,当她复出时诗坛已是另一番风景;顾城继续述说着他那童话王国的故事;而江河和杨炼,则在前期史诗意识的烛照下,又开始向历史的深层掘进,力图寻求这种整体意识的源头和潜在形态,最早预示了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回归的迹向,促成了以契入文化和历史为特征的后期朦胧诗的形成。如果说他们曾经以群体的形式最早出现于《今天》,那么最后一次以集群形式的展现,则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所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中。这是一次“最后的晚餐”,而梁小斌可谓是一位“犹大”式的反叛人物,他写了《诗人的崩溃》一文,宣告了朦胧诗的最终解体。当然,朦胧诗的解体事实上还要更早一些,一般人认为是在1984年,自然这只能是一个约数。我们姑且以这一年为界,之后,朦胧诗完成了一次自身的变衍,过渡到后期朦胧诗阶段。同时,一股反叛朦胧诗的思潮也逐渐弥漫了整个青年诗歌,尤其是大学生诗歌,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
后期朦胧诗
在客观地描述朦胧诗后新潮诗的变衍时,我们忘不了以江河、杨炼为源头的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四川的一些青年曾把这一诗潮称作“第二次浪潮”(相对于朦胧诗的第一次浪潮而言)。但只要考察一下他们的创作和理论,就会发现这一群体并不能构成独立的意义。因为无论诗的内在本质,还是外部形态,都与朦胧诗有着血肉继承关系,它只能是朦胧诗自身内部的一次深刻而自然的延伸,当然也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如果说朦胧诗体现了一种社会现实意识的话,那么后期朦胧诗则体现了一种历史文化意识。这应合了当时文化反思的一种思维定向,即思考的触角不断地向民族的历史深层突进,诗正是以其感性的形式完成与哲学的同构的。
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萌芽于一些诗人对东方现代史诗的探求,这在早期的江河、杨炼那里就有比较自觉的意识和追求。江河在1980年左右就曾呼唤史诗:“为什么史诗的时代过去了,却没有留下史诗”(1)?并且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我要写这个古老大陆的神话,写中国的史诗”(2),他先前的《纪念碑》、《祖国啊,祖国》和杨炼的《大雁塔》,就已内蕴着一种史诗的气魄和特质。但是,那时朦胧诗的整体追求是寻觅西方新异的声音,正如他们在《今天·致读者》中所说的:“今天,当人们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文化遗址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因此,即使是江河、杨炼也不能一味地留连在古文化遗址之上,他们频频环视着广阔的地平线上的风景,而被一种现代意识浸润着。当然,正如谢冕所说,他们毕竟是东方的诗人,他们不能按西方的模式来写东方的诗歌,当他们向着世界艺术全方位的扫描之后,一部分青年诗人又开始回到东方,沿着黄河入海处溯源而上,寻找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之根(3),向着古老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的深层领域不断地掘进,一股文化思潮渐渐地在青年诗人中蔓延。江河、杨炼自然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杨炼继《大雁塔》之后,又写出了《诺日朗》、《半坡组诗》、《敦煌组诗》、《西藏组诗》等,以一系列优秀作品为东方现代史诗的创作提供了较为成熟的范式。有一段时期,诗人江河曾一度辍笔,读着中国的历史、神话和诗歌,并一次又一次在广阔祖国的名山大川间神游,终于在1985年奉献出《太阳和它的反光》这组现代中国的古老神话。随着江河、杨炼而来的便是一长串陌生和并不陌生的名字,仅以四川为例,就有石光华、廖亦武、宋渠、宋炜、王川平、黎正光等。他们以博大的哲学意识重新观照古老先民的生命形态,从深邃的东方文化中确认生命存在的真正价值。由此,一个饱蕴着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质的意象群落组成了现代史诗的象征世界,诸如盘古开天辟地,羲和驭龙巡天,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使我们从中真正体验到了原始的生命意象。这种东方现代史诗性作品,开始时总是对古老的神话、先民文化遗址、宗教寺庙等历史素材给予过多的关注,企图将历史幻化为一片感性的时间和风景,从而探触到民族文化的原始意象。比如王川平的《雩舞》,以宏大而悲壮的场面,再现了了远古先民祈雨时的巫术仪式。这是一种充满神秘力的舞蹈,虽然仅存于人类非常遥远而淡漠的记忆中了,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生命绵延中,曾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有形无形地延续着,形成了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层面,体现着我们民族那种坚韧顽强的悲剧精神以及“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形象地显示了民族心理的原型范式。再如宋渠、宋炜的《大佛》,表现了对民族心理的深入剖析,香火和朝拜的虔诚只能被自己的虚妄所欺骗,“一个坐着的宁静,坐着的永恒”的大佛,其实只不过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他自身“永远都是开始,永远都是结束”,并没有任何充满希望的神谕。
东方现代史诗与我们民族的心理达成了一种同构。我们这个民族有着可供回忆的辉煌的过去,有着随处可见的过去时代的遗址。因而,对历史便怀有其他民族少有的原始的热情,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说的,“在中国,每个旅游者都勤奋地追寻‘古迹’,而中国哲学的基本原则——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即系从此一深挚的历史感情而来”(4)。自然,我们不会怀疑民族历史感的意义,但对历史若钟情到足以扼杀对现实存在的关心,那就应该值得怀疑。现代史诗性作品的寻古倾向,显然受着文化积淀理论的影响,每一处古物遗址或一块历史的石头,都能给人们造成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这在寻根者即以此物作为原始文化的形态或象征,从而窥视古老的文化原型。按照荣格的解释:“原始意象……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着同样的路线”(5)。但这种原始意象不是客观存在的物的机械反映,而是在主观体验的幻想中得到的。因此,单纯地用现代语言去诠释古代的历史和神话并不能表现“集体潜意识”,正如荣格所说:“有些诗人写诗时,把历史和神话作为他们的素材,但这两者之中都不含有感人的力量和深刻的意义。感人的力量和深刻的意义包含在幻觉经验中”(6)。因此,集体潜意识以至文化,并不是无生命的存在物,它是伴随着人的生活经验共存的,并潜在地支配着现实的人的生活方式,它如同血液流淌在人的生命体中。
如果说江河、杨炼们出于建构东方现代史诗的热情,以清醒的历史意识倾心于民族的原始神话和历史素材,企图于再现先民远古景象中呈现民族心理的原型范式。那么后来标榜新传统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新古典主义诗人,更多的则是对人类整体精神的形而上观照或者幻觉体验,力图从自身体验的角度超升到人生与宇宙精神的汇通,从而使诗歌负载起一种文化基因。这在廖亦武的诗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不可能象‘史诗派’那样,依靠丰厚的文化基础和高强度的理性思维去‘论史’,我只有凭借铭心刻骨的想象去设计一条线索,把个人沉沦转化成人类的苦难。”(7)因此,他的诗中没有那种明显的历史遗迹,他甚至不去关心任何历史,而只凭想象的穿透力,描摹人类永恒的生存状态,以契入民族的原型心理及原始情状。他的这种诗的方式与他那种泛灵式诗学观密切关联。因为在他看来,文化并不是什么古史遗址和博物馆的文物陈列,这些都是消逝了的远古象征,文化就在一片陶然忘机的自然和流动着的血液之中,“一片石壁,一阕山歌,一种民间舞蹈,都携带着某种生生不息,世世递嬗的远古‘文化基因’”,诗人只有通过想象力的穿透性,才能破译这种“自然——文化语码”(8)。廖亦武诗那幻想的瑰丽和磅礴,无疑是现代中国的神话史诗,特别那些长篇巨什,更是如此。《大循环》给我们表达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条普遍法则,“万事万物都在循环,人也亦然”,诗人通过个体的生存体验,来展示群体的生命本质,在个体的循环超越中,上升为人类整体精神。在《巨匠》中,诗人描绘了生命、自然和文化浑然同构的生存状态,他沉陷到民族潜意识的底层,体现了原始形态的泛文化倾向。廖亦武是个超然和旷达的诗人,他的全部努力都在于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时空,而进入一种与天地同流的宇宙境界,以达成高级的生命形态。在一首诗里,他给我们描绘了人生的这种最高境界:“超越时空的纯洁/没有思想却进行着/最高的思想/白猿般月亮在我身旁进化/人们又一次征服陆地/面/对天/空/想象之马沿银河遨游/星星是马蹄/践踏起悠远、清脆的泡沫”。(《归宿》)
欧阳江河相对于廖亦武,是一个理智多于幻觉的诗人,他的诗充满着形而上的思辨色彩,并努力使自身散发出文化的氛围,变成艾略特式的文化的白金片。我们读到了欧阳江河的《悬棺》,那史诗型的宏阔篇什,整个儿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神秘和阴阳五行的玄奥,难以索解的意象和象征,大都是在生与死的自悖中展开的。
1984年夏天,在朦胧诗逐渐式微之后,石光华、渠炜和杨远宏等在四川成立了自称为“整体主义”的诗歌社团。石光华、渠炜均是提倡过现代史诗的诗人,这时他们提倡整体主义诗歌,不免仍带有现代史诗的精神内核,即宇宙生存整体的显现。整体主义根本上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存在形式,它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存在与整体的联系和生成,只有包括人在内的整体才是具有确定意义的存在”,人也只有超越自身的存在而上升到整体的层次才是真实的,因为他不能离开整体而生存。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强调世界整体对有限个体的包容。整体主义诗歌即是这种思想“在诗学域中的还原”,是“对整体状态的描述或呈现”,这样才能“直接面对整体而向存在开放”(9)。理论的完整和深入只能为诗学提供一个基础,真正显示意义和价值的应该是诗歌作品本身。但是我们目前还很少读到他们精致而典型的篇章。石光华的《结束之遁》或许是其代表性的力作吧,意境的神秘、寂冷和静穆足以使人沉潜到生与死的底层。灵魂与生命在一个又一个的意象间徘徊、追寻,有如穿行于生与死的通道,寻找着逃离或永恒的瞬间。这首诗的前边有一则题记道:“死亡作为一种瞬间,使所有先行其中的灵魂体验了永恒,而生命亦因之成为一次对死亡的逃离”。这体现了生死观的整体律动和对整体状态的描述。在“现代诗群体大展”中,我们还读到宋氏兄弟的《大曰是》(选章)和石光华的《梅花三弄》(选章)。就艺术上说,前者如汉大赋似的铺陈恣肆,后者如宋词般的典雅、清丽,整体上表现了一种对东方艺术的回归。这是他们企图建立东方现代诗歌的实验,也是他们企图回归东方精神的冒险,他们预言,“在荒原上一个重建人类文化背景的大时代已经来临”。作为东方人,他们在遍走西方之后又回到东方,找到了本世纪“最平静最丰实的精神合流”(10),这就是他们借鉴“全息生物学”和“宇宙全息统一论”的理论,所创立的“全息宇宙生物律”。这能否成为东方的现实,我们只好静静地期待着。
如前所说,后期朦胧诗主要包括前期的现代史诗和后期的新传统主义与整体主义诗歌,它是朦胧诗一次深入地自身变衍。当然,这不独是因为江河、杨炼曾启示和催生了现代史诗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与朦胧诗大体一致的艺术精神,其中主要的是文化意识、理性主义和崇高感。在朦胧诗那里,文化表现为政治性和现实性。诗人总在政治和现实的边缘上行走,而理性主义又启迪了他们对人的价值地位的认同,这多半还带有启蒙时期的人文精神。人的主体意识的极度张扬,必然导致人的自我崇拜,因此,朦胧诗在把宗教的神人拉下祭坛之后,却又导向自我的神话,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或优雅或悲壮的崇高意识。后期朦胧诗继续在此精神上向一片开阔地走去,他们曾受过一阵文化热的煽动,自觉的文化意识促使他们从现在和未来转过身去,向着人类的过去频频注目。凭着理性的触须,他们深入到人类文化的深层域限,在个人被集体潜意识包容的同时,东方文化并没有减弱他们的优雅姿态,尤其是蜕变期的困苦,使一部分诗人表现出强烈的神圣感和悲壮感。在艺术的方式上,朦胧诗适应主体的表现要求,多采取意象手法,这里自然包括变形意象和象征意象。意象的密植、跳跃,意象间的递嬗、流动,这一切均致力于营造知性的空间张力场的效应。后期朦胧诗只不过把这种意象手法用到了更宏阔的艺术形式中,其意象的繁富、流丽与辉煌,更有过于朦胧诗,象征也从先前较多的单主题象征而深入到多主题象征。其发展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并也有某种程度的超越,但从总体和本质上看,它依然归属于朦胧诗范畴。
这里还要分析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即所谓“超越性”。超越,骨子里是一种理性意识,无论朦胧诗还是后期朦胧诗,对此都怀有特殊的热情,他们总是要超越此时此地的自我的限定和生命体验而导向另外的目的。朦胧诗人被一种政治现实意识所升华,后期朦胧诗人或超越具体的生命存在,显现整体的精神律动;或达成人生与宇宙精神的汇通,实现高级的生命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与此时此地生存着的个体相游离的。事实上人不能全然超离生命的存在,即使新传统主义的廖亦武,也不能彻底“超越我的本体”,因为“想象高飞而身体沉重/他还不能走出树的视野”(《越过这片神奇的大地》)。因此,超越只能是有限度的,如果说诗歌本体是对诗人本体的全然超越,那又是矫情的,不真实的。对此,另外一种实验的潮流开始涌动在我们的视野,那旗帜上写着:回到本体,也即回到诗歌,回到诗人。这是一股感性生命的潮流,它几乎孕育在朦胧诗的理性泛滥的时候,并最终形成了一股大潮,冲决着朦胧诗所经营的艺术堤坝。
校园诗歌
如果说朦胧诗在它的高峰之后便缓慢而平静地顺延为后期朦胧诗,那么“第三代”诗在它的高峰之前也曾有过一段漫长的酝酿、滋长过程。可以说,大学生诗歌就是“第三代”诗产生的触媒和温床,它无疑构成了“第三代”诗的直接背景。因而,我们不能不把目光延伸到几年前的大学校园,那里荟萃了当时许多中国新一代的知识精英。当朦胧诗鼎盛时期的1980年和1981年,大学校园聚集了“文革”后第一次“四代同堂”的大家族,并度过了一段圆满和充满生机的时期。学子们追求知识,追求思考,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当北岛们以深刻的人文色彩、理性精神以及淡淡的忧郁和美好的幻想向他们袭来的时候,他们不由自主地被慑服了。他们狂热,他们陶醉,他们开始在杂志上寻找着仅有的几个比较熟悉的名字,传抄着一首又一首陌生的诗歌。然后他们涂抹、划掉,然后再涂抹,直至酷肖而自豪。无疑,那时一颗颗年轻诗魂的骚动是自不待言的。只要你的一颗心还是属于诗的,你就不能不受着那种形式与情感的煽动,无论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你都会随着北岛们走一段或长或短的路程。
当然,我们不能以“模仿”这个与艺术本质相悖的词语来统观朦胧诗的追随者,因为其中也不乏佼佼者,他们的诗歌同样凝聚着个人的心血和体验,凝聚着对创造的热情。只是因为时尚是不可抗拒的,这种心理效应几乎可理解为某种血质和命运。因而,追逐时尚并非什么致命的缺失,有时它往往是一种生命的机遇。对此,我们看到了第一批模仿的幸运者,如徐敬亚、王小妮、叶延滨、高伐林、王家新、吕贵品等等。他们大都和朦胧诗人有着相似的履历和遭际,共同经历过理想的追求、幻灭和思考的过程,因此那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便构成了大致的主体意向。在艺术上,他们大都在传统的诗歌氛围里熏陶过,并熟悉了那种单一的诗歌程式。所以,当他们第一眼目睹到怪异新奇的朦胧诗时,几乎被这种艺术给惊呆了,正如徐敬亚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我想不到,诗竟可以这样写?!读烂了诸如‘朝霞满天’、‘东风万里’,我想不到我们古老的方块字里,竟还埋藏着如此美妙的诗篇”。(11)因此,他们最早感应着朦胧诗的脉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大潮,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作为第一批校园诗人,他们依然没能超越朦胧诗人们所开拓的意识范畴和艺术范式。
1981年初,甘肃的文学刊物《飞天》率先办起了《大学生诗苑》,编者并预言:中国新诗最集中的读者群和作者群之一,新近几年就在大学校园。随后,其它几家刊物如《诗潮》、《诗林》、《青年诗人》等也相继开辟了大学生诗专栏。于是,大学校园的诗歌精英们开始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在自己的园地中。第二批校园诗群就其队伍的庞大来说远远超过了先行者们。这部分诗人都比较年轻,大都在1979年之后入学,他们爱上诗,也多半由于朦胧诗的诱惑,这就不可避免地有一段模仿的过程。然而,他们毕竟与朦胧诗人和第一批校园诗人不同,他们大都没有卷入那“红色的风暴”,没有扭曲的人生履历和痛苦的遭际,缺乏那切入骨髓的情感体验。因而,他们模仿的诗也就不免给人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就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不选择另一条路,那是永远不会有什么造就的。因而正如这模仿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分化和超越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
1982年之后,一个校园诗歌的新格局渐渐形成。这首先应该有赖于诗人们自我独立意识的确立,当然也离不开文学和社会的背景因素,诸如反思文学的渐趋低落或转型,建设时代的高涨的热情以及开明的政治气候影响等。我们看到,先前那种伤痕诗的阵痛和追索消失了,形式上也一改那凝重和沉郁的格调,变得或热烈,或沉静,或轻快优美,或自然淡远。在1982至1984年的几年间,一方面,较为流行的热态生活诗活跃于诗坛的表层;另一方面,一部分甘于寂寞的年轻诗人,不随俗流,只是默默地执着于诗的实验,于是产生了一种冷态抒情诗。它虽不被刊物所青睐,但却显示了充沛的生命力,以至后来奏出了“第三代”诗的主旅律。
热态生活诗的产生和发展在其时间和质的层面上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982年至1983年流行的新生活颂诗和1984年流行的新生活宣叙诗。新生活颂诗开始萌芽于80年代初期,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由于改革的春风较早地吹到了这里,人们的生活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时代节奏的加快,生活内容的丰富繁杂,使人们目眩神迷。短暂的不适应状态结束之后,人们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开始汇入了新生活的大潮之中。年轻的诗歌爱好者被新时代的召唤所吸引,开始从先前刻意的模仿中挣脱出来,由关注自我开始转向关注周围的生活,由内心走向了身外的世界。从艺术上说,年轻一代的诗人们不能总是靠模仿搪塞诗歌,也不能总是愤怒、怀疑、叹息或幻想童话的王国,那毕竟不是更年轻一代的经历与情调。即使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第一批诗人,这时也有一种新情感在悄悄滋长,比如:“我,和我的同辈人一样/有过忧伤。然而/……/然而今天,我却禁不住又一次激昂”。(徐敬亚《长江,在我的手臂上流过》)
1982年开始,这类描摹和歌咏新生活的篇什在一些刊物上比较流行,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几乎形成了一股诗潮,这在《飞天》的《大学生诗苑》中可以看出。他们用饱蘸着新情感的恬淡笔触,热情地描画着现实生活的图景,表现着现代生活飞速旅转的节奏以及这种生活所引起的千差万别的情绪波动。于是,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日常生活的镜头,纷纷跃入了他们的诗行。我们不仅看到了那修理钟表的待业青年,卖馄饨的小女孩和粗鲁厚实的锻工;而且也看到了那高高的脚手架,自行车流动的大街,以及迪斯科舞厅和旅转餐厅等。无疑,一种新生活的兴旺和繁忙洋溢在诗人的笔端。但是,这个时期的新生活颂诗,似乎接续上了50、60年代反映工农兵生活的诗歌传统。因而,过于拘泥于平面地描摹热火朝天的场面,很少探触丰富复杂的人的内心世界。过分渲染的颂歌情调以及艺术上的机巧的类比与象征、大而无当的虚化与升华,不免显得过于造作。并且这一旦形成了模式,也就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后来,一些年轻的诗人着意克服这种写实的缺陷,转而关注人的心理世界,同时又要揭去那种矫饰的面纱,而使人物显得自然平实。因而,他们常常避开那轰轰烈烈的场景或明显积淀着现代色彩的大事件,而把目光投向日常的平凡生活,并以朴质的令人亲切的叙白流泻出来,写得随便自由,好似音乐的宣叙调,读来格外亲切。这种宣叙诗大概成熟于1984年,并曾风行一时。
热态生活诗的总体情绪已告别了朦胧诗式的悲剧色彩,转而表现现实的生活和情感。他们关注的是今天,即使偶而把触角伸向昨天,也很少绝望、颓废的世纪末情绪。《我洗净了我的衣衫》(曹汉俊)即是这种情绪的总体象征:“我永别性地清除了过去的污染,即是宣告向过去时代告别”。“今天的我不再是昨天的我”(杨榴红),是因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无忧无虑阳光一样灿烂/他们说黑夜过去了如今是太阳的年代”(于坚)。因而,他们纷纷从朦胧诗那痛苦的心灵和自我中走出来,而置身在灿烂的阳光下,正如伊甸所说:“他们直面生活,把最平凡的人和最平凡的事作为抒情的对象,他们的诗情之海不捐弃哪怕微小的浪花——只要这些浪花能反射太阳的光芒”(12)。如果说他们的诗中还有“我”的话,那也只是一种指代和假托(这在新生活抒情诗中更为明显),他们更多地是转过身去,面向他人和整个群体。因而,他们诗中的名称也多半是“我们”、“他”、“他们”。他们自认为自己是这个平凡的群体中的一员,因而也只是作为群体的代表而出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叛了朦胧诗的自我英雄模式,但在有所获得的同时,也丧失了另一部分诗的个性。这就导致了一些诗看似对人物心灵洋洋洒洒地铺写,其实是将一些表层认识投射到人物身上,表现了社会的某种流行观念和对生活的浅层感受,由此出现了一些模式化、概念化的诗作。
热态生活诗的总体艺术特征之一,是它的叙事性。在叙事文学纷纷心理化而趋近诗的同时,而诗歌却默默地向叙事文学借鉴着什么,似乎力不能及地担当起叙事的角色。自然这类热态生活诗的叙事并非有清晰的事件逻辑,它常常是间断的、浓缩型的,因而,也就常常需要读者的想象来串接。尤其是新生活宣叙诗,它多半是自我的宣言式介绍,因而事件的密度就难于化开。
由于叙事性的强化,铺排就成为热态生活诗的一种基本艺术方式。新生活颂诗的铺排是事件铺排,这与诗人对此所采取的艺术手段有关。一般来讲,新生活颂诗句式明快、急促、节奏强,这和生活节拍是相适应的。正如一些诗人所说的,诗与生活的节奏互相交融形成创作的节奏层,把握住了节奏,就把握住了艺术创作的脉搏。但在叙事过程中,往往事件进展缓慢,铺展过多,常常中断事件,铺排想象或作无边际的升华。这多半又大量运用朦胧诗的表现手法,比如通感、变形、象征、隐喻、意象叠加、具象词与抽象词的嵌合、打破时空秩序等等,由此,叙事与比附交叉流转,使得篇幅过分冗长。新生活宣叙诗的铺排表现为句式和篇幅的绵长,他们写得洋洋洒洒、随随便便,似乎不太经意,读了他们的诗,“给人一种笑咪咪甚至懒洋洋的感觉,大方阵的队伍似乎随意地组合在一起;黑压压貌似缓慢实则急煎煎地扑过来,似一大段嘈杂的闹响,聒耳而来……”(13)。又如徐敬亚所说,他们“走朦胧诗的‘深刻度’。长长的句子,为他们平凡而充满厌腻气的校园书桌宿舍生存方式,找到了无法删改的冗长之年”(14)。从句式上看,宣叙诗多采用反复、顶针、省略句子成分等方式,给人造成绵长流转而又急迫的感觉,句与句之间也通常不留想象或语韵回旋的空间,有时用大片大片的排比,让你一口气读下来,犹如串掇起的珍珠,绵绵不断。如“我们郎平一样蛮狠地干活/我们用毛巾使劲地擦汗/(象那位络腮胡子的师傅)/我们常常把手上的油污当作胭脂/给自己的小圆脸瓜子脸鹅蛋脸/或者大胖脸和瘦长脸/错落有致地点缀几朵/叫不出颜色的牡丹”(伊甸《快乐的女车工》);“月亮的镜子是白沙岛白沙岛的镜子是太阳”,“也曾有美人鱼在晒月光/皎皎地象白色沙/白色沙柔柔地托着我”(杨榴红《白沙岛》);“我们溜冰跳舞看小说吃奶油话梅/每星期两个晚上/拜访韦达牛顿门捷列夫”(伊甸《快乐的女车工》);“既然跳舞不行咱们就不跳了/既然唱歌不行咱们就不唱了/咱们溜冰吧永远去溜冰/溜冰真快乐溜冰也象跳舞/还象唱一乎奋斗者的歌/咱们去溜冰吧永远去溜冰/咱们去溜冰吧永远去溜冰”(若子《溜冰、跳舞、唱歌》)。这种语言机巧、诙谐,富有幽默感。
诗坛表面的喧闹,并没有掩盖一股潜在而冷静的探索潮流,这就是冷态抒情诗。这些诗人不象新生活诗那样,一味地追逐刊物和名利,他们似乎对艺术本身更执着一些。因此,他们便一直是地下的,唯此地下,他们才更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说朦胧诗旨在表现和寻找自我的价值和意义;热态生活诗意在描摹周围平面的生活或宣谕年轻人并非深刻的精神世界;那么,冷态抒情诗则是对人的命运的严正审视。在这些冷色调的抒情诗中,我们似乎处处可触摸到那命运的不可抗拒的奔突和凄惋,以及作者冷静的咏叹。生命被这命运无可避免地支配着,这是平凡的生命的常态,也是世界本来的样子。韩东先前的一些诗,几乎就是这命运的咏叹调。他视命运如血液流淌在我们的肉体中,一切都无可改变,我们别无选择或唯一的选择就是默默地承受它。因此,在他的许多诗中,我们都能感受到那冷冷的目光和静穆的心灵。当然这并非说他从没有火样的热烈过,那首令人激动的《山》,可说就是如岩浆一般奔突出来的与命运的挑战。那种威武不屈的挑战者的姿态何等执着与坚定,简直就如树立起的一尊英雄的雕像。可是后来,他在命运面前渐渐地平静下来,变成了一种咏叹和诉说。那首《山民》可理解为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概括,但又何偿不可以理解为对他人命运和自己命运的感叹。走出群山去见大海的渴望与现实存在的落差,只能使他深深地遗憾,可想到飘渺虚幻的未来,又不免感到疲倦。他对命运虽怀有一种祈祷、渴盼、期待的心态,但当这种期待真正实现以后,又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呢?我们读到他的《你见过大海》,那
“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的回环,给我们满目索然的空洞之感。命运就是如此地不可捉摸,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你感到命运的无常和神秘,但你又不能不正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去关注生命自身的存在,命运或许就在这生命的形式和过程之中。至此,已引出了“第三代”诗的一个中心母题:生命。
1988、9
(1)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青年诗人谈诗》第23页。
(2)转引自肖驰:《〈太阳和它的反光〉的反光》,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3)谢冕:《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
(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台湾版。
(5)(6)见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1987年三联书店。
(7)(8)转引自巴铁:《他的执拗,他的热情》,见《中国》1986年第11期。
(9)参见《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第三辑),《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主办。
(10)(14)徐敬亚:《圭臬之死》(上),《鸭绿江》1988年第7期。
(11)徐敬亚:《她的诗,请你默读》,见《新叶》1982年第7期。
(12)伊甸:《南方,又一个崛起的诗群》,见《诗林》1985年第4期。
(13)于慈江:《新诗的一种宣叙调》,见《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4期。
【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