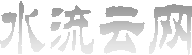第三代诗学
◇
孙基林 ◇
文化的消解:第三代诗的意义
八十年代诗坛经历了朦胧诗的激烈震荡之后,实验诗仍以突进的前倾姿势继续前行。尤其经历了1984至1985年的潜伏和发生期之后,到了1986年,进入全面的喧哗骚动期。一些刊物如《中国》、《诗歌报》等,刊载了大量青年诗人的新潮作品,特别是1986年底《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更是展现了先锋诗坛的全景性景观。尽管它不免失之于某种浮躁和芜杂,但给人们心灵的冲击和颤栗却是永久和深刻的。它曾一度使人们陷入某种迷茫和沉默的窘境,就如诗人们当时所嘲讽的:如今沉默似乎也变成了一种风度。然而诗人们却不能因为一种风度而永远沉默,他们纷纷揭竿而起,自我命名,自我确认……在看似纷披迷离的格局中,依然呈现出了一种有序的诗歌生态图式。一般说来,这种以前倾态势突进的实验诗,逐渐显现为两种生存形态:其一是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为前锋的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的凸起和变延,这里还包括要“走向民族文化意识”深层的“大浪潮现代诗学会”,推崇东方神秘主义、老庄哲学和佛教禅宗的“东方人”以及“从混沌的历史中心繁殖诗的蝎子”螫形而上之虎的“太极诗”和“自入真化之境”的“求道诗”等等;其二是以“他们”、非非主义为中心的非文化诗的生长,其中包括反崇高、反意象的“莽汉诗”、“大学生诗歌”以及反技巧、重语言及生命的“海上诗群”等。这后一诗歌流向所辖社团不下数十种,它们既有共同的诗学追求,又各自保持着独异的特色,并相互交错、补充甚至对立,共同汇成了实验诗歌的洪峰大潮。
对于朦胧诗后的新潮或实验诗歌,人们曾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称谓。有称“后崛起”、“后朦胧诗”、“后新诗潮”的,有称“第二次浪潮”或“第三次浪潮”的,也有称“第三代”或“新生代”的……但无论怎样称谓,它都应该是指朦胧诗之后先锋诗歌的一种新的审美思潮和创作倾向,而决不是整个青年诗歌的无差别的整合。在这里,我们所论及的第三代或新生代诗歌,主要是指以“他们”和“非非”为代表的非文化的实验诗歌文本及其诗学形态。
大概由于某种历史的因素,中国当代诗歌始终没有摆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命运。共和国诞生之后,诗歌本应摈弃战时文学的观念,转入诗的本体世界的建构。然而,诗歌并没有获得这一次机遇,只是仍然顺延着诗教传统的惯性流变,继续充当政治的附庸,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诗歌事实上只是政治的传播媒体和宣谕工具。朦胧诗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诗人的自我,淡化了诗的政治角色,然而,北岛们最终仍然没有摆脱政治的牵制,因为他们以反现实的姿态出现,所表现的恰恰是一种泛化的社会政治意识。江河、杨炼对历史感的呼唤和史诗性作品的探求,只不过是这种泛化的政治意识向纵深的延展,他们所思考的中心仍然没有远离现实的政治,只是把现实与历史紧紧地扭结在一起罢了。无论是这种现实的政治感,还是悠远的历史感,都是文化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是后来一些曾经追随江河、杨炼的诗人,更是在涵盖政治感和历史感的基础上,企图使诗上升到更高的文化的层面,这便是前所述及的文化诗的建构。然而,在第三代诗人看来,这种对诗的现实政治感、历史感和文化感的强化,都是妄图使诗变为抽象理性的载体,这种非诗的因素,正是使诗长期徘徊在诗之外的主要障碍。于是,一场重建诗的本体的革命便从这里开始了,而“非文化”便是这次诗学革命的最灿烂的标识和出发点。
“非文化”的另一深刻动机还在于对既有文化的怀疑和清算。所谓文化,这里主要是指一种观念形态的理性积淀,它是既有的人类生存方式、行为方式等诸种主体活动的精神产品和范型。人在其自己的活动过程中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同时也被这辉煌的文化所编织所创造,因此说,他始终生存在文化的世界之中,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文化的动物罢了。正是人的这种似乎恒定的无生命的生存状态,使第三代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忧虑和怀疑。他们确信,人类曾经生存在一片令人怀恋的本真的乐土即前文化世界之中,那里的一切,都真诚地裸露出一片存在的澄明。只是到了后来,人的双手不仅创建了文化,同时也毁灭了这一片真纯的净土。从此,人和世界便失却了本源的意义和面目,而被一种文化的网络所牵绕,他们只是以一副文化的面具和符号相互呈现,全然远离了自己所由诞生的本真的乐园,就如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一样,只不过这杯苦酒与上帝无关,只是人自己一手酿造而成的。前一时期,知识界曾经热烈地讨论过人的异化,那只是说人被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社会罪恶所异化,就如卡夫卡的小说所描述的那样,人最终被这种罪恶异化成了非人的甲虫。而第三代诗人显得更为偏激和彻底,他们认为,人决不仅仅只是被一种所谓的社会罪恶所异化,他被远比这大得多的文化及文化的诸种形式所异化了,人变成了非人,世界也变成了非世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第三代诗人纷纷从非文化开始,企图重建一个本体的世界,使之重现人和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诗派的“归真返朴”,非非主义的“前文化还原”,“反诗”的“不变形描述”,都是向着这一前景的美好的跋涉。
第三代诗人的非文化,绝不只是止于一种动机或一种观念的提出,也不是一个美丽的寓言,他们已切实地突进到了诗体实验的前沿,在纷纷淡化文化、消解文化的过程中,使人和诗还原到了本真的存在状态,呈现出一种非文化的“原在”。这里有两首同样写“大雁塔”的诗作,杨炼以“位置”、“遥远的童话”、“痛苦”、“民族的悲剧”、“思想者”等节的巨大篇幅,具体表现了大雁塔的人格化历史:“我被固定在这里/山峰似的一动不动/墓碑似的一动不动/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在杨炼笔下,大雁塔被赋予了浓重的历史感和人文色彩,它是民族命运的象征,是民族苦难的历史见证者。可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就完全是另一种境界,“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不过如此而已。大雁塔不再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积淀物,它没有任何美丽的侧面和深度象征,它完全切断了与历史的某种联系而成为一个在此时此地存在着的物体。我们爬上去,就如爬上一个有一定高度的其它什么东西一样,只不过为了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你能说这大雁塔还有什么历史感和文化感吗?从以上两者的比较分析中,我们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启示,所谓第三代诗学,其全部的思想基础便奠基于非文化意识之上,他们企图超越文化的樊篱,而回到诗的本体世界,这个本体世界的任何事物,均是借助语言的形式而呈现出来的原生状态。仅仅是呈现,而不是表现,因为事物只能是事物自身,而不是别的什么。它不负载任何其它的意义,任何文化的价值评判对它都不起丝毫的作用,它就那么存在着,无所谓有意义或无意义。这种非文化形态,正是第三代诗的真谛所在。
非文化是第三代诗的总体思想基础。而文化决不是不可感觉的,它既然以诗的方式存在着,就必然呈现出一种具体的状态,一种表现的形式。在现代诗中,尤其是在第三代诗的近景——朦胧诗中,“崇高”便是这种文化所呈现的一种美学形态,而“意象”则是文化得以存在的形式。因而,“非崇高”、“非意象”就构成了第三代诗歌非文化的两大基本标志。
非崇高:消解文化的美学形态
崇高是一种具有质的规定的美学范畴,它在近代艺术中一直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即使以叛逆者相标榜的现代派艺术,也终没有根本动摇崇高所赖以生长的基础,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强化了这种美的范式。介于浪漫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朦胧诗,总体上便是一种崇高型的艺术。这种崇高在北岛那里具体表现为异化现实的悲剧感,而在江河、杨炼那里则体现为民族悲剧的历史感、神圣感。或许再也没有另一个比这更悲惨的世界了,在北岛笔下,黑暗竟然假借着太阳的名义,肆意掠夺和戕杀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在本是太阳镀成的金色的天空,却到处飘动着死者的倒影和冤魂。江河们继续把这种悲惨的景象延伸于历史的国土上,长城在国人传统的心目中,本是民族的伟大象征和骄傲,可在江河的笔下,它却变成了一条沉重的锁链,把整个民族束囿在一片血泊之中。这种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悲剧,构成了诗人们的灵感基础和意识背景,并随之衍生出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这是一种民族的原型心态,可朦胧诗人们给予了集中的升华和渲染,使之更具有反抗性和英雄主义色彩。历史的人格虽久在忧患中浸淫着,但却绝少能摆脱默默地诞生和消失的生命模式,一桩桩的悲剧也就在这沉默的土地上不停地换幕着。可北岛们以历史悲剧的挑战者的姿态,纪念碑似的屹立在人们纷纷倒下的地方。在他们的诗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原始母题:普罗米修斯意象。他们就和普罗米修斯一样从天上盗得火来,撒向人间的芸芸众生,而自己却甘愿忍受高加索山上那永恒的苦痛。这种英雄式的悲壮和济世人格所给人的激动自然是崇高的,如同面对一座纪念碑时所感受到的肃穆、庄严。当然,朦胧诗还有另外一种崇高的形态,如果北岛们的崇高是一种“静穆的伟大”的话,那么舒婷们的崇高则是一种“高贵的单纯”。他们表现的当然也是那种社会的忧患意识,只不过与北岛们的深沉、冷凝不同,舒婷们往往把一种忧患与反抗意识寄托于古典式的童话和幻美的寓言之中,无论舒婷式的“美丽的忧伤”,还是顾城式的天真的寻求,虽均似贵族王子式的优雅姿态,但却终究掩盖不了骨子里的悲剧性。
然而,北岛舒婷们的命运几乎是宿命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们不能摆脱那个悲剧性的年代,他们曾经和那个过往的世界一起沦落、浮沉过,因而,对时代的脉搏也就格外的敏感,并不可避免地感染了那个年代的典型情绪:忧患与怀疑。加上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责任感和他们所特有的英雄意识,其崇高感也就自然而然地弥漫在或深沉或优雅的诗意氛围之中。无可疑义,朦胧诗的崇高感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真实的,只是当这种姿态被认可为一种供人或供己效仿的范式时,其真诚也就渐渐地消隐和遁迹了。1981年之后,我们看到了朦胧诗日趋沦丧的迹向,诗的崇高感已成了与生命不相联属的矫情,诗人们在纷纷美化自己的同时,而去扮演一个角色、制造一种范式,就如一位朦胧诗的代表人物所说:“美化自己的倾向,是朦胧诗人们所坚持的最顽固的一个倾向。”“显然,真正的解放,不仅限于让世俗的生活摆脱一个美学的压迫,而是让人自身从‘美化自己’的精神梏桎中挣脱出来”⑴。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第三代诗人看来,这种沦丧的诗学在朦胧诗的继承者那里,几乎被推到了极致。他们同样具有朦胧诗人的责任感、忧患感、优雅感和崇高感,他们以文化入诗,简直就是在制造庄重、典雅的文化殿堂;他们故作博学与高深,由此,人们完全可以想见他们一边读书,一边写诗的神秘姿态。
就较深刻的时代背景而言,一个悲剧性的年代结束之后,自然仍将伴随着一个时期的惊悸、痛苦和回忆,尤其是这种悲剧作为个人的独特体验时就更是如此。然而,回忆毕竟是属于过往的故事,面对新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总是被一种回忆的母体所牵绕,那他的心理就一定会负荷沉重的压力而与现实的生活相游离。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它只有从一种普遍的怀旧情结中解放出来,才能重新开启新的生活。第三代诗人毕竟面对着刚刚诞生的新生活的端倪,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令人悲愤的年代,因而,回忆对于他们就几乎等同于在诉说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故事,他与这个弥漫着念旧情绪的世界和艺术显得格格不入。所以,了解了两代诗人不同的经历的心理基础之后,再去直面第三代诗人的反叛时,就会感到这无疑是一场可以预料的必然事件。一份《大学生诗报》曾以《对现存诗歌审美观念的毁灭性突破》的标题宣言道:“现代派对生活的回答是--我不相信;大学生诗派是——我这样生活。”这不啻是对两代诗人不同的生活态度的最好注脚。朦胧诗人也曾经虔诚地信奉和热爱过生活,但是,当这种生活被最终认定为只是一场虚假的政治骗局之后,他们便自然产生了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对生活也便怀有彻底的戒心与怀疑,于是,“不相信这一切”就成了整整一代人所特有的心态。由不相信进而便以英雄者的姿态去反抗生活、超越生活,这就自然地显现出人格和审美的崇高感。而第三代诗人却怀着对生活的认同心理,认为人并非朦胧诗人所表现的或想象的那个样子,他并不崇高,甚至还有些卑下,或者说人既非崇高,也非卑下,他不过如此地生活着;而生活也并非总是悲剧,甚至还可以说有点喜剧性,或者说生活既非悲剧,也非喜剧,它不过如此地存在着,“就是这样”,“一切都是这样”(韩东)。他们生活着,存在着,然后写点叫做诗的东西;他们不故作什么姿态,以显得高贵和优雅,他们也不故作忧伤状,以示沉重和深刻;他们时而哭,时而笑,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他们不觉得“置身其中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⑵,他们甚至还有点热爱生活。因为“他们不以为生活欠了他们什么,他们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使命感,他们是一群小人物,是一群凡人,喝酒,抽烟,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候还酗酒,打架……他们顶顶重要的是要生活”⑶,这就是作为一代诗人的第三代诗人,这也是一群中国式的“嬉皮士”。不过,他们并不绝望,尽管这个世界并非尽如人意,可他们宁愿“撒娇”,也不愿抛弃这个世界。有人称他们是“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不可惹的一代”……我却乐意把他们称作“执着于生活的一代”。
在第三代诗人那里,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诗不再是某种典雅、堂皇的圣物,正如《别了,舒婷北岛》一文所说的,那种“高雅而且忧美”的鸟,“老是飞在高高的空中,我们仰望得脖颈已经发酸。”他们认为“文学总是在老百姓中活着,我们宁愿做平民诗人,也不要成为贵族作家。”因而,在诗人们看来,诗首先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或生命的形式,反崇高的目的,也即是使诗返归到平凡人的世界。这种平民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消解和淡化了朦胧诗那种英雄主义的崇高感,一方面使人切实地回到了人的自身。所谓平民,这里自然是指那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这是一种假借和隐指,不带过去时代的阶级对立意味。但是,平民和显贵者的基本差别还是存在的。卢梭曾经说过,人类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或生理上的,另一种则是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这里主要指的就是一种精神或心态。朦胧诗人无疑是一群精神的贵族,他们自恃为一个时代精神的代表者,而超然于芸芸众生之上。然而,第三代诗人则不同,他们既无意代表时代,也无意代表他人,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这无疑是一次美学和艺术精神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一个平民的世界突起在诗的大陆,就如一场四处漫溢的洪水,浸没了英雄和平民,高贵和低贱,伟大和渺小的界限,一切都是洪水消失之后平展无垠的大地。即使卡尔·马克思这位令人尊崇的伟人,在诗人的笔下,也显得那般平凡,他叼着雪茄,用鹅毛笔写字,字迹非常了草;他很忙,以至于满脸的大胡子,没时间刮掉;卡尔·马克思还写情诗,他没有职业,到处流浪……(见尚仲敏《卡尔·马克思》)在如此淡淡地不动声色地描述中,你还能区分哪是平民和伟人吗?在第三代诗人看来,人是什么?他不过是一个食人间烟火,有着喜怒哀乐的凡夫俗子,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这是一片平凡人的风景,潜意识的呈现和裸露,原欲的喧闹与骚动,感性的开启,情绪的漫溢,都是那般的自然、顺畅、无拘无碍。你若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留连,任何典雅和禁忌,或者诸种文化编织的罗幔,都会无声地滑落在你的脚下,任你践踏,然后抛弃,你只感觉生命是那么通体的澄明和自由,甚至被传统视为丑的东西,如今也一古脑儿的突现在你的面前,被一片艺术的光芒所照亮,化为你生命的真实状态,并与崇高构成直接的对立。这种所谓审丑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对既有文化和崇高美的亵渎,并试图最终消解它,以达到生命的本真存在。所以,当莽汉主义诗派宣称他们自己“正逐渐地变成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以为诗就是最天才的鬼想象,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时,你能说诗的崇高和诗人的崇高又能在哪里呢?我们只能说,这种丑的描述,最终既消解了诗的崇高,又消解了自我的崇高,而以一个赤裸裸的真实自我,直接地介入现实世界之中。
当然,丑的东西出现在艺术中,这并非是第三代诗所独有的,毋宁说它是历来的叛逆者们所特有的一种最便捷和激进的姿态。当那位现代画家以几撮胡须点缀蒙娜丽莎那永恒的微笑时,传统的优美便终于消失在亵渎操作过程之中。丑艺术大师波特莱尔曾经精心地描绘过病态的丑恶现实,一些不堪入目的字眼诸如“髑髅”、“妖精”、“魔鬼”和“淫妇”都纷纷出现在他的笔下,并且他还一再不厌其详地描述“吸毒、饮酒、追求肉欲、梦幻灭亡”细节,企图以此返回存在的本质层次,以艺术家的身份去面对真正的命运。第三代诗人的这类所谓审丑诗,其亵渎崇高的一个最便捷的手法,首先即是波特莱尔式的将许多具有刺激性的字眼突入到诗的高雅的殿堂。那令人作呕的粪便和厕所,使人惊悸的血污和难以忍睹的死亡,都无可遮蔽地成为诗所经常触及的细节,一句国骂“他妈的”,常常恰切地道出了生存的尴尬、无奈和令人忍俊不禁的谐谑。当诗人们以赤裸裸的自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时,我们看到了神性人格破灭后的所谓大写的人竟是如此的粗鄙、渺小和不堪一击,人的神圣庄严的面纱揭破了,一切都变得如此不可收拾,他不再温文尔雅如正人君子,倒甚至有点象一头野兽,左突右冲,将个传统的秩序踏成一片废墟。“性”这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字眼,如今也被第三代诗人拿来用作亵渎崇高的杀手锏,这种弗洛伊德式的性本能渲泄,构成了第三代诗的基本母题之一。这不独表现于一般意义上的性意识的觉醒与勃兴,而且还表现在诗中大量地出现了表示性官能的词汇、隐喻性的暗示以及一些性的过程的描述。禁忌扼制中的野性骚动,从来没有象这帮青年人一般放肆和淋漓尽致,尤其是几位女诗人的崛起,更为这性诗的潮流卷起了黑色的风暴。翟永明和唐亚平曾分别写出了《女人》和《黑色沙漠》两组诗,她们所显示的黑夜意识的滋长,一方面表现了性本能的压抑与潜隐,同时也显示了性的奔突与勃郁。作为女性诗人对其生活方式和生命意识的展示,无疑标志着他们对性禁地的超越,并开辟了又一片生命存在的领域。
诗的这种消解文化和崇高美的亵渎式实验,不仅仅在于突入了个别的丑的事物,而且一个更为深切的效应还在于初步形成了一种基本的美学范式,即反讽。“反讽”本源自古希腊戏剧中的一种角色类型,所谓“佯作无知者”,他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故意说傻话,但最后证明这些傻话均是真理,从而使对方出尽了洋相。后来这个词衍变为“讽刺”、“嘲弄”的意思。直到新批评派进而把这个概念普遍化,使之几乎成为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这里所使用的“反讽”,是在较小的意义上使用的,其基本的品格表现为嘲谑和幽默。正如莽汉主义所宣称的“莽汉主义自始至终坚持站在独特的角度从人生中感应不同的情感状态,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平常感及大范围连锁的幽默来体现当代人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极度敏感”⑷。因而,反讽的对象便是生命存在的真实图景,它在其根本的品格上呈现为荒诞的形态,即文化了的世界和人的状态的荒诞。周伦佑在谈到第三代诗人时说,他们“也有些现代性的东西,比如灵魂与肉体的普遍分裂。经常把眼睛忘在枕上。用纸牌算命。读一本名著便折断一条手臂。有时冒雨到桥上看水。有时站在头上看自己。当尾巴咬住狗转圈时,便突然感到人的可悲了”⑸。这简直就是一幅全息生命的荒诞图。在崇高化了的文化程式中,人的还原和回归自身就只有从亵渎开始,于是,他们开始嘻笑怒骂,开始嘲笑世界,亵渎神圣。李亚伟有一首著名的《中文系》,其语言的刻薄和幽默可谓达到了极致。教授们自然代表着知识和经验,也是博学和高深的象征,诗人在亵渎一种荒诞现象的同时,也嘲弄了师长们这种伟大的崇高感:“老师说过要做伟人/就得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亚伟想做伟人/想和古代的伟人一起干/他每天咳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图书馆/回到寝室后来真的咳嗽不止”。这伟人的崇高最终也只消解为令人讨厌的“咳嗽”。诗人在文化亵渎、他人亵渎的过程中,也给予自我以同样无情的嘲弄。当然,自我嘲弄更多地还是面对那种灵魂和肉体普遍分裂的“自我”,也就是那个被文化异化了的自我,“你究是谁呢/你根本就不是谁/你只是你自己的一种尴尬”。(闲梦)诗人在亵渎、嘲弄一个分裂的自我的同时,也揭破了人的荒诞的生存图景,从而露出了生命的本真世相,一个崇高化了的文化世界也便消失了。
这种野性的反讽诗呈现了其中一种平民的近乎原始的生活方式,其热烈的动态渲泄表现了与某种崇高感的对抗心态及行为。然而,平民意识更多的、大量的存在于人们琐屑的平凡的日常生命感觉之中,对其进行静态的描述是第三代诗的中心所在。即使面前对某种明显地积淀着崇高感的所谓重大事件,他们也要施行淡化处理,使之显示出平凡性,比如邵春光的《太空笔》是这样写的:“我真是祸不单行/我把钢笔弄丢的那天
美洲的航天飞机/在升空时爆炸了……/美洲的潜艇/在大西洋里打捞飞机的残骸/已经打捞两个月了/若无其事的远东编辑/依旧/不把我的《寻笔启事》登在报上/远东的报纸转载了那么多/各国首脑发往美洲的慰问电/没准其中的一封,是用/我丢失的那支笔写的。”诗人把与自己本来毫无干系的美国航天飞机的爆炸与自己偶尔丢失的一支笔相提并论,并以一连串机巧的幽默尽情地调侃,使得如此重大的事件淡化为一桩不起眼的小事,由此在淡淡的叙述中呈现出一种平民的心情。这种回到尘世中来的动人的姿态,显得格外的感人。日常的生命是最为具体和显在的,它之不同于理性所规范的另一种生活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可感性。第三代诗人既然要这样生活,他就自然不会抛却这每一个片刻和现在,无论是忧郁的、欢乐的,甚或是大喜大悲的,这一切对他都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要抓住它,享有它。这是小君的一首《过冬》:“冬天一到/开始了很长的睡眠/阳光穿过半边窗帘/唤醒你/或让你半醒半睡/你的呼吸/时有时无/象白天一样/对我讲述你安居乐业的想法/我看不见你的梦境/看不见那个象恶梦一样/追了你多年的心情/你安祥如同一个树枝/出现在冬天。”这安居乐业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通过慵懒的睡眠、阳光以及树枝般安祥的姿势表现出来,那平静地淡淡描述,透露出平凡人的心境意态。这里既没有令人肃然起敬的优雅,也没有任何高贵优越的情愫,一切都显得如此的世俗,就如每一个人身边的平凡生活一样,我们随之也消失了所谓的庄严与崇高,而被一片世俗的潮流所裹挟,进而还原到一个真正的存在的世界。
非意象:消解文化的艺术方式
所谓意象,在一定意义上可理解为文化语义的可感受形式,即意义与物象的有机交合体。以往的诗歌,大都以营造意象作为基本的归宿,尤其是朦胧诗或文化诗,更是以意象作为诗的基本单位和思想方式,他们只是把某种观念寄寓给一个客观的对应物,然后如积木般的组合连缀,构成一个无限的智力空间。这种意象的张力场既有对读者的召唤效应,同时又使你不得不每每停下来,在其象征和隐喻的背后,作些深度意义的追寻。因此,阅读事实上已变成了一种释义活动。当这种释义操作愈来愈使人疲惫不支的时候,“Pass”也就成了一种普遍的情绪和行为,“别了,舒婷北岛。我们不仅想告别你们的诗意识,而且想告别你们的诗形式。你们这个意象,那个具象,这个象征,那个浪漫,是不是写得太累了?你们月亮呀,船呀,溪呀,窗口呀,花呀,雪呀,风呀,泪呀,是不是写得太玄了?我们只想通过汉文字流动出我们的意识,我们追求这种流动的语感、诗感、节奏感,哪怕是大白话”⑹。大学生诗派更是主张“对语言的再处理——消灭意象!它直通通地说出它想说的,它不在乎语言的变形,而只追求语言的硬度”⑺。这时所说的“语言的硬度”,在我看来,即是指语言的本色、自然和单纯性。下面是韩东的一首《你见过大海》:“你见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然后见到它/就是这样/你见到了大海/并想象过它/可你不是/一个水手/就是这样/你想象过大海/你见过大海/也许你还喜欢大海/顶多是这样/你见过大海/你也想象过大海/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读完这首诗,或许你会产生一种“一无所获”的困扰,然而困扰之后,只要你能逃离传统的心态,稍稍转换一下视角,就会得到这样的启示:一切不过如此罢了。这首诗已失去了任何美丽的背景和深度,它只是以大体相近的语句反复回环,以此显现大海的单纯性、表象性:大海就是大海,它是湛兰色的、咸咸的一种液体,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这里意象消失了,意义又能在哪里呢?你尽可以诅咒它,但却不能否认这是一种新的感受。
第三代诗的非意象,本质上便是这种消解意义、消解文化的过程。诗由此真正地回到了语言自身,这是诗人们反抗文化的最基本的契入点和出发点,也是一次语言的觉醒与革命。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诗歌是以失去自身和语言为代价的,即便是朦胧诗人,也仅仅只是回到以语词作为营造意象的基点,这还不是能说真正地回到了自足的语言本体。因此,在这种背景上,第三代诗人语言意识的觉醒就自然地带有历史意义。这不仅表现在诗人们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语言之于诗的根本性地位,而且对此也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表述。韩东曾说过:“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即是要把语言从一切功利观中解放出来,使呈现自身,这个‘语言自身’早已存在,但只有在诗歌中它才成为了唯一的经验对象”⑻。这是针对诗的终极形态而言的,它最终只能是“语言自身”的呈现,而不该是超越语言之外的任何其它什么,比如理念或某种功利观等等,这就从理论上界定了诗只是一种语言的自足体,语言之外是没有诗的。另有一些诗人(如非非诗派)以诗的起始作为出发点,其理论表述是:“诗从语言开始”,最终的指向是“超语义”。但无论如何,诗也不能走到语言这外。因此,这两种诗观表面上看似矛盾,然本质上又都是同一的,二者从各自的一极互为限定和补充,或许最为完满的表述应为:“诗从语言开始,至语言为止”。这样就使语言全然回归自身而成为自足的诗歌本体。
人居住在这个充分象征化、变形化和语义化的世界之中,诗人的非意象就自然每时每刻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困扰。然而可喜的是,摆脱这一切已成为第三代诗人的信条,因此,诗的语言实验便从各种不同的侧面汇入了诗的实验大潮。
反象征:艺术的象征无疑构成了朦胧诗的意象核心。所谓象征,按照劳·坡林的定义应该是“一个东西的含义大于其自身。”这就是说,一个东西绝不意味着只是这个东西本身。比如当你面对几片款款飘落的秋叶时,你决不可以为这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即谓“秋风落叶”。事实上决没有这么简单,它一定象征着某种心境:颓丧、寂寞、如秋叶般凄凉,这就由此建立起了精神世界与自然界的联系,使观念或情绪化为一片自然的风景。以往的传统艺术尤其是现代主义视象征为基本的艺术方法,,波特莱尔式的“象征的森林”和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或者“玫瑰的薰香”,均是这种理论的形象化表述。谈论现代主义.不能不谈论象征,朦胧诗自然也如此。这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其主旨已经超出了语言之外。第三代诗人要回到语言,回到事物本身,就不能不以象征作为反叛的对象了。车前子的《三原色》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反抗的心态。“我”用三支蜡笔,在白纸上画了歪歪扭扭的三条线,可这在大人们看来,却是三条道路的象征,而“我听不懂/(讲些什么呵?)”,又依照自己的喜欢画了三只圆圈。这里,诗人以“我”稚拙的迷惑拒绝了所谓深度的象征,在他看来,“我”只不过是画着自己所喜欢的线条和圆圈而已,并没有其它的深层的内蕴。“没有任何负担”的白纸、三支原色的蜡笔和天真稚气的童心都呈现出人与物的单纯性和本原性,而这一切又是通过纯静的语言表现出来的。
反变形:所谓变形,可以理解为诗中所见的事物已经远离了自然界中自在着的事物的样子,它是经诗人的主体理性对自然界的事物进行重新组接、塑造的再生物。变形意象和象征意意象一样,都是心理世界的一种表现形态,只不过象征并没有失去自然事物的表现性,它的表现是在其背后隐喻着的;而变形意象的表现却是在自身中显现出来的。当诗人写那“微微隆起的枝柯在呻吟着……”时,诗人已将树变形为人了,并赋予给它一种痛苦难当的姿式和声音。事实上,树既非人,当然也没有任何痛苦,树只是树,并在那里生长着,一阵风吹过,它或许会摇曳起来,亦或发出轻微的响动,然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无生命的,而赋予它生命,无疑是诗人的一种矫饰,他只是一味地张扬个体理性,并以对立的方式对待役使自然,使之失去了本真的面目。反变形,也即是回到事物的原生态,回到语言直接描述事物的单纯性,正如韩东所说,诗歌既不是语言的变形,也不是变形了的语言,它只是语言自身。反诗派的主张者也进行了一系列反变形的语言实验,在他们看来,“诗人一旦进入了触动状态,诗人只需要对触动状态进行直接描写,描写的结果即属于反诗”。这种直接描写的真正的诗状态,或说“诗人被触动和震撼的状态,先于一切诗感受方式”
⑼,它自然呈现,既是语言的原生态,也是事物的原生态。如阿吾《三个一样的杯子》:“你有三个一样的杯子/你原先有四个一样的杯子/你一次激动/你挥手打破了一个/现在三个一样的杯子/两个在桌子上/一个在你手里/手里的一个装着茶/茶是故乡茶。”一切都那么客观而冷静地描述出来,语言既不辉煌,也没有任何变异性;事物只是在单纯的语言中裸露,既不象征什么,也不表现什么,它只是和“你”一样地存在于那里,并且交往着,共存着。
在第三代诗中,世界和人被还原到如此纯粹的存在状态,它不再是有心营构的意象,而是语言所自动呈现的印象、感觉或“被再听”(杨黎)的声音。这被诗人们称作“语感”的东西,虽然在各自的表述中不尽相同,或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或视为“超语义”的一种声音,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均视“语感”为自足的语言本体,这足以构成了与意象范畴的根本对立。如果说意象表现了一种语词意识的话,那么语感则是一种语句意识,这又构成了艺术方法即意象的修辞和语感的描述的差异,修辞总是人为的装饰,而描述则是自在的天然。故而,语感描述的结果便是一种新鲜的语句的诞生,有人称这种语句为“口语”,如在自然、顺畅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同它,但“口语”决没有这么纯粹、透明,并且,它决不是那种日常的会话语言,它既没有那种语言的交际功利性,也不象那种语言的如此模式化,它是更接近于生命的一种自然的声音。“就象是我们身内的血”,“是我们心里流淌的那个东西,禁不住流到了纸上,在纸上活动起来”⑽。
眼下还存在着一种“超语义”的语言实验,这主要表现于非非主义的诗歌方法之中。如果说“非意象”主要着眼于反对那种有意图的诗歌,而最终返回到语言的本体,那么,“超语义”则企望在语言自身展开一次革命,从而彻底地超越语义关联。这个命题在清除语言的意图时虽然已经有所涉及,但那时还不至于怀疑语言自身的语义性,“超语义”者这样做了,并且已初露端倪。目前看来,这虽然还只是一个美妙的幻觉,但毕竟为接近它提供了一种启示。这个问题需作专题论述,因而在此只作如是说。
这一切,终究还得归结第三代诗的非文化态度,无论是非崇高,还是非意象,都是消解文化的一种方式或文化消解后的一种形态,当你习惯了一幅文化的世界之全,再去窥视一下非文化的风景,这本身就是相当的动人的,更何况,另一个世界正在款款地向我们展开。至于第三代诗的未来,曾有人预言过它的并不乐观的结局,而我却乐意看到它的辉煌的过程。因为未来到底如何,我只能说:不知道。我只相信,一切均孕育在过程之中。
1988、10
注:
(1) 梁小斌《诗人的崩溃》,见《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深圳青年报》、《诗歌报》主办。
(2) 于坚语。见《当代青年》1988年6期。
(3) 参阅《大学生诗报》(1985、6)及徐敬亚《圭臬之死》,见《鸭绿江》1988年7、8期。
(4) 见《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深圳青年报》、《诗歌报》主办。
(5)
周伦佑〈第二次诗浪潮与新的挑战〉,见《艺术广角》1988年3期。
(6) 程蔚东《别了,舒婷北岛》。
(7) 见《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深圳青年报》、《诗歌报》主办。
(8) 韩东《自传与诗见》,见《诗歌报》1988年7月6日。
(9)
阿吾《诗的自救,从变形到不变形》,见《艺术广角》1988年3期。
(10) 尚仲敏《为口语诗辩护》,见《诗歌报》1987年12月21日。
【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