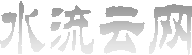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
孙基林 ◇
“他们”论
这是个阳光明媚、花朵灿烂的季节。1984年春天,大学毕业后曾流浪至八百里秦川的韩东,这时已落脚在石头城下。或许,他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预感:这一年,诗界所面临的新的转机已势在必然。于是,他四下联络各地有着相同或近似倾向的文朋诗友,组成了“他们”文学社,并于1985年三月创办了《他们》。虽然这是一个不只是诗歌,而且也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团体(如新潮小说的代表人物马原、苏童等就曾是“他们”文学社的一员),但“他们”主要的和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却是在诗歌方面。《他们》迄今已出版了四期,发表了几百首诗歌,其主要作者有:韩东、于坚、小君、丁当、吕德安、王寅、陆亿敏、小海、普珉、于小韦等。“他们”这一群曾被尚仲敏誉为“第二次浪潮”或“第三代”诗歌的主流,事实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
论及“他们”和“第三代”诗人,韩东自然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潮头人物。大概是在1981年的春天,他的组诗《山》在《青春》上获奖以后,年仅19岁的韩东就成了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当然,他的诗歌那时仍免不了时代风尚的影响,就说《山》所表现的也不过是北岛式的悲剧英雄主义品格和姿态。可是不久,韩东变了,变得更像他自己了。他在默默地寻觅着一条与北岛们全然不同的路,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那个英雄崇拜狂的年代里,他却毅然出走,回到了平民的世界,富丽堂皇的修辞也变而为新鲜自然的口语。于是,一个新的诗大陆便渐露端倪,他以《山民》等一些佳作显示了最初探索的实绩。以后的数年间,他卓然独步于自己的路上,并与其他少数有着相似追求的诗人一起,引起了诗坛的一阵阵骚动与哗变,以至最终酿成了新诗的又一次超越与变异。这在每一个稍稍关注诗坛的人都会是有目共睹的。这里我们不能对韩东的诗作做一个全面的描述,只好汇入下述的综论之中了。
“他们”是一个注重作品自身的诗歌群落,因而很少顾及诗的理论的发言。当然,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他们对于理论的忽略和蔑视,正如他们所说的:“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的诗歌就是我们最好的发言,我们不蔑视任何理论或哲学的思考,只是我们不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此。”(1)可见,他们认为作品依然是先于理论的第一位的东西,而理论只是作品之后的总结和阐发。在《他们》第三期的封页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总结性的艺术自释:
“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我们是在完全无依靠的情况下面对世界和诗歌的,虽然在我们的身上投射着各种各样观念的光辉。但是我们不想,也不可能用这些观念去代替我们和世界(包括诗歌)的关系。世界就在我们的面前,伸手可及。我们不会因为某种理论的认可而自信起来,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不在我们手中,即使有千万条理由,我们也不会相信它。相反,如果这个世界已经在我们的手中,又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觉得这是不真实的呢?”(2)
这就是“他们”诗歌的理论基础,它告诉人们:“他们”在追求着什么?首先,他们主张返回本体,即返回诗本与人本。他们反对任何理性观念的干预,而只关心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的诗歌本身。而这种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的美感又是诗人的生命形式。因而,返回诗歌本体也即返回诗人的生命本体,从这种意义上说,诗本和人本是统一的。其次,“他们”注重感觉、体验和本能的力量。生命表现为个人的感觉形式和体验过程,诗人联接世界(包括诗歌)的唯一通道就是感觉体验。而这种感觉体验,又内蕴着本能的潜在原力而与理性观念无缘。最后,“他们”追求世界的真实性、客观性,并力求呈现客观存在着的世界自身,以完成使诗歌返回真实的艺术使命。当我们以此观照他们的诗歌作品时,便会发现这种理论与实践已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与吻合。
(一)返回本体,诗与生命的双重醒悟
在“他们”看来,文学的流浪是历史性的,自然诗歌也是如此。一如永远流浪的吉普赛人,他们始终歌舞在没有尽头的路上,压根就没有返回家园的渴望,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家园。这种诗的流浪导致了现代诗的长期的失落,即诗不是诗本身,而只是诗之外的某种东西。若从本质上追溯,这又是以诗人个人生命的失落为前提的。现代诗人均远离自己的生命而去扮演一种社会的世相,这是与时代紧密相联的诗人的宿命。那“集香木自焚”的凤凰,只不过是社会和自我的象征。诗人与社会同浮升、共沉沦,因而他只能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不独郭沫若如此,即使那些过多地含蕴着个人情绪的诗人,也多少涵映着时代的表征,比如某种忧患意识或浪漫英雄的崇高感等,这事实上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社会个体。北岛们的觉醒是局部的,当他们在横遭毁灭的废墟般的原野上站起来之后,他们首先呼唤和寻找的是自我的伦理价值。因而,这还只是理性的观念“自我”,是大写的“人”字,而游离于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因此,在“他们”看来,北岛们普遍地陷入一种理性的幻觉之中,假定或相信“自我”是无所不能的英雄,而失却了真实存在的生命状态。诗人们或去造仿于西方现代的艺术,寻觅着谓之于时尚的人性观念,然后制作具有启示录般的艺术;或去登临圣殿古迹,翻阅高文典册,重现种族的人格范式。这都无疑在向彼岸世界寻找“自我”的归宿,而结果呢?人在这种自我的假象中淹没了自在的血肉生命。韩东在一篇文章中曾分析了中国人的三个世俗角色,他认为:中国人常被理解为卓越的政治动物、稀奇的文化动物和深刻的历史动物,而我们以往的诗歌即是这三种角色的扮相。只有在全然摆脱了这三种世俗角色之后,诗歌才能真正回到诗歌本身。
(3)可见,韩东所说的摆脱三个世俗角色,意在重新界定诗人和诗的范围。诗人是什么?诗是什么?这个最古老和最本源的命题,如今却又变得这般陌生和新鲜。当新一代诗人的本体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它自然被上升到首要的位置。诗人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每一个诗人最内在的意识。如若说诗人是什么,毋宁说诗首先不是什么。他不是一种政治的动物、历史的动物和文化的动物,然后即可说,诗人就是他所是的那个东西,即他是以诗安身立命的那类人。因而,诗一定与诗人的生命有关,它是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的生命体,这种语言的运动被诗人称作“生命的呼吸”,因此,诗只有切近生命的本体,才具有最高的价值。正如韩东所说:“一首诗的审美价值也许就在于此,它必须是活的东西,必须是生命”。(4)“写诗似乎不单单是技巧和心智的活动,它和诗的整个生命有关。”(5)从这种意义上说,诗和生命是同一的、互为存在的,诗人回到了个人的生命本体,事实上也即回到了诗本体。既然诗是诗人生命的形式,那么,如离开诗人活生生的生命自身,诗也就无从谈起。就如崖边岸畔那一株春风中飘摇的垂柳,其翠嫩欲滴的点点鹅黄是由生命自然而然绽放出的,它是树的生命的存在形式。我们不能设想盆柳也会长出芽苞来,它顶多只能是人工的装饰而已。有一种诗也是这样,它只是外在观念的人为对应物,与诗人的生命毫无关系。而“他们”这一群诗人则把诗看作是从生命的根部生长出来的语言流,它既是生命的感觉,又是生命和语言的同构。这里牵涉到如何认识生命与语言的关系。当诗人的生命意识凸现出来之后,能不能内充于一种自然的形式,以便展现真实的生命形态,这最终仍要归结到诗的语言。因为诗人的生命形式只能是诗的语言,一如画家的生命形式只能是线条和色彩,舞蹈家的生命形式只能是舞姿和动作一样,这是毫无疑义的。只是语言是否显示一种生命的延伸,这却有着大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生命的语言呈现是自然的而非装饰性的,自然的语言是一种生命的感觉,而装饰性的语言却是意图的还原。
韩东所谓“诗到语言为止”的“语言”,即是这种生命的感觉语言,这是诗人们返回诗歌本体和生命本体的最本质的描述。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6)。“他们”这一群则会说:语言的界限则意味着我的生命的界限。当然,这语言绝不是一般大众的普通交际语言。如上所述,它是一种生命的感觉语言,或称为纯语言。它是生命自然呈现的描述形态,诗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语感”。于坚说:“这些诗再次回到语言本身。它不是某种意义的载体。它是一种流动的语感。”(7)他还说:“在诗歌中,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的有意味的形式,读者在诗中被触动的也正是语感,而不是别的”。(8)韩东也说:“诗人的语感既不是语言意义上的语言,也不是语言中的语感,更不是那种僵死的语气和事后总结出来的行文特点。诗人的语感一定和生命有关,而且全部的存在根据就是生命。”(9)这种语感意识的觉悟,可说是对传统的语言意识的一次反拨与革命。正如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罗朗·巴尔特所说:古典主义诗歌“不论怎样,都使用唯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反映出精神世界的永恒范畴”,“因此,它无损于语言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古典主义的信条。”(10)所谓“精神世界的永恒范畴”,即“精神的某种普遍范式”,正是这种“普遍性”构成了语言的统一性。中国的传统诗也是如此,它是按照某种普遍的理念对符号性语言的编码处理,语言中根本缺乏的是诗人的生命意味和个性品格。诗人们语感意识的自觉是诗的自觉时代的开始,而这种语感意识又是和生命意识同时呈现的。因而,返回诗本体和生命本体便达成了一致和同一。
虽然诗人们并没有给予语感一种经典性的界说,但我们仍可从中捕捉到其基本的内核。所谓语感,即是语言自动呈现的一种生命的感觉状态或者说生命自动呈现的一种语言状态,它具体表现为语音和语象所产生的语境,正是这种语境构成了诗人生命的存在形式。这里是普珉的《丧失于风》,所描述的即是生命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和感觉状态:“这么多年了
我望着天空/云来云往/千百种声响/起自草丛与树林中/超自灰色的路上/可我无法讲述风/这么多年我坐在广场/或身在密室
耳朵追寻着/令人绝望的声响/最后却渴望一场暴雨/或一次死亡/把我覆盖/因为我无法想象风……”读后,你无须去索求什么意图,你只会感觉它整个儿是充满生命意味的语感,从中似乎听到了那生命的有节奏的呼吸和起伏,看到了那日常生命的模样和姿态。如果离开了这质朴而富于感觉的描述语言,我们还能触摸到那本真的生命面目吗?因此,这语感,既是诗感,也是生命感。
(二)感觉与过程:诗和生命的存在形式
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关心作为个人对于世界的感受与体验以及流淌在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正是基于这种认同,他们的诗呈现为感觉过程的描述特征,这或许也是诗与生命得以存在的基本方式吧。人每时每刻都生存于自己的生命感觉之中,因而,感觉世界是诗人生命的本真世相。每次鲜活的感觉都是独特的、一次性的生命体验,它非源生于纹饰成普遍理念的一块历史的石头或未来的云霓,而是从现时生命的过程中摇曳出的一丝明火的烛光,烛照着普通人日常而平凡的灵魂。从“他们”的大量诗作中,我们看到了这芸芸众生的生命本色。他们被鲜活的感觉涌流裹挟着,既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既定的意图,只是感觉着,行动着,以此显示生命的存在;而感觉的描述也只是描述而已,它既不改变什么,也不含任何从外部附加的意义,一切都是本来的面目,一切都是原初的印象和感觉。韩东有一首《下棋的男人》,诗人只以冷态的口吻描述着两个在灯下下棋的男人:一个头戴鸭舌帽,另一个手上着火,鼻孔冒烟。这期间周围的环境很寂静,就如中午时分的村庄,一声鸟鸣也显得那般嘹亮。这种日常的情景恐怕是随处可见的,诗人对此并没有寄寓什么思想,他只是把此刻自我的生命显现在日常情景的感觉描述中,以此获得一次生动的体验过程,从而丰盈无限的生命内涵。
事实上,生命的时间即是感觉的时间。类属的生命是循环往复的、无限永恒的,而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存在,它具体展开为一个个的感觉瞬间。而诗便是这种瞬间感觉的复合状态,是不可重复的生命体验过程,它在时空上表现为“此时此地”,即对现时的感觉过程的描述。于坚有这样一首诗,即《在旅途中不要错过机会》,他告诫人们要抓住一切机会,去体验此时此地的生命过程:你不要错过一片树林,要到林子里躺上一阵,望望天空;你也不要错过一个生人,要找个借口,问问路,和他聊聊……倘若错过了这片树林和这个生人,情况可就不同,生命便失去应有的过程、内容和色彩而显得黯然。是的,人的一生就是一段短暂的生命旅途,每一片树林、每一个生人都是生命可供栖息体验的对象,只有抓住眼下每一个感觉的时刻,才能真正聆听到生命的音乐。
这种“过程意识”在那些描述感觉的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过程意识的核心便是弃绝对“过去”与“未来”的幻觉而回到“现在”,也即一种“现在意识”。在三维时间的绵延中,只有现在才是现实的、存在着的,除此可说一无所有。过去永远地消逝了,而未来又是永远地缺席,我们既不能生存在过去之中,也不能生存在未来之中,人的生命只能是永远的“现在时”。所以韩东说:“那怕是你经历过的时间,它一旦过去,也就成了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了。我们无法判断哪些东西是出于梦境,哪些东西是实际发生了的。但对于一个人的此时此地,二者并无区分的必要。”(11)诗人还说:“‘根’是没有的。它是对往事的幻觉,一种解释方式。对未来,我们真的一无所有”。(12)
他早些时候的那首《山民》,便最早表露了这种意识。“他”曾渴盼眺望山之外那片蔚蓝色的海洋,然而,外在于个人生命的遥远无尽的浮士德式的寻求,已使他感到疲惫了。未来无疑是不属于他的,而祖先的过去也不可回溯,他只是关注现在的生存。为此,他为现在不能体验那种面临大海的喜悦而深感遗憾。这无疑是一种新观念或新情感的兆头,之后,诗人们愈来愈关注此时此地的生命体验,并自然地呈现为诗的感觉过程的描述。
在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的背后,我们注意到传统的民族心态渐渐地剥离和远去了。我们的民族历来有着异乎寻常的历史崇拜情结,它对于过去的关心远比其它民族显得热烈。当那文化“寻根”的一群以反省的目光回溯过往时,最终也不免以崇仰的心理返归于历史的温馨之中。可历史对我们又能意味着什么呢?它只能说曾经作为人类的“现在”存在过,可如今它毕竟消失了,消失了就不会再生。时间决不是一个点的简单的循环,它既不会走到终点,也不会回到起点,它是无始无终的“现在”的过程。因而,对过去的回归必定是以牺牲“现在”为代价的。事情还并非仅仅到此为止,本来,幸福的人生应从眼下开始,可人们却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可结果呢?人们失却了“现在”,犹如被无端地抛置于一片生存的废墟之上,变成了无时间性也即无生命的悬置物。因为“他”既失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也便荡然无存。在“他们”看来,我们的诗歌甚至包括朦胧诗,在很大程度上所呈现的即是这种非生命状态。就如于坚所说,这是一种“病态的诗歌”,“它使人忧心忡忡,怀着世纪末的感伤或狂人式的梦幻,它使人以为,人所置身其中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在某个时代(往昔的或未来的)、某个不为人所知的地点存在着某种‘美好的日子’,只有不在身边、遥远的东西才值得憧憬,而现在是那么‘不幸’,多么缺乏‘诗意’。”(13)以“他们”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终于告别了这种远离生命存在的诗歌形式。他们热爱人生,热爱“人自己一生只有一次的人生”,因为“唯有这种人生,才使生命具有存在的意义”(14)。唯有这种人生,也才能使人们更执着于“现在”的生存。生命的全部现实只是“现在”,即使它有着些许的痛苦和颓丧,只要它是真实的,就是值得去过的。这是“他们”的诗歌关注感觉与过程的深刻思想基础。
(三)单纯性:语词及语象的存在形态
在人们的先验意识中,似乎诗必然就是语言的繁丽、结构的堂皇和修辞的摇曳多姿,诗美的全部奥妙也在于此,否则,便不是诗。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便是这种意识的终极表述。就如意象派诗人终生要创造一个意象一样,杜甫式的诗人则要倾其一生创造一种惊人的词语。于是,精心推敲字词、修饰语句、装点结构,便渐渐酿成了一种诗的装饰风潮。白话诗兴起之后,这种风潮并没有止息,直至朦胧诗,为这种观念提供了一种典型的现代诗语体。然“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起而淡化修辞、弃绝装饰,提倡“归真返朴”,这便开启了另一种语言或语象形态。所谓“归真”,即是回到真实的生命状态;而“返朴”,便是返回朴素本色,返回生命的最原始感觉。“归真返朴”是一种无技巧的单纯境界,然而,这又是最大的技巧,就如老子所谓最大的声音是没有声音、最大的形象是没有形象一样,一切都浑然于一片单纯的化境之中。
“他们”的诗是语言的单纯呈现,因而如口语般的自然亲切。这里所说的“口语”,决不是那种日常的会话语言,因为那只是浮泛于生命表层的消息性语言,因而不能呈现生命的隐秘层次。“他们”诗的语言是内蕴着生命的原初感觉和意味的,这是它与日常会话语言的根本区别,或许称之为“语感”更为恰切一些。他们呈现了这种语言,不是一种机遇或理性的设计,而是一种自然和本质。就如朦胧诗人必然选择幽深的意象一样,“他们”也必然呈现单纯的语感。朦胧诗表现的是一种超越性,因而诗人是不在场的,他只是躲在幕后,着意编织与意图对应的自然事物,并组成超越此时此地的意象群落,从而引渡自己到达那理想的彼岸。而“他们”的诗本身就是生命的形式,是生命的感觉和过程。诗人作为生命的存在,自然是出场的,他与诗同在,与语言同在,他无须编织和组合,也无须引渡,他就是他此时此地感觉着的行动和呼吸。就如我们随时可目睹他的一种行动和姿态一样,我们也随时可听到诗人的生命或灵魂自身涌动出来的一连串语感,它流在了纸上,于是就产生了诗。一切都是这般的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刻意操作,但却能以感觉和语言的单纯震颤你,使你觉得它是美的,是诗的。这是韩东的《明月降临》:“月亮/你在窗外/在空中/在所有的屋顶之上/今晚特别大/你很高/高不出我的窗框/你很大/很明亮/肤色金黄/我们认识已经很久/是你吗?你背着手/把翅膀藏在身后/注视着我/并不开口说话/你飞过的时候有一种声音/有一种光线/但是你不飞/不掉下来/在空中/静静地注视着我/无论我平躺着/还是熟睡时/都是这样/你静静地注视着我……”这是诗人某晚面对月亮时的一种叙白。诗来自生命隐秘层次的原初感觉,没有隐指,没有象征,也没有富丽堂皇的假饰,他只是自然而然地直陈着他的感觉和印象,即使把月亮拟人化,也是那般的稚气和纯真。在这里,一切的面具和深度均消失了,诗歌裸露出语言和感觉的单纯来。这是真正的诗的白话,透过白话般的单纯,我们似乎听到了纯净的生命的声音,看到了裸露的生命真正的面目。
“他们”诗歌的单纯性,不仅表现为语词的单纯,而且还呈现出语言再现事物即语象的单纯,这种单纯性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客观地呈现物象形态。他们不仅客观地描述外部世界,而且也把生命自身作为客观的物来对待,即是说,生命不再有主观性而带有了物的特点。所以有人称他们的诗为“客观诗”。诗人不是一位万能的上帝,他既不能主宰事物,同时也不能主宰自己,这或许就是他们的诗歌呈现“冷态”的一个原因。他们淡化了以人为本位的理性主义思想,而把人与物平等看待,这样既回到了事物本身,也回到了生命本身,恢复了事物和人的真实性、客观性。并且在此可以见出他们的诗歌与朦胧诗发生了明显的错位。朦胧诗的母题是“表现自我”,因而,不仅诗中的自我是一种主观性理念,就是物也带有鲜明的主体意向。所以说,朦胧诗是一种主观性的意象结构,其重心在于主观自我的理性表现。这与诗人怀有的象征主义观念有关,他们总把自然看作一座与主观理念相对应的象征森林,因而,自然的世界也就变成了主观的世界。而“他们”的诗则是一种客观性的语象结构,诗人们追求的是“回到事物本身”的事实。这种观念根源于自然和个人生命的单纯性、客观性,“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别的”,这是“他们”的信条。因而,在他们的诗中,我们便看到了一片自在的客观风景,一丛野花,总是与一壁静寂的石崖作伴,时而有几朵流云飘曳而去,然后裸露出天空的湛蓝;或许你听到一阵自然的风声,轻轻掠过哗哗作响的树林以及清清的河水漾起涟漪……这一切,都是自然构成的自律性网络世界,“他们”的诗常常呈现这种自然的自在性。有时他们也展现人的行为,一个动势,一种姿态,以及动作前后相继的时间过程,都自在地流动出来,而没有丝毫主观的变异。这是一种物与人存在的真实性,“他们”诗的价值就在于对这种真实性的寻求。
当然,“他们”的诗并没有彻底摆脱人与自然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不是理性的对待态度,而是一种感觉方式。感觉最接近于事物的原生性,也最接近于生命本身,因而,它是诗和生命的最基本形式,语言或语象的单纯概源于此。
“他们”的诗歌毕竟给诗坛带来了一种新的声音和意味。它促成了诗和生命的双重醒悟,使诗真正地回到了诗和生命自身。当然,这只是针对某些优秀的作品而言的。对于另外一些作品,并非均出于如此的自觉,因为它们不是基于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而只是为了模仿某种口吻,某种声音或某种外在的形式,根本缺乏的是诗的内在灵魂。自然,这不应全然归罪于“他们”,说到底还是模仿者的根性所致。他们只注意到了“他们”诗歌的单纯性、口语化倾向,而根本忽略了诗的生命的本质。因而产生了一些粗劣的仿作,并影响了“第三代”诗歌的声誉,这是应该加以剔除的。
1988、11
注释:(1)、(2)引自《他们》,1986年第3期。
(3)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见《百家》1989年第4期。
(4)见《诗刊·青春诗话》1986年11期。
(5)见唐晓渡、王家新编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198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
(6)[奥]路·维特根什坦:《名理论》,张申府译,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7)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见《诗歌报》,1988年7月4日2版。
(8)、(9)引自《现代诗歌二人谈》,见《云南文艺通讯》,1986年9期。
(10)见杨远宏:《现代诗对语言、言语格局的触犯》。
(11)引自《诗刊·青春诗话》,载《诗刊》1985年第9期。
(12)引自韩东的一则诗论。见韩东给作者的一份手写稿。
(13)、(14)引自《当代青年》1988年第6期。
【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