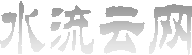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
孙基林 ◇
“非非”论
5月4日,这绝非一个偶然的巧合,它意味着一种选择,一种继往开来的文化重建意识的延续。1986年5月4日,“非非”就在这个吉日良辰里开始了它的生涯。之后,它以一系列理论和诗歌作品凸现于诗坛,显示了新诗史上最具理性的诗歌实验现象。惟因最具理性,所以它的理论受到了众人的注目。事实上也是如此,“非非”的理论远远走在了作品的前面,因而,给人们的心理留下了不尽的期待或遗憾。这或许也是“非非”同仁们所乐于认同的吧!
“非非主义”社团创办了《非非》杂志和《非非评论》报,前者已出版了四期,后者出版了二期。“非非”的主要成员有:周伦佑、蓝马、杨黎、何小竹、刘涛、小安等,原是大学生诗派的尚仲敏,“莽汉主义”诗派的李亚伟,浙江“极端主义”团体的余刚、梁晓明等人,后来也都加入了“非非”,“乃前文化思维之对之象、形式、内容、方法、过程、途径、结果的总的原则性的称谓。也是对宇宙的本来面目的‘本质性描述’。非非,不是‘不是’的”(1)。看来这是极具理性的一种阐释和描述。
(一)前文化还原及其诗歌方法
“非非主义”反对唯文化的一种方式,就是超越文化,为此,他们提出了前文化理论。“非非主义”者认为,“文化”只不过是一种“人类行为”——人类作为社会化的群体对宇宙万事万物进行利于人类的操作,而将宇宙万事万物及其相互关系施以符号化处理的一种人类行为。其结果便带来了一个“符号的世界”、“语义的世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已变成一种文化的假象,它的最大危险就在于使人们一眼就把世界看成是“语义中的那样子”。而真正本源的宇宙却不是这样,它是一种“前文化”的存在状态。所谓“前文化”,并不是一种史前文化,也不是任何其它文化或潜在文化,它是一种在共时和历时时态上都前于文化,并一直存在和永远存在的非文化和无法文化的思维领域,它既与宇宙同在,也与宇宙中的人同在。它与文化不同的是,文化是一种“人类行为”,而前文化则是一种“宇宙行为”,宇宙是它的“唯一的真正主体”(2)。它是以自身表现自身的自在物。
诗歌历来是最具先锋意识、最流动不居的创造性活动,因其是创造的,所以才是前文化的。而只有彻底摆脱这个符号化、语义化了的世界,才能真正地实现“前文化还原”。为此,“非非主义”者提出了前文化还原的三种方法,即感觉还原、意识还原和语言还原(3)。
感觉还原——诗人生活在一个文化了的世界之上,因而,一种语义的方式阻隔了他与世界的本源联系,只有消除感觉活动中的这种语义障碍,诗人才能真正直接地与世界接触。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感觉还原”。所谓“还原”,即是回还到原初的感觉,这是彻底摒除了文化语义的感觉,也可称为直觉。真正的艺术作品是直觉的,它不负载着任何本身以外的东西,就如那些由“画面本身讲述着画面本身”(4)的绘画一样,我们所感觉的也只是画面自身,而不是别的什么。
意识还原——人的意识是由直觉产生的,这是一种原初意识。可在一切都语义化了的世界之中,诗人的直觉体验很难直接地到达意识,因为它往往被共同经验所牵绕,在其途中遭到语义的阻隔和参预。比如,当你体验着一种痛苦时,很可能突入关于痛苦的理性分析,诸如痛苦的原因、程度以及痛苦中的思想演绎等。要是诗人,恐怕还会联想到别人所描述的痛苦的样态,这样出现的意识很可能远离了直觉体验的痛苦本身。因而,只有彻底摒除了语义网络的种种界定,直觉体验才能直接地呈现为原初的意识,这就是所谓的“意识还原”。还原后的意识,是毫无语义界定的纯意识,或者“灵”,由此展开的活动,便是“灵感”活动。
语言还原——与文化相对应的,便是一种文化语言,这种语言都带有固定的语义结构,它是一种载体,总是被约定地代表着或表达着“别的什么”。而前文化语言是一种语言本体,它不代表也不表达任何“别的什么”,它只表现着它自身。所谓“语言还原”,即是还原到前文化语言。什么样的语言才是前文化语言呢?蓝马在文章中举例说,“风”(英语Wind)“太阳”(英语Sun)等名词都是文化语言,在不同的民族中虽然有着不同的约定程序,但所指却是一致的;而各种各样的风本身才是前文化语言,它本来没有语义,但确实又能使你知道无须言喻的那个东西。“太阳”也是一样,它被约定来代表天上浮游的“明晃晃的那东西”,作为“明晃晃的那东西”表现着“明晃晃的那东西”自己时,它所拥有的和可能拥有的种种表现就是前文化语言(5)。由此可见,所谓语言还原,也就是还原到“事物本身”。
诗人如此地做了三度还原之后,据说语义和文化感便消失了,“被文化(语义界定)之网膨胀起来的意识屏幕象孤帆一样远远离去,只剩下飘来荡去的直觉”,我们仿佛被这直觉涌动着而飞升飘荡,就象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岁月已是那般的遥远了,可“天空还活着,天空还在想;土地也活着,土地也在想”,我们来到古罗马遗址上,似乎看到那高高大大的石柱也是这样,它们一直在活着,并且一直在想……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在活着,都在想,它们充满着自足的生命,各自以自身表现自身,以自身证明自身(6)。这或许就是“非非主义”所追寻的前文化世界吧!
如果说“非非主义”的前文化还原,还只是为艺术创造(甚至不仅仅艺术)提供了一种方法论,那么,创造诗歌艺术的具体途径,便是“超语义”和“超表现”。前文化是诗的一种终极目的,而“超语义”和“超表现”则是它的过程及出发点。
文化是以语义的形式存在于语言之中的,因而,超语义毋宁说是一种语言的革命。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界限看作他的世界的界限,这多半指的是一种文化语言。韩东所说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语言,则指一种消除了文化语义之后的纯粹语言状态;而“非非主义”所谓“诗从语言开始”的“超语义”,企图消解和超越语言与文化的语义关联,而获得一种纯语言,也即蓝马所说的“语晕”现象。它的生成或是由于突入宇宙的一种声音,或是事物的一种图像,最终消解了有效的语义运动,使语义发生偏离、中止和丧失,产生了语言的不定性和多义性。当然,这一切终究还要归到语言,如果说“语义——是用以刻画‘文化中的那份世界’的语言要素”,那么“语晕——是用以呈现世界的‘尚未被文化部份’和‘永不被文化部份’的语言要素”(7)。非非主义是从对语言的彻底怀疑开始的,通过超语义或语晕试验,用语言超越语言,用语言反叛语言,以求最终呈现出非语义的纯语言世界。
“表现论”是西方现代艺术的一种美学形态。浪漫主义一览无余的意志和情绪的渲泄,冲决了传统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单纯“模仿”和“反映”的模式,而使表现艺术获得了一种形式。现代主义更是把“表现”作为艺术的“核心”,这是与人的主体性崇拜分不开的。中国80年代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为新时期文学进入现代主义奠定了基石。然而,这一切都是一种过往的或已有的艺术,“非非主义”要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就必须超越曾经有过的一切,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现代主义。当然,这决不意味着他们的返回,因为现实主义的“反映”模式早已成为历史,“非非主义”是要超越历史的。它仅仅面对自身,既不反映社会现实的表层意义,也不表现主体的理念意识,它存在着的自身就是意义,而且意义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在《非非主义诗歌方法》中,他们列表比较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非非主义的不同。他们认为,现实主义是单一主题和表层现实意义的确定性反映,现代主义则是多主题和深层象征意义的确定性表现,而非非主义却是主题和意义的不确定描述(8),甚至说它根本就是无主题、无意义的,它只是描述自身而已。
“非非主义”者认为,“情志”是表现论的基础,因而,“超表现”最终表现为“超情态”,因为,它从根本上既超越了表现的内容,又超越了表现的动力,使诗人由对内心情态的关注转而回到诗歌本身及事物本身。周伦佑曾在一次对话中对超情态的诗人和“超情态境界”有一段清晰的描述:“他可以弃个人的亲仇恩怨于不顾,凝神艺术的纯粹。于大悲大喜中超然度外,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化入一片忘形的透明。这便是超情态境界”。这时,“一切艺术的冲动熄灭了,你感觉到创造原来是你的本能。写作过程也不再是‘表现’什么,你直接面对艺术——并坚信它,只有它,才是你唯一的现实”(9)。
然而,艺术的世界总离不开自然和人,情态创作的基本方法,便是赋予自然宇宙以一种人的内容,由此沟通人与自然的永恒联系。超情态创作却要废除人与物的某种契约,剥除附着在自然之上的人的因素,使自然、同时也使人回返到本来的样子。这似乎与法国新小说达成了某种沟通,新小说的主将阿兰·罗伯一格里耶在对“人化了的比喻”分析之后说:“使用这种术语的作家都或多或少有意地在宇宙和居住其中的人类之间建立起一种不变的关系。这样,人的感情就好象是一个个地从人与世界的接触中产生出来,并且,即使不是在这世界里得到自我完成的话,也是在这里面找到了它们自然的对应”(10)。新小说的实验就是要把自然和人还原为各自存在的那个样子,“事物就是事物,人只不过是人”(11),事实上,事物在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且还将永远地存在下去,它不以人的存在作为全部存在的理由,它存在着,无所谓有意义,也无所谓无意义,只是存在着而已。从新小说这种自然的境界里,我们仿佛看到了“非非主义”那还原后的前文化风景,这里既失去了文化和语义,也失去了情感,一切都是自身创化的自在之物。
(二)“非非主义”的诗歌实验
“非非主义”的前文化诗学为诗的实验提供了某种诱惑和目标,或许通向它的路途是遥远而又曲折的,为此,他们的实验也便在多元的、多向度的侧面展开。目前,有两种实验似乎显示出了比较明晰的轮廓,即“超语义”和“超表现”。这使悬置在前文化还原过程中的途径,也有了可供追寻的足迹。
“超语义”或者语晕试验,它是消解语义的一种写作过程和方法,按照我们的理解,它主要通过凸现诗歌语言的语音和语象,从而消解语义的正常流动,使之呈现出不定性、多义性或者弥漫性的直觉状态,直至最终完全地消失语义,使你只感觉到一种声音的流动或一个物象的闪现。一种自觉的语言本体意识,这是“第三代”诗的显著特征之一,可“非非”们对于声音的强调却是独特的,在他们那里,诗歌似乎已脱离了语言文字而成为一种声音。他们认为,宇宙中回荡着的无一不是声音,春天是烂漫的声音,夏天是热烈的声音,秋天是萧索的声音,而冬天则是冷凝的声音……鸟有声音,树有声音,一块无生命的石头也有声音,不仅如此,在生命没有产生之前,声音就在那里存在着了,声音先于生命,而生命则先于文字,甚至声音先于世间万物,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前文化世界,所以尚仲敏说:“《非非》诗歌要做的是回到声音”(12)。杨黎有一首《高处》,开首写道:“A/或是B/总之很轻/很微弱/也很短/但很重要/A,或是B/从耳边/传向远处/传向森林/再从森林/传向上面的天空……”阅读着这首诗,似乎只感觉着一种声音飘浮在耳边,然后飘向远方,掠过大片的森林,回旋在遥迢的高空。这时,你不可能再去猜想它的意图,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意义甚至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声音,显得那么纯粹、空灵,而又有点飘忽不定:是A呢还是B呢?不过,这肯定只是一种声音,你只要把每一颗细胞都伸张开一只只耳朵,凝神谛听那自然的天籁,你的生命也一定会变为一种声音在高处飘动。这或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诗人不仅只呈现一种语音,而且又把这语音揉合在另一种声音里让人们倾听,并由此创化了一个无语义的世界。杨黎是善于倾听和描述声音的,在其它的诗中,你不仅会听到那雨声浑然笼罩的整个世界(《声音》);而且也会看到被诸般声音纠缠的诗人自身:“雨打着我的烂雨披/风吹着我的烂雨披/我的烂雨披哗哗地响着/使我置身其中的耳朵/逃不出去”(《大雨》)。当然,这里例举的只是些描述声音的语感,就是那些单纯的语音,或舒缓或急促,也足以使你陶醉在一种声音之中。比如《高处》吧,它是以听觉效果取悦于你的,你如一遍遍诵读它,它的语音美感一定会浸润你的生命的全身。
“非非”们对于声音的倾听和呈现,决非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音乐感,因为那是单纯针对某种音律和节奏的效果而言的。而“非非”们却把声音看作宇宙的本源或纯粹的前文化境界。所谓“超语义”的存在形式,就是这种“被再听”的声音。因而,诗的语音也就自然而然地变为一种自然的天籁,它的本质就是“超语义”。除了这种对语音的倾听之外,对语象的操作也是一种“超语义”的方式。在他们的诗中,我们会看到一种以语言拼凑组合的图象诗,它的好处是让人超越语言的阻隔,直观到事物的本来形象,而最终忘掉语言和语义。不过,这种形式古今中外均已有之,因而在创造性的层面上考察,就显得格外微弱。
“超表现”或者“超情态”实验,从根本上就是把人与物还原到各自的存在状态,既不使物役于人,也不使人役于物,它们只是平等地自在地存在着,诗的方式和目的也只是客观地描述它们。阿兰·罗伯——格里耶曾经说过:“但在我这里,人的眼睛坚定不移地落在物件上,他看见它们,但不肯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不肯同它们达成任何默契或暧昧的关系,他不肯向它们要求什么,也不同它们形成什么一致与不一致”(13)。杨黎有一组《冷风景》,作为呈奉给大师的献诗,所坚持的就是这种待人观物的态度:“这会儿是冬天/正在飘雪//这条街很长/街两边整整齐齐地栽着/法国梧桐/(夏天的时候/梧桐叶将整条街/全部遮了)//这会儿是冬天/梧桐树叶/早就掉了//街口是一块较大的空地/除了两个垃圾箱外/什么也没有/雪已经下了好久/街两边的房顶上/结下了薄薄一层/街两边全是平顶矮房/这些房子的门和窗子/在这个时候全都紧紧关着”。这是《小镇》开首的几节,一切风景都客观地呈现在面前:一个正在飘雪的冬天,一条长街及两边光秃的梧桐,街口较大的空地及垃圾箱,积下薄薄一层雪的平顶矮房及关着的房门、窗子……风景冷冰冰的,诗人看着它,然它并不回望诗人一眼,既失去了物我交流,也失去了关于物体的深度神话。它只是被平淡地表面地呈现出来的一种样子、姿态和距离等,好象早就存在于那里了,早于这首诗之前和诗人的生命之前。它自身就是一种结构,一个宇宙,诗人之所以呈现它,就因为他与它就这么对等地共存于这个世界上,或许它就是他眼前日常的事物和情景,也或许在一个偶然的下雪的傍晚,他发现了这条街和街上许多陌生的风景,然后把它描述到了纸上,就是如此。这里既失去了文化语义,甚至也失去了情态感受,没有喜悦,没有忧郁,没有爱,也没有憎,诗人和事物都表现出超情态的冷漠。诗人另有一首《旅途之一》,或许更能显示诗人超情态的创作心理。恐怕没有比死的惨象更能让人颤栗和痛苦的了,然而诗人面对一位惨遭车祸的小女孩,却能那般不动声色地描述,实在是一个平凡人所难能有的体验。
自然,如前所述及,“非非”们的实验是多元的、多向度的,可说每一种实验都为“前文化还原”开辟了一种可能。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此无法一一展开。这里所要说明的、也是无可讳言的是,“非非”们的实验仍然面临着至今难以摆脱的悖论和困境。当诗人们以反叛的姿态背叛语言的时候,他仍要呈现另一种语言状态;当他反叛语义、超越语义的时候,他的语言又无法摆脱另一种语义;当他决意反理性的时候,他的诗歌却又极具理性。这或许是诗人们永远困惑和迷惘的。因而,迄今为止,“前文化还原”也只能是一种美妙的幻觉而已,诗人们虽然能够接近它,但却难以进入它。也象我们前所述及的,“非非”的理论建构显得过于辉煌,而创作又显得那么疲弱、无力,这就构成了极大反差,使人们对其终极目标不免产生怀疑。另外,它所具有的极大的包容性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任何前锋的实验都可纳入“非非”们的领地,这必然使其创作实验呈现出散射芜杂状态,而缺乏整一性,最终也削弱了作为群体的意义。
1988、11
(1)《非非主义宣言》(1986.5),见《非非》第1期。
(2)参阅《非非主义宣言》和蓝马《前文化导言》,见《非非》第1期。
(3)关于三度还原的理论,参阅《非非主义诗歌方法》,见《非非》第1期。
(4)见蓝马《前文化导言》,《非非》第1期。
(5)参见蓝马:《前文化导言》,《非非》第1期。
(6)参见《非非主义宣言》,《非非》第1期。
(7)蓝马《语言革命——超文化》,见《百家》1988年第2期。
(8)周伦佑、蓝马:《非非主义诗歌方法》,见《非非》第1期。
(9)参阅打印稿《第三代诗:对混乱的澄清一尚仲敏、杨黎、蓝马、周伦佑成都对话录》。
(10)、(11)、(13)阿兰·罗伯一格里耶:《自然、人道主义、悲剧》,见柳鸣九编选《新小说研究》,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参阅尚仲敏:《今日诗坛:对形势的判断》,见《诗歌报》1988年9月6日1版。
【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