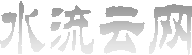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
张中行《诗词读写丛话》
第01页
02页 03页 04页
05页 06页 07页
08页 09页 10页
11页 12页 13页
14页 15页 16页
17页 18页 19页
20页
第21页 22页
23页 24页 25页
26页 27页 28页
29页 30页 31页
32页 33页 34页
35页 36页 37页
38页 39页 40页
四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这题目是由王国维《人间词话》那里截来的,全文是:“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意思很明显,总的是诗词有别。借用六朝时期形神对举的旧例,可以说,王氏所谓别是神方面的,不是形方面的。形方面的好说,如词常用长短句,有调,声韵变化多,宽严因地而异,词语可以偏于俚俗等,都有案可查;诗就不然。神方面呢?不思或一思,像是问题也不复杂。如:(1)“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2)“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3)“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4)“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没读过而对诗词稍有所知的人都会认出,(1)(3)是诗,(2)(4)是词,意境有明显的分别。王氏上面一段话想来就是从这样的明显分别说的,所以拈出词,就说它要眇宜修(《楚辞·九歌》中语,意为美得很),言长(宛转细致,因而意境就娇柔委曲)。可是再思三思,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且说诗词之作都是众木成林,从中取出少数相比,也许分别并不这样明显;何况还有明目张胆越界的,那是大家熟知的苏、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形是词,意境却不娇柔委曲,又因为苏是大名人,才高,揭竿而起就占地为王,竟至开创了豪放派。百花齐放,多个派像是也没什么关系,然而又不尽然。影响之大者显然是,诗词的(意境)界限就模糊了。这好不好?只好把上面的意思重复一遍,问题太复杂了。
首先是事实上有没有这样的界限。苏兵力太强,只好避其锋,就他以前说,曰有。最有力的证据是实物。如: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温庭筠《苏武庙》)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憀独(读仄声)倚门。(温庭筠《菩萨蛮》)
清瑟怨遥夜,绕弦风雨哀。孤灯闻楚角,残月下章台。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来。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韦庄《章台夜思》)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读仄声)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持也)旧书看(读平声)。几时携手入长安?(韦庄《浣溪沙》)
温、韦都是兼作诗词的大家,人同一,心同一,可是拿起笔,写出来,意境就有了明显的分别。什么分别?可以用个取巧的办法说,以京剧为喻,诗是出于生角之口的,所以境阔,官场、沙场都可以;词是出于旦角(还要限于正旦、闺门旦和花旦)之口的,所以言长,总是在闺房内外说愁抹粉。
这分别还可以找到深一层的根据。只谈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的。关系重大的有两种情况。一种,诗,由三百篇起,基本上是供生角用的,所以常常搬上庙堂;词就不然,而是基本上供旦角用的,所以起初,唱的场所限于花间、尊前。另一种是同源而异流,具体说是,开始都与音乐有不解之缘,往下发展,诗不久就变了心,离开音乐去单干,词却甘心守节,从一而终。话过于简单,就补充几句。《诗经》的诗都是入乐的,汉以来,正牌乐府也是入乐的。可是汉五言诗,苏、李赠答的虽然靠不住,但至少到东汉,《古诗十九首》已经不入乐。其后这股风大盛,建安作手,南北朝,唐宋,直到皇清前后,文人作诗都是在作文章的另一体,根本没有想到入乐的事。诗人士大夫之手,没有入乐的拘束,自由发展,士大夫(生角扮的)气就会越来越重。词就不然,唐、五代,如敦煌曲子词,都是出于歌女之口的。以后文人仿作,依调填写,心目中也是在写供歌女用的歌辞。北宋,柳词能唱,周邦彦精于音律,朝云唱苏词“枝上柳绵吹又少”,到南宋,《白石道人歌曲》旁缀工尺谱,都有文献可征。其后词渐渐不能歌了,可是直到皇清前后,文人作词还要照谱填,这是要求甚至自信为还可以入乐。有这种信心,词就没有诗那样的自由,其结果是,虽然拿笔的是士大夫,口吻和情意却要装作从旦角那里来,于是就不能不娇柔委曲了。根据的另一方面是人情的。人之情,过于复杂,只说与这里关系密切的,是有距离远的两种。这两种的差异,可以来于人,如焦大与林黛玉。也可以来于不同的情怀,如李商隐“永忆江湖归白(读bò)发,欲回天地入扁(读piān)舟”是一种,柳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读仄声)人憔悴”是另一种。前一种宜于生角唱,依传统,是用诗表达。“宜于”就不能变吗?这夸张一些说,等于问,狗就不能捉老鼠吗?我的想法,猫捉,总会有生理、心理等方面的来由;或干脆退一步着想,既然千百年来猫干得很好,那就还是让猫捉,既省事又无损失,不是很好吗?
这各有特点,宜于分工的想法,是早已有之的。只引一时想到的三处。一处见《历代诗余》引俞文豹《吹剑录》:
(苏)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一处见《苕溪渔隐丛话》引陈师道《后山诗话》:
(韩)退之以文为诗,(苏)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一处见李清照《词论》:
……至晏丞相(晏殊)、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
可见直到北宋、南宋之际,至少是绝大多数人,还坚守传统,认为诗词是有大分别的。这分别既表现在音律方面,又表现在意境方面。
值得重视的是意境方面的分别,因为音律是手段,意境是目的。还是就苏以前说,也为了与豪放对举,大家公认词的风格是“婉约”。什么是婉约?不好讲。勉强说,是感情纤细,借用弗罗伊德学派的诛心法,可以说是大多来于男女之间,所以常常带有闺房粉黛气。少数诗也有这种气,但放出成为格调,韵味还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别。--无妨总的说说差别,用对比法:一是给人的感触印象有别,诗刚,词柔;二是表达的手法有别,诗直,词曲;三是情意的表露程度有别,诗显,词隐;四是来由和归属有别,诗男,词女。一句话,诗是诗,词是词,专就意境说,疆界也是分明的,也应该分明。
不幸是出了造反派,上面的金城汤池不能不受到冲击。一般治文学史的人都说,这造反派的头头是苏东坡,冲锋陷阵之作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等。其实情况并不这样简单。纠缠是来自士大夫仿作,学语,有时就不免露了马脚,或者说,干脆就随自己之便。这可以早到五代。最突出的是南唐后主李煜,如: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不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读仄声)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语句、情怀都这样慷慨悲凉,显然不能出于歌女之口,也就闯出花间、尊前的范围。如果词作只能分作婉约、豪放两类,像这样的当然就得归入豪放一类。王国维有见于此,所以在《人间词话》里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士大夫有士大夫的情意,有士大夫的手法,一旦强拉词体来为自己服务,词就几乎是欲不变而不可得了。这样说,词的婉约传统,旁边忽然杀出个豪放李逵来,也是自然之事。
问题是怎样看待这关西大汉闯入娇羞佳人队伍的现象。看法有保守和革新两派。旧时代,保守派占上风;近年来,革新派的气焰有高涨之势。保守派的理由,上面引过的三处可以为代表,轻的是作作无妨,但终“非本色”;重的是,那是(句读不葺之)诗,是用作诗之法作词,不能成为词。革新派的理由是,由“鬓云欲度香腮雪”发展为“大江东去”,是解放,是扩大词的表现范围。由长在闺房刺绣变为上山下乡,或同一场地,既容纳闺房刺绣的佳人,又容纳上山下乡的干部,有什么不好?各是其所是来于各有所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文学史家也许更难断文论的争执。力最大的是事实,不管保守派怎样恋旧,甚至因之而大声疾呼,反正“大江东去”一流作品早已在刻本上流传,近年来并在铅印本上大量流传。有人也许会想,惟其都流传,就更应该评定是非高下,装作视而不见是不对的。但这很难。保守派旧家底厚,几乎用不着什么力量来支援。革新派呢,赞扬豪放的作品,你想反对,恐怕除了不爱吃酸的因而不买醋之外,也很难找到致其死命的理由。你说不该这样写,豪放派可以反问,谁规定的?而且,豪放派还有个道德方面的据点,是并没有反对婉约派去写“鬓云欲度香腮雪”(他们自己也不少写)。所以为今之计,只好用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的办法,承认词有表现娇柔委曲的本领,但也无妨豪放一下。站在爱好词的立场,似乎还可以顺水推舟,说怎么怎么锻炼之后,本事大了,就像梅兰芳,虽然经常扮演虞姬,却也可以反串楚霸王。
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本职行当与反串终归不是一回事。直说是,词,就意境说,确是有正有变: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正,关西大汉持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是变。这样认识,理由不是谁曾规定,而是情势使然。以下说说情势,可以分为质和量两个方面。先说质,还可以分为正面说和反面说。正面说是,诗的意境千差万别,其中一大类,上面称为娇柔委曲的,重要性也许不低于慨当以慷吧。这就需要表现,即用语言抓住,成为诗境,以供无数的痴男怨女神游。而事实证明,词的表达形式最适于担当这个责任,或者说,完成这样的任务,常常比我们希望的还要好。论功行赏,词在这方面当然应该受上赏。反面说,所受之赏也许应该上上,那是本篇开头所引王国维的话,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何以这样说?看下面的例:
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读仄声)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牛希济《生查子》)
醉别(读仄声)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读仄声)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晏几道《蝶恋花》)
风鬟雨鬓,偏是来无准。倦倚玉阑看(读平声)月晕,容易语低香近。
软风吹遍窗纱,心期便隔(读仄声)天涯。从此伤春伤别(读仄声),黄昏只对梨花。(纳兰成德《清平乐》)
人各有见,我说我自己的,像这三首所表现的意境(兼韵味),五七言律绝就难于为力,因为与词相比,显得太敞太硬;古体更不成,因为太朴太厚。如果这样的领会不错,那词就堪称为只此一家,并无分号。无分号,你想用,就只好上此门来买,就是说,如果有此情意想表达,就最好填词,不要作诗;同理,想找这类的意境来神游一下,就要找什么词集来读,暂把什么诗集放在一边。
婉约的词为正,还有量方面的理由。这好说,只用数学的加减法就可以。传世的词作,由唐朝后期起(所传李白的两首有问题),到皇清逊位止,总不少于几万首吧,其中像“大江东去”那样的,究竟是极少数。作者也是这样,南宋以来,忠心耿耿跟着苏、辛走的,人数也并不多。在这种地方,我认为,民主的原则同样适用,即票多者上台,为正,反对派只能坐在下边。再有,帐还可以算得更细,就说苏、辛吧,也不是一贯豪放而不婉约。说辛的风格是豪放,据孤陋寡闻如我所知,不同意的人不少。理由也是来自数学的加减,如有大名的《祝英台令》: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倩谁唤流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持也)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呜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将(带着)愁归去。
谁都得承认这是上好的婉约派作品。还不只此也,即如“更能消几番风雨”(《摸鱼儿》),“绿树听鹈鴂”(《贺新郎》),“千古江山”(《永遇乐》),也有大名的几首,语句和意境也不是纯豪放的。所以与苏的“大江东去”诸篇比,辛终归不是以诗为词;或正面说,辛虽然堂庑大,感慨深,写出的篇什,大体上还是词人之词,不像苏,有不少篇,只能说是诗人之词。说有不少,意思是,就是这位造反派的头头,也不是日日夜夜都造反。看下面这两首:
道字娇讹语未成,未应春阁(读仄声)梦多情。朝来何事绿鬟倾?
綵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困人天气近清明。(《浣溪沙》)
花拥鸳房,记驼肩髻小,约鬓眉长。轻身翻燕舞,低语啭莺簧。相见处,便难忘(读平声)。肯亲度瑶觞,向夜阑、歌翻郢曲,带换韩香。
别来音信难将,似云收楚峡(读仄声),雨散巫阳。相逢情有在,不语意难量。些个事,断人肠,怎禁得(读仄声)凄惶。待与伊移根换叶,试又何妨。(《意难忘》)
像这样的,总不能不说是地道的婉约吧?尤其后一首,颇像出于柳永之手,可见苏作词,只是为性情所限,常常豪放,而不是摒弃婉约。不摒弃,来由的一部分应该说是,婉约是正,豪放是变。
那么,据以上的多方面考虑,诗词之别的问题就不难解决。总的,我们可以接受“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的看法,因为大体上是对的。这接受有引导行的力量,就是写或读,都无妨以婉约的为主。但引导不是限制,如果有苏那样的情怀,愿意顺着“大江东去”的路子走,那就慨当以慷一番,也无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