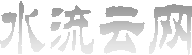二、创作论
(一)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
长吉《高轩过》篇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①,此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夫天理流行,天工造化,无所谓道术学艺也。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书•皋陶谟》曰:“天工,人其代之②。”《法言•问道》篇曰:“或问雕刻众形,非天欤。曰:以其不雕刻也。”③百凡道艺之发生,皆天与人之凑合耳。顾天一而已,纯乎自然,艺由人为,乃生分别。综而论之,得两大宗。一则师法造化,以模写自然为主。其说在西方,创于柏拉图④,发扬于亚理士多德⑤,重申于西塞罗⑥,而大行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其焰至今不衰。莎士比亚所谓持镜照自然者是⑦。昌黎《赠东野》诗“文字觑天巧”一语⑧,可以括之。“觑”字下得最好;盖此派之说,以为造化虽备众美,而不能全善全美,作者必加一番简择取舍之工。即“觑巧”之意也。二则主润饰自然,功夺造化。此说在西方,萌芽于克利索斯当⑨,申明于普罗提诺⑩。近世则培根⑾、牟拉托利⑿、儒贝尔⒀、龚古尔兄弟⒁、波德莱尔⒂、惠司勒⒃皆有悟厥旨。唯美派作者尤信奉之。但丁所谓⒄:“造化若大匠制器,手战不能如意所出,须人代之斲范”。长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可以提要钩玄。此派论者不特以为艺术中造境之美,非天然境界所及;至谓自然界无现成之美,只有资料,经艺术驱遣陶熔,方得佳观。此所以“天无功”而有待于“补”也。窃以为二说若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夫模写自然,而曰“选择”,则有陶甄矫改之意。自出心裁,而曰“修补”,顺其性而扩充之曰“补”,删削之而不伤其性曰“修”,亦何尝能尽离自然哉。师造化之法,亦正如师古人,不外“拟议变化”耳。故亚理士多德自言:师自然须得其当然,写事要能穷理。盖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师天写实,而犁然有当于心;师心造境,而秩然勿倍于理。莎士比亚尝曰:“人艺足补天工,然而人艺即天工也。”圆通妙澈,圣哉言乎。人出于天,故人之补天,即天之假手自补,天之自补,则必人巧能泯。造化之秘,与心匠之运,沆瀣融会,无分彼此。及未达者为之,执著门户家数,悬鹄以射,非应机有合。写实者固牛溲马勃,拉杂可笑,如卢多逊、胡钉铰之伦;造境者亦牛鬼蛇神,奇诞无趣,玉川、昌谷,亦未免也。(60—62页)
①李贺《高轩过》,写韩愈、皇甫湜坐牢来看他,他写诗称两人的文笔能补救大自然的不足。
②“天工,人其代之。”大自然的作为,人代它。即大自然的作为有不足的,人代它补足。
③汉朝杨雄《法言•问道》:“有人问雕刻各种万物的形象,不是天吗?”答:“因为天不雕刻。如果天雕刻万物的形象,那有这么多的力量。”这里含有大自然造物是自然形成的。
④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主张模写自然。
⑤亚理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学生,也主张模写自然。
⑥西塞罗:古罗马哲学家,也主张模写自然。
⑦莎士比亚:十六、七世纪英国大戏剧作家。
⑧韩愈称孟郊的诗能观察到大自然的巧妙处。
⑨克利索斯当:古希腊演说家。
⑩普罗提诺:三世纪埃及哲学家。
⑾培根:十三世纪英国科学家。
⑿牟拉托利:十七、八世纪意大利考古学家。
⒀儒贝尔:十八、九世纪法国伦理学家。
⒁龚古尔兄弟: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家爱德蒙•德•龚古尔、于勒•德•龚古尔兄弟二人。
⒂波德莱尔:十九世纪法国浪漫派诗人。
⒃惠司勒:十九世纪美国画家。
⒄但丁:十三、四世纪意大利诗人。
这里指出艺术有两派:一派主张模写自然,一派主张润饰自然。主张模写自然的,认为大自然具备众美,但不能全善全美,所以要加一番选择。像韩愈称孟郊的诗:“文字觑天巧。”能观察到大自然的巧妙处,写入诗里。说明大自然不都是美的,要加以选择,选美的来写。主张润饰自然的,认为大自然不够美,要靠人力来补充,人工胜过大自然。钱先生认为这两说实是相反相成。模写自然的,对大自然要进行选择,那也有对大自然进行矫改的用意。润饰自然的,还要根据大自然的本性来改造,不能违反大自然的本性。艺术创作得恰到好处,要避免斧斫的痕迹,要求合于自然。所以模写自然的,不是完全照自然的样子来写,要加以选择矫改。润饰自然的也不能离开自然,两者有相通处。钱先生认为道术学艺,是“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即就艺术说,作家创作艺术,还是要师法自然,这是“法天。”在师法自然时,对大自然有选择矫改,这是“胜天”;不论选择和润色,都不能违反自然,这是“通天”。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这里讲的写境,近乎模仿自然;所讲的造境,近乎润饰自然。两派都不能违反自然,即钱先生说的“法天”“胜天”“通天”了。不仅这样,有时候,一篇作品中就有写实与理想两种境界的结合。如苏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坡仙集外纪》说:“神宗读至‘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乃叹曰:‘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这说明上片写“天上宫阙”,“我欲乘风归去”,是写理想。这个理想,宋神宗读了,认为是想离开朝廷去隐居,词写怕“高处不胜寒”,即不想去隐居,所以说“苏轼终是爱君”,那末这个理想里还含有写实的意味。下片写月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是写实。但“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在“不应有恨”里,以月比人也有恨,又含有理想了。这是说写实与理想有相通处,这是一方面。但上片理想,下片写实,还是不同,虽有不同,又都是合乎自然。
(二)“选春梦”的创作论
长吉尚有一语,颇与“笔补造化”相映发。《春怀引》云:“宝枕垂云选春梦”;情景即《美人梳头歌》之“西施晓梦绡帐寒,香鬟堕髻半沉檀”,而“选”字奇创。曾益注①:“先期为好梦”,近似而未透切。夫梦虽人作,却不由人作主。太白《白头吟》曰:“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言“或”则非招之即来者也。唐僧尚颜《夷陵即事》曰:“思家乞梦多”,言“乞”则求不必得者也。放翁《蝶恋花》亦曰:“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参观《管锥编》1041—1042页)。作梦而许操“选”政,若选将、选色或点戏、点菜然,则人自专由,梦可随心而成,如愿以作。醒时生涯之所缺欠,得使梦完“补”具足焉,正犹“造化”之能以“笔补”,踌躇满志矣。周栎园《赖古堂集》卷二十《与帅君》②:“机上肉耳。而恶梦昔昔〔即夕夕〕嬲之,闭目之恐,甚于开目。古人欲买梦,近日卢德水欲选好梦”,堪为长吉句作笺。纳兰容若妇沈宛有长短句集③,名《选梦词》;吾乡刘芙初《尚絗堂诗集》卷二《寻春》④:“寻春上东阁,选梦下西湖”,又卷五《白门惆怅词》:“寻芳院落蘼芜地,选梦池塘菡萏天”;必自长吉句来。方扶南批注长吉集⑤,力诋此诗“庸下”、“浅俗”、“滑率”,断为伪作。方氏以为长吉真手笔者,亦每可当“庸下”、“浅俗”、“滑率”之评,故真伪殊未易言。方氏所诃此篇中“庸”、“浅”、“滑”处,窃愧钝暗,熟视无睹,然渠侬于“选梦”义谛,正自愦愦耳。《管锥编》122—123页论《荣华乐》、782页论《南山田中行》、《管锥编增订》56页论《艾如张》,兹不复赘。《艾如张》首句“齐人织网如素空”,可参观《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二年四月:“诏齐相省方空縠”,章怀注:“纱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纱也。”所谓“如素空”矣。(382—383页)
①曾益:明代作家,注有《昌谷集》四卷。
②周栎园,清周亮工字,著《赖古堂文集》二十四卷。
③纳兰容若:纳兰性德字。
④刘芙初:刘嗣绾字,著《尚絗堂诗集》五十二卷,词集二卷。
⑤方扶南:方世举字,清作家。
这一则讲创作规律,用李贺《春怀引》中的“选春梦”来加以发挥,称为“选”字奇创。钱先生用李白的“或有梦来时”的“或梦”,尚颜的“乞梦”,陆游的“只有梦魂能再遇”的“遇梦”,都不如“选梦”的“选”字奇创,可以作为创作规律。“选梦”是“梦可随心而成,如愿以作”。“醒时生涯之所欠缺,使得梦完‘补’具足焉。”就创作说,是反映生活的。生活中有不少欠缺的东西,从反映生活说,这些在生活中欠缺的东西,在作品中就成为缺憾。有了“选梦”,把醒时缺少的东西,可以在梦中如愿以偿,借选梦来得到补偿。好比生活中欠缺的东西,可以在作品中得到补偿,这是“笔补造化天无功”的又一种补偿了。周亮工讲的“选好梦”,就说明了“选梦”的用意了。
作家怎样在作品中“选春梦”?钱先生在《管锥编》122—123页里引了李贺的《荣华乐》作例,这篇是写后汉的权臣梁冀的。照《后汉书•梁冀传》里说:梁冀“鸢肩豺目”,生得不美,他得到君王的宠信专权,并不由于他的“色媚”。但李贺把他写得美,作“台下戏学邯郸倡,口吟舌话称女郎,锦祛绣面汉帝旁。”好像汉顺帝的宠爱梁冀,是由于梁冀的漂亮,正好像梁翼的宠爱秦宫,是由于秦宫的漂亮。“倘亦深有感于嬖幸之窃权最易,擅权最专,故不惜凭空杜撰,以寓论世之识乎?”这就是作者改变生活中的真实,用“选春梦”的创作方法吧。又《管锥编》782页引李贺《南山田中行》:“鬼灯如漆点松花。”又《感讽》第三:“漆炬迎新人,幽旷营扰扰。”
“王琦注谓鬼灯低暗不明,是也。”钱先生在这里说“鬼灯如漆”和“漆炬”,指出李贺认为鬼灯的低暗不明,也是出于想象,是选梦。又《管锥编补订》56页论李贺《艾如张》:“齐人织网如素空,张在野田平碧中。网丝漠漠无形影,误尔触之伤首红。”这是说齐人用素丝织网,看不见网。鸟触在网里就被捕了。这也是想象,也是属于选梦。“选春梦”的诗,还可举陆游的诗作例。陆游《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这是“选春梦”,长期想象恢复失地,因有好梦,诗写梦中所见,是“选春梦”,也是写好梦了。诗称:“熊罴百万从銮贺,故地不劳传檄下;筑城绝塞进新图,排仗行宫宣大赦。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驾前六军错锦绣,秋风鼓角声满天。苜蓿峰前尽亭障,平安火在交河上;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这是写春梦,这个梦是作者生活中所不能达到的想望。向往过于逼切,就真的化而为梦,是个好梦,成为“选春梦”的杰作了。这首诗是在宋孝宗淳熙七年做的。梦里从宋孝宗的大驾亲征,收复了汉唐故地,收复了凉州,建立了边防亭障。凉州女儿梳头已学京都样。这真是一个好梦了。
(三)谈灵感
《朱子语类》卷十八论“致知节目”云①:“逐节思索,自然有觉。如谚所谓:冷灰里豆爆。”尼采自道其“烟士披里纯”之体验云②:“心所思索,忽如电光霍闪,登时照彻,无复遁形,不可游移。”(601页)
①《朱子语类》:宋黎靖德编朱熹语录一百四十卷。
②尼采: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烟士披里纯:灵感。
这一则讲创作的灵感。《谈艺录》286页称:“出世宗教之悟比于暗室忽明,世间学问之悟亦似云开电射,心境又无乎不同。”这里说的“悟”,即指“灵感”。朱熹讲“觉”,即“悟”,从“致知格物”来,逐节思索,久之自悟,如“冷灰里豆爆”,指积久功深,自然有悟入,这即是“世间学问之悟”,“亦似云开电射”,“电射”的光正像“灵感”了。钱先生在《管锥编》讲陆机《文赋》里的“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钱先生说:“按自此至‘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一大节皆言文机利滞非作者所能自主,已近后世‘神来’、‘烟士披里纯’之说。创作者在丰富实践的基础上进行酝酿思考的紧张阶段,由于有关事物的启发,促使创造活动中所探索的重要环节得到明确的解决,一般称为获得灵感。严肃勤奋的劳动态度和负责精神,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积累,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技巧的掌握,是获得灵感的前提。
(四)谈“活法”
《艇斋诗话》记吕东莱论诗尝引孙子论兵语①:“始如处女,终如脱兔。”陈起《前贤小集拾遗》②卷四载曾茶山《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五古,今本《茶山集》漏收③,有云:“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政用口诀故。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如脱免。”“脱兔”正与“金弹”同归,而“活法”复与“圆”一致。圆言其体,譬如金弹;活言其用,譬如脱兔。茶山二句即东坡《次韵欧阳叔弼》所谓:“中有清圆句,铜丸飞柘弹。”观《谢幼槃文集》卷一《读吕居仁诗》:“吾宗宣城守,诗压额谢辈④。居仁相家子,哦诗亦能事。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则东莱虽有取于谢玄晖语,而尚以为玄晖所行不逮所言也。章冠之《自鸣集》卷四《送谢王梦得借示诗卷》:“人入江西社,诗参活句禅”;“参活句”即茶山句之“勿参死句”,盖以此为“江西社”中人传授心法。东莱借禅人“死语不离窠臼”话头(参观《五灯会元》卷十二昙颖达观章次),拍合谢玄晖“弹丸”名言,遂使派家有口诀、口号矣。其释“活法”云:“规矩备具,而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不背于规矩”;乍视之若有语病,既“出规矩外”,安能“不背规矩”。细按之则两语非互释重言,乃更端相辅。前语谓越规矩而有冲天破壁之奇,后句谓守规矩而无束手缚脚之窘:要之非抹杀规矩而能神明乎规矩,能适合规矩而非拘挛乎规矩。东坡《书吴道子画后》曰⑤:“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其后语略同东莱前语,其前语略当东莱后语。陆士衡《文赋》⑥:“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正东莱前语之旨也(参观《管锥编》1193—1194页)。东莱后语犹《论语•为政》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恩格斯诠黑格尔所谓“自由即规律之认识”⑦。谈艺者尝喻为“明珠走盘而不出于盘”、或“骏马行蚁封而不磋跌”、甚至“足镣手铐而能舞蹈”(参观《宋诗选注》苏轼篇注3、4,又杨万里篇注24、25,《管锥编》149页、1197页、又《增订》17页)。康德言想象力有“自由纪律性”⑧,黑格尔言精神“于必然性中自由”,是其大义。以此谛说诗,则如歌德言⑨:“欲伟大,当收敛。受限制,大家始显身手;有规律,吾侪方得自由。”希勒格尔尝言韵律含“守秩序之自由”⑩。黑贝尔语尤妙⑾,谓“诗家之于束缚或限制,不与之抵拄,而能与之游戏,庶造高境”。近人艾略特云⑿:“诗家有不必守规矩处,正所以维持秩序也。”均相发明。《晋书•陶侃传》记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语亦不啻为谈艺设也。(438—440页)
①《艇斋诗话》:宋曾季貍撰,一卷。吕东莱:吕本中,字居仁,学者称东莱先生,宋诗人。孙子:孙武,春秋时兵家,著有《孙子》十三篇。
②陈起:字宗之,南宋书坊主,刻《江湖小集》等书多种。
③曾茶山:曾几,号茶山居士。有《茶山集》八卷。《谢幼槃文集》十卷,宋谢逸撰。
④宣城守:谢朓,字玄晖,官宣城太守。颜谢:颜延之,谢灵运,与谢朓南北朝时宋诗人。
⑤东坡:苏轼号东坡居士。吴道子:吴道玄字,唐画家。
⑥陆士衡:晋陆机字,文学家。
⑦思格斯:十九世纪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理论家。黑格尔:十八、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⑧康德:十八世纪末期、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⑨歌德:十九世纪初德国诗人。
⑩希勒格尔:十八、九世纪德国文学艺术家。
⑾黑贝尔:十九世纪德国诗人。本书又译为“赫贝尔”。
⑿艾略特:英国诗人、批评家。
这一节讲创作要讲究“活法”。《孙子•九地》:“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处女比安静,脱兔比行动迅速。一静一动,变化不定,即指灵活。曾几讲“学诗如参禅”,指诗人在生活中有所感触,就抓住这种感触来作诗。像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钱先生《宋诗选注》评:“这首诗里的‘留’字‘分’字都精致而不费力”;第四句参看白居易的《前日〈别柳枝〉绝句,梦得继和,又复戏答》:“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这里“留酸软齿牙”,“留”和“软”写出生活中的一种感触。“分绿”又是一种感触。“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里又有一种感触,感触到看儿童捉柳花的活泼可爱。抓住生活中的这种感触,写成诗句,这就好像参禅了。参禅分死活,像杨万里抓住生活中的感触来写,就是活句。再像白居易的“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感叹自己已经失去童年无法追寻了。这又是一种感触,抓住这种感触写出来,也是参活句。倘作者没有自己的感触,抄袭别人的话,就不是参活句了。“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有了自己的感触,不论怎样说都可以。像白居易那样说可以,像杨万里那样说也可以。“乃在欢喜处”,应该是在有感触处。
再说像学仙那样,“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成仙了。这正如杨万里《荆溪集序》:“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这就是“辛苦终不遇”。后来觉悟了,“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
“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去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这就是“忽然毛骨换”了。懂得了诗从生活中来,在生活中有了感触,把它抓住就写成了。方东树《昭昧詹言》:“玄晖别具一副笔墨,开齐梁而冠乎齐梁”,所以说谢朓“诗压颜(延之)、谢(灵运)。”又称:“玄晖自云:‘圆美流转如弹丸。’”这就是“譬如金弹”。这里指出活法说胜过弹丸。因为弹丸说讲诗的圆美流转,就诗的艺术成就说。活法讲诗的感触,有了感触才能写诗,才有诗的艺术成就,所以活法更重要了。没有对外界事物的感触,说人家已说的话,没有新的意境,没有新的艺术手法,这叫落入前人的窠臼,所以说“死语不离窠臼”。
讲活法,提到苏轼《书吴道子画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钱先生在《宋诗选注》苏轼篇里说: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应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这里就谈到“规矩备具,而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不背于规矩”了。
钱先生引陆机《文赋》:“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在《管锥编》1193页里作了发挥:“离方圆以穷形相”即不囿陈规,力破余地,……西方古典主义以还,论文常语如:“才气雄豪,不局趣于律度,迈越规矩,无法有法”;“规矩拘缚,不得尽才逞意,乃纵心放笔,及其至也,纵放即成规矩”;“破坏规矩乃精益求精之一术”,均相发明。
(五)谈妙语
沧浪别开生面,如骊珠之先探①,等犀角之独觉②,在学诗时工夫之外,另拈出成诗后之境界,妙悟而外,尚有神韵。不仅以学诗之事,比诸学禅之事,并以诗成有神,言尽而味无穷之妙,比于禅理之超绝语言文字。他人不过较诗于禅,沧浪遂欲通禅于诗。胡元瑞《诗薮•杂编》卷五比为“达摩西来”者③,端在乎此,斯意似非李氏(李光昭,见256页)所解也。(258页)
①骊珠:《庄子•列禦寇》说深渊中有骊(黑)龙颔下有珠,要在它睡着时才能探骊得珠。
②犀角:旧说以犀牛角有白纹,感应灵敏。李商隐《无题》:“心有灵犀一点通。”
③胡元瑞:明胡应麟字,有《诗薮》二十卷。达摩:天竺人。梁普通元年入华,在嵩山面壁九年而化。为禅宗传入中国的初祖。
这一则讲诗歌创作的妙悟和神韵。严羽《沧浪诗话》在《诗辨》里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浩然)学力下韩退之(愈)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沧浪所论毕竟重在透彻之悟,偏于神韵一边,所以在‘诗道亦在妙悟’之后,即言‘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可知沧浪所谓妙悟,正指下节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从这点讲,则王士祯神韵之说为最合沧浪意旨。王氏谓:‘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维)裴(迪)《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殻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悟上乘。”这里讲的“妙悟”,粗浅地说,诗人看景物时,产生出一种情思,没有这种情思,写不出诗,所以“诗道惟在妙悟。”有了情思,再结合具体景物来描绘,景中含情,这就是神韵。如王维在雨中的山果落,灯下的草虫鸣里体会到一种极为幽静的境界,这种体会就是妙悟。有了这种体会,写出“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在这两句诗里透露出一种幽静的境界,这就是景中含情的神韵了。因此以禅喻诗就妙悟方面说,诗有了妙悟以后,还要结合景物来透露情思,还要神韵;禅只要了悟以后就可以了,不必要有神韵。所以钱先生说:“在学诗时工夫之外,另拈出诗成后的境界,妙悟而外,尚有神韵”,即“言有尽而味无穷之妙”。以上举出王维诗的两句是言有尽,在这两句中含有一种极幽静的境界可供体味,即意无穷。没有这种幽静的境界,人们在热闹中,就感不到山果落,听不到草虫鸣了。钱先生又指出李光昭《诗禅吟示同学》诗:“沧浪且未知禅理”,反对以禅喻诗。其实以禅喻诗指妙悟,这点非李氏所解。胡应麟认为达摩创禅宗,即讲妙悟,妙悟可通于诗,所以说是“达摩西来”意。
(六)抓“诗思”
《剑南诗稿》卷二十二《杂题》①:“山光染黛朝如湿,川气熔银暮不收。诗料满前谁领略,时时来倚水边楼”;卷二十五《晨起坐南堂书触目》:“奇峰角立千螺晓,远水平铺匹练收,诗料满前吾老矣,笔端无力固宜休’;《晚眺》:“个中诗思来无尽,十手传抄畏不供”;卷三十三《山行》:“眼边处处皆新句,尘务经心苦自迷。今日偶然亲拾得,乱松深处石桥西”;卷四十二《春日》:“今代江南无画手,矮笺移入放翁诗”;卷八十《日暮自湖上归》:“造物陈诗信奇绝,匆匆摹写不能工。”欧阳永叔评文与可诗②:“世间原有此句,与可拾得耳”,见《东坡题跋》卷二《书昙秀诗》③,放翁“偶然亲拾得”语本之。杨诚斋言得句,几如自献不待招、随手即可拈者,视放翁事更便易。《诚斋集》卷十三《晓经潘葑》④:“潘葑未到眼先入,岸柳垂头向人揖,一时唤入诚斋集”;卷十八《船过灵洲》:“江山惨淡真如画,烟雨空濛自一奇。病酒春眠不知晓,开门拾得一篇诗”;卷三十七《晓行东园》:“好诗排闼来寻我,一字何曾拈白须。”方虚谷《桐江续集》卷五《考亭秋怀》第九首⑤:“登高见佳句,意会无非诗。顾视不即收,顷刻已失之”;又卷二十八《诗思》第四首:“满眼诗无数,斯须复失之”;则不脱唐子西、陈简斋窠臼⑥。(455—456页)
①《剑南诗稿》:陆游号放翁,撰《剑南诗稿》八十五卷。
②欧阳永叔:欧阳修字。文与可:文同字。
③《东坡题跋》,苏轼著,六卷。昙秀:宋僧名。
④《诚斋集》:宋杨万里撰《诚斋集》一百三十三卷。
⑤方虚谷:方回字,撰《桐江续集》三十七卷。
⑥唐子西:唐庚字。陈简斋:陈与义字。
这一节讲从生活中有所感受,抓住了写在诗里。这里引的陆游诗,从“山光染黛”,“川气熔银”里,即从“山光”和“川气”里,产生了“染黛”“熔银”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成为“诗料”,“领略”了它,写入诗中,就成了这首诗。再如看到“奇峰”像角立的千螺,看到“远水”像平铺的匹练,这种感受就成为“诗料”,写在这首诗里。再像在《晚眺》中,看到无尽的诗思,怕来不及抓。再像《山行》里写眼前景物都是诗句,一时无从抓起,只点出这些景物在哪里:“乱松深处石桥西”。这又是一种写法。再用反衬的说法,说江南无画手来画,衬出风景的美好,非画手所能画,而放翁的诗却能描画。或说用诗来“摹写不能工”,即景物的美好,超过诗人的摹写。再看苏轼的《书昙秀诗》:
昙秀作诗云:“扁舟乘兴到山光(寺名),古寺临流胜气藏。惭愧南风知我意,吹将草木作天香。”予和云:
“闲里清游借隙光,醉时真境发天藏。梦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风草木香。”予昔时对欧阳文忠公诵文与可诗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与可诗,世间原有此句,与可拾得耳。”
在这里,苏轼点出“醉时真境发天藏”,很有意思。为什么同是景物,一般人看过也就看过了,诗人看了,却能看出其中含有诗料,把它捉住,写入诗中呢?这就是诗人从景物中看到真境,能够揭发大自然的奥秘。像昙秀诗里写的南风“吹将草木作天香”,就是一种感受,就是揭发大自然的奥秘,所以说:“梦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风草木香。”“梦回”即指“醉时真境”,醉时忘掉了人世的争名争利的干扰,才能领略到“真境”,即大自然的奥秘,即“十里南风草木香”。这个真境是客观存在,一般人领略不到,昙秀在梦回时领略到了,所以称为“拾得吹来句”,即把客观存在的真景拾来了。苏轼给欧阳修诵文同诗:“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写美人却扇,不用扇障面,她坐在花下,容光焕发,使花害羞落下。文同看到了,借此来赞美美人的美。欧阳修所以说:“世间原有此句,与可拾得耳。”是因为美人坐在花下,有花落下来,这是客观存在。把它说成“羞落庭下花”,这却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南风吹来草木的香气,这是客观存在,诗人写成“惭愧南风知我意,吹将草木作天香”。这却是诗人的感受。客观存在中有很多美好的景物,还要靠诗人对这些景物作出感受,才能写成为诗。把“山光”看成“染黛”,把“川气”看成“熔银”,把“奇峰”看成“角立千螺”,把“远水”看成“平铺匹练”,这些都是诗人从景物中所产生的感受,即看到“真境发天藏”,这样才能写成诗。
钱先生称“杨诚斋言得句,几如自献不待招”,即杨万里《荆溪集序》所谓:“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去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但杨万里要把客观景物写入诗中,还得凭自己对客观景物的感受。如写《晓经潘葑》,看到岸柳垂条,一定要产生“岸柳垂头向人揖”,这是诗人的感受,有了这个感受才好写入诗中。再像《船过灵洲》,看到江山,产生“惨淡真如画”的感受,看到烟雨,有了“空濛自一奇”的感受,才好写入诗句。再像《晓行东园》:“好诗排闼来寻我”,产生了美好景物构成诗料排闼来找我的感受,才写成诗。而方回却用另一种写法,写出诗人对美好景物的感受,稍纵即逝,不抓住,立刻就消失了。在这里钱先生又提到唐庚和陈与义。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里选了唐庚《春日郊外》:“疑此江头有佳句,为君寻取却茫茫。”在注里说:眼前景物都是诗意,心里忽有触悟,但是又写不出来。参看苏轼《和陶〈田园杂兴〉》:“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茫。”;陈与义:“新诗满眼不能栽”;又《春日》:“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又《题酒务壁》:“佳句忽堕前,追摹已难真。”这里指出有两点:一是看到佳景,但没有产生感触,写不成诗;一是有了感触,但没把它抓住,稍纵即逝,这样也写不出诗。
(七)创作前的精神准备
东坡《送参寥》①有云:“颇怪浮屠人,谁与发豪猛②。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③。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静了群动”,暗合载之之意④,“空纳万境”,明同梦得之言⑤;“咸酸中有至味”,又本司空表圣《与李生论诗书》之旨⑥。东坡《书黄子思诗后》极推表圣论诗⑦,而表圣固沧浪之先河;东坡此篇殊可玩味。(260页)
①苏轼《送参寥》。参寥:僧道潜,字参寥。
②《送参寥》:“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浮屠人,指和尚。《维摩诘所说经》:“是身如丘井。”颇怪和尚是淡泊的,谁与他发豪猛呢。
③真巧非幻影:和尚真是巧妙的,他的作为,并非幻影。
④“静了群动”,暗合载之之意:唐权载之《送灵彻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读其词者,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
⑤“空纳万境”,明同梦得之言:刘梦得《秋日过鸿举法院便送归江陵引》:“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
⑥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若醯(醋),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盐),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
⑦苏轼《书黄子里诗集后》:“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
这里讲创作以前的精神准备和创作时的要求。《荀子•解蔽》:“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心未尝不藏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在酝酿文思时,着重在虚心和宁静。只有虚心,才能采纳不同意见;只有专一,才能专心体察,看到问题;只有静心,才能看得细致。所以在酝酿文思时,重在虚心和宁静。苏轼在这里提出:“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即着重虚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心静不浮躁,才能仔细观察。了解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吸收了各种各样的境界,才能反映各种新的生活,写出新的境界,才能使诗语妙。创作时还要求“至味永”。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说:司空图“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又称:“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那末他引司空图所讲的味外味,即在简古中含有纤秾,在淡泊中含有至味。因为所反映的是新的生活,所写的是新的境界,给人以清新的感觉,所以虽写得简古淡泊,还是含有至味。这是可以玩味的。
(八)“即物生情”与“执情强物”
元僧觉隐妙语所云:“我以喜气写兰,怒气写竹。”《佩文斋书画谱》卷十六引《紫桃轩杂缀》①,按《杂缀》无此则。北宋以后,抉剔此秘而无遗。抑所谓我,乃喜怒哀乐未发之我;虽性情各具,而非感情用事,乃无容心而即物生情,非挟成见而执情强物。春山冶笑,我只见春山之态本然;秋气清严,我以为秋气之性如是。皆不期有当于吾心者也。李太白《赠横山周处士》诗,言其放浪山水,有曰:“当其得意时,心与天壤俱,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苏东坡《书晁补之藏与可画竹》第一首曰②:“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③。”董彦远《广川画跋》卷四《书李营丘山水图》曰④:“为画而至相忘画者”;卷六《书时记室藏山水图》曰:“初若可见,忽然忘之”;又《书范宽山川图》曰:“神凝智解,无复山水之相”;又《书李成画后》曰:“积好在心,久而化之。举天机而见者山也,其画忘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记曾无疑论画草虫云⑤:“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曰“安识身有无”,曰“嗒然遗其身”,曰“相忘”,曰“不知”,最道得出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否则先入为主,吾心一执,不见物态万殊。春可乐而庾信《和庾四》则云:“无妨对春日,怀抱只言秋。”秋可悲而范坚乃有意作《美秋赋》,唐贾至《淝州秋兴亭记》、李白《秋日鲁郡尧祠亭赠别》、刘禹锡《秋词》旨言秋之可喜。汉《郊祀歌•日出入》篇曰:“春非我春,夏非我夏。”回黄转绿,看朱成碧。良以心不虚静,挟私蔽欲,则其观物也,亦如《列子•说符》篇记亡斧者之视邻人之子矣。我既有障,物遂失真,同感沦于幻觉。如孔德璋《北山移文》之“风云带愤,石泉下怆,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林惭无尽,涧愧不歇”⑥,虽极嘲讽之致,无与游观之美。试以“北陇腾笑”,与“晚出淡笑”相较,差异显然。长吉诗中好用涕泪等字⑦,亦先入为主之类也。至吾国堪舆之学,虽荒诞无稽,而其论山水血脉形势,亦与绘画之同感无异,特为术数所掩耳。李巨来《穆堂别稿》卷四十四《秋山论文》一则曰⑧:“相冢书云:山静物也,欲其动;水动物也,欲其静。此语妙得文家之秘”云云。按《青乌先生葬经》⑨:“山欲其凝,水欲其澄”两句下旧注云:“山本乎静欲其动,水本乎动欲其静。”穆堂引语殆本此。实则山水画之理,亦不外是。堪舆之通于艺术,犹八股之通于戏剧,是在善简别者不一笔抹煞焉。(55—57页)
①《紫桃轩杂缀》三卷,《又缀》三卷,明李日华撰,中有论书画处。
②苏东坡:苏轼字。与可:文同字。
③嗒(tà榻)然:亦作“嗒焉”,状沮丧。《庄子•齐物论》:“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偶。”
④董彦远:董逌字。
⑤《鹤林玉露》十六卷,似诗话兼语录。
⑥孔德璋:孔稚珪字。南齐周彦伦隐居锺出(即北出),后出为海盐令。秩满入京,复经此山。孔稚珪写《移文》只是说,你一直在做官,何必在山里造隐舍,到山里来住呢?文章写得夸张了些,引起了人们的误解。
⑦长吉:李贺字,有《昌谷集》四卷。
⑧李巨来:李绂字,有《穆堂别稿》五十卷。
⑨《青乌先生葬经》一卷,青乌子名见《晋书•郭璞传》。此书为后人托郭璞名所作。
这里讲两种创作方法:一是“即物生情”,一是“执情强物”。先说“即物生情”。如写“春出冶笑”,是认为春山本身具有冶笑的情态,不是诗人加上去的。这样说,诗人先要把春山比作美女,所以认为春山会冶笑。说“秋气清严”,认为秋天的气候本身是清严的。诗人从景物中看到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把它写出来。像“我以喜气写兰,怒气写竹”,即认为兰花本身具有使人喜爱的特点,所以这个“喜气”是兰花本身所具有的,不是画家加上去的。竹子挺拔上长,这是它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好像有怒气。这里的“我”,并没有喜怒哀乐的感情,所说的“喜气”、“怒气”,是从兰花和竹子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来的。不过要从兰花和竹子中看出喜气和怒气来,也要对兰花和竹子有感情,只是这种感情是从兰花和竹子中生出来的,所以称“即物生情”。文与可画竹时,只看到竹,忘记了自己,即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意想中的竹子上,意想中的竹子是从观察中来的。在观察时,注意竹子的各种姿态,这各种姿态是竹子本身所具有的。画竹时,把意想中的竹子的各种姿态画到纸上,画出竹的各种姿态来,不是临摹前人的画竹,所以“无穷出清新”。因为注意力集中在画意想中的竹子,所以“见竹不见人”,也忘了自身,所以“其身与竹化”,这就是“凝神”。又如画山,不是对着山写生,是在观察中看到山的各种情态,引起爱好。这种爱好,积累起来,形成一种典型的形象,这叫“积好在心”。这种“积好”,是积累许多山的好的形象形成的,形成一个典型,这就是“久而化之”。是“神凝智解,无复山水之相”。即这个典型,不再是一山一水的形象了。“举天机而见者山也,其画忘也”,这个意想中的山,是“积好在心”,这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是“天机”,所见的是“积好”的山,是忘掉一山一水的山。再像画草虫,在观察中看到草虫的各种姿态,画时全神贯注在草虫的各种姿态上,忘掉了自身。像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好像此身化成蝴蝶。所以说“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草虫的跳动,好像我身在跳动了。这就做到“即物生情”,能把物的各种情态画出来,“无穷出清新”了。
再看“执情强物”,作者自己有了喜怒哀乐的感情,把这种感情著到物上,这是强加上去的。如瘐信在北周愁苦,认为美好的春天也像秋天那样使人愁苦。晋代范坚写《美秋赋》,认为秋天也是美好的。唐朝贾至作《淝州秋兴亭记》称:“四时之兴,秋兴最高。”认为登亭观望,秋天兴致最高。李白《秋日鲁郡尧祠亭赠别》:“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把我觉秋兴的美好,加到秋兴上。刘禹锡《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也是把个人爱秋的感情加到秋上。汉《郊祀歌•日出入》:“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这里指出世乱时代,与人民求治的愿望不同,所以春夏秋冬四季都觉得苦恼,即以苦恼的感情加在四季上。“回黄转绿,看朱成碧”,指时令的变化,由秋冬百草的枯黄,转到春天的碧绿。看到红花落了,绿叶抽了。作者把主观的感情色彩著到景物上去。《列子•说符》记有人丢了斧子,疑心邻人之子偷的,看他的走路、言语、态度,都像偷斧子的。后来找到了斧子,再看邻人之子,走路、言语、态度都不像偷斧子的。这说明主观在起作用。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一说周彦伦曾隐居北山,后出山做官。后又要经过此山,孔稚珪因假借山灵来嘲笑他的假隐居,写林木涧泉为他的假隐居而感到惭愧。这是作者把主观的感情加到山林泉涧上去。再像说,山是静的,要它动;水是动的,要他静。这是看风水的把主观的想法加到山水上去。李绂借它来讲写作,即把作者的主观感情著到景物上去,即“执情强物。”
按“即物生情”与“执情强物”,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即写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有我之境”即以我的感情色彩著在景物上。不过将“无我之境”理解为“即物生情”,这个“情”是我看到的物的情态,这里显然并非真是无我,所以称“无我”还不如称“即物生情”更为确切些。
(九)心以应物,意到笔随
流俗以为艺事有敲门砖,鸳鸯绣出,金针可度,只须学得口诀手法,便能成就。此说洵足为诗窖子、画匠针砭。然矫枉过正,诸凡意到而笔未随、气吞而笔未到之境界,既忽而不论,且一意排除心手间之扞格,反使浅尝妄作、畏难取巧之徒,得以直书胸臆为借口。夫艺也者,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兴象意境,心之事也;所资以驱遣而抒写兴象意境者,物之事也。物各有性: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应物。一艺之成,而三者具焉。自心言之,则生于心者应于手,出于手者形于物,如《吕览•精通》篇所谓:“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应之。①”自物言之,则以心就手,以手合物,如《庄子•天道》篇所谓:“得手应心”②,《达生》篇所谓:“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③”Croce执心弃物④,何其顾此失彼也。夫大家之能得心应手,正先由于得手应心。技术工夫,习物能应;真积力久,学化于才,熟而能巧。专恃技巧不成大家,非大家不须技巧也,更非若须技巧即不成大家也。“画以心不以手”,立说似新,实则王子安“腹稿”⑤、文与可“胸有成竹”之类⑥,乃不在纸上起草,而在胸中打稿耳。其由尝试以至成功,无乎不同。胸中所位置安排、删削增改者,亦即纸上之文字笔墨,何尝能超越迹象、废除技巧。纸上起草,本非全盘由手;胸中打稿,亦岂一切唯心哉。《朱文公集》卷四十五《答杨子直书》之一云⑦:“身心内外,初无间隔。所谓心者,固主乎内。而凡视听言动出处语默之见于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尝离也。今于其空虚不用之处,则操而存之;于其流行运用之实,则弃而不省。此于心之全体,虽得其半,而失其半矣。”高攀尤《困学记》云:“心不专在方寸,浑身是心。⑧”融澈之论,正可移用。是以G.C.Lichtenberg游英,睹名伶Garrick演剧⑨,嚬笑运为,无不入妙,叹曰:“此人竟体肌肉中,无处非灵心。”《梁书•裴子野传》⑩:“或问其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虽有见否之殊,其于刊改一也。”此即“画以心而不以手”之好注脚。E.Mach论科学家推求物理⑾,尝标“经济”为原则,谓不每事实验,而以推想代之,乃所以节省精力。致知造艺,心同此理尔。(210—212页)
①《吕氏春秋•精通》:“锺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使人召而问之。”答称母为公家酿酒,己为公家击磬,不见母三年矣,是故悲,锺子期叹谓“悲存乎心,而木石应之。”
②《庄子•天道》:轮扁讲砍木为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
③《庄子•达生》:“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工倕用手指旋转画圆胜过圆规,手指化成圆规的巧妙,在于心不停留。
④Croce:克罗齐,十九、二十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美学家。他抛弃了先验主义的方法。
⑤腹稿:《唐诗纪事》:“[王]勃(字子安)为文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书之,初不加点,时谓腹稿。”
⑥胸有成竹:苏轼《筼筜谷偃竹记》:“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
⑦朱文公:朱熹谥。
⑧高拳龙:明代作家,有《高子遗书》十二卷。
⑨G.C.Lichtenberg:里希登贝克,十八世纪德国物理学家、讽刺作家。Garrick:加里克,十八世纪英国戏剧家、演员。
⑩《梁书》:唐姚思廉撰,五十六卷。
⑾E.Mach:马赫,十九、二十世纪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
这则讲创作的物——意——笔——辞,从观察外物,到形成意境或题旨,到用笔表达,成为文辞。这里根据“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认为看到金针度人的绣法,即学习一些写作法,就可以直抒胸臆来写,来画,只能成为“诗窖子”,像《类说》二六称宋王仁裕作诗万首称诗窖子,即多而不精妙。像绘画的只能成为画匠,即会画而不能成为名家。陆机的《文赋》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称:“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从观察外物到形成一个意,即主旨,意与物之间不免有距离,所谓“意不称物”。有了“意”用文辞来表达,又怕“文不逮意”。从物到意到辞处理得恰好的,称“密则无际”;从物到意到辞有距离的称“疏则千里”。钱先生称“意到而笔未随、气吞而笔未到”,即意能称物,故称“意到”,“辞不逮意”,故称“笔未随”,是文辞的表达不能达意。钱先生又从心物两端分开来讲,从观察物象到形成兴象意境,是心之事。把兴象意境写成文辞,是物之事,即手笔的事。钱先生又引《吕览•精通》里称有人心悲,击磬时发出悲声,是木石应与心。又引轮扁砍轮,得心应手,心应于手。工倕用手代圆规,是“指与物化”,即手指化成圆规。这里指出怎样打破心与手的距离,即打破“文不逮意”的距离。从轮扁砍轮得心应手里,从工倕以指画圆的指与物化里,可以看到轮扁是在长期砍轮的实践中达到得心应手。那末要打破“文不逮意”,光靠懂得一点写作方法是不够的,要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做到得心应手才成。钱先生称“真积力久,学化于才,熟而能巧。”即要积累真实的实践,达到“指与物化”,熟能生巧。所谓王勃的腹稿,文同的胸有成竹,是在胸中打草稿,在胸中做好删削增改,在胸中做好得手应心的工作,才可以立即写出。钱先生又指出:朱熹说的:“身心内外,初无间隔。”先是手不应心,心里想好的兴象意境,手笔写不出来。经过写作的长期实践,做到得心应手,心里想到什么意境,手笔能够如实表达出来,最后心与物化,心和手一致,心怎样想,手怎样写,心的灵巧完全表现在手上。好比名演员的表现,所有灵心妙想,完全表现在肌肉中了。这就是创作达到的很高境界了。但这里还需要心有灵心妙想,要打破“意不称物”问题。刘勰在《神思》里曾讨论这个问题,陆机在《文赋》里也讨论过这些问题,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一○)“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新补六①《再次韵杨明叔•引》:“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此诗人之奇也。”天社无注②。按《后山集》卷二十三《诗话》云③:“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④。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圣俞答书似已失传,赖后山援引,方知山谷所本。葛常之《韵语阳秋》卷三称山谷与杨明叔论诗此语⑤,盖南宋初人早征古而忘祖矣。《中州集》卷二引李屏山为刘西嵓诗序亦以此为山谷诗法⑥,更无足怪。近世俄国形式主义文评家希克洛夫斯基等以为文词最易袭故蹈常,落套刻板,故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或亦曰使文者野。窃谓圣俞二语,夙悟先觉。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六一诗话》记圣俞论诗所谓“状难写之境,含不尽之意”⑦,数百年来已熟挂谈艺者口角。而山谷、后山祖述圣俞论诗语,迄无过问者,故拈出而稍拂拭之。抑不独修词为然,选材取境,亦复如是。歌德、诺瓦利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狄更斯、福楼拜、尼采、巴斯可里等皆言观事体物⑧,当以故为新,即熟见生。(320—321页)
《东坡题跋》卷二《题柳子厚诗》之二:“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亦如山谷之隐取圣俞语,而专为“用事”发,似逊原语之通方也。(《钱锺书研究》7页)
①新补:《谈艺录》补订本新补宋黄庭坚诗注第六个注。
②天社:任渊号天社,注黄庭坚诗内集。
③《后山集》:宋陈师道号后山,有《后山集》二十四卷及《后山诗话》。
④梅圣俞:宋梅尧臣字。
⑤葛常之:葛立方字常之。《韵语阳秋》二十卷,主要评论诗的立意的诗话。
⑥《中州集》:金元好问编,十卷,选录金代人诗。
⑦《六一诗话》:一卷,宋欧阳修著。
⑧歌德:十八、十九世纪德国作家。
诺瓦利斯: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
华兹华斯: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湖畔派诗人。
柯尔律治:十八、十九世纪英国诗人。
雪莱:十八、十九世纪英国诗人。
狄更斯: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
福楼拜: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
尼采: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
巴斯可里: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初意大利诗人。
这一则是讲“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创作方法。这个创作方法,钱先生考出始见于梅尧臣的信里,但这封信已无考,见陈师道的《后山诗话》里提到过。“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另一种提法是“使熟者生,使文者野”。按《南齐书•文学传论》:“习玩为理,事久则黩,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文章怕写得平凡的旧的。俗指庸俗,即平庸,故指陈旧。提出“新变”,即变庸俗为雅正,变陈旧为清新。庸俗的陈旧的已经过时,人家不要看,所以要变。变庸俗为雅正,雅即正,指正确的。变陈旧的为清新的,是新鲜的,人家就爱看。“使熟者生”,即变旧为新,大家熟悉的是旧了,所以要变新的。“使文者野”,按《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野指乡野的质朴,史指掌史书的多闻习事而诚不足,即史文的华伪。“使文者野”即使华伪的文辞变为诚朴。诚朴才正确,华伪才庸俗,“使文者野”,也就近于“以俗为雅”了。钱先生从另一角度讲,“使文者野”,反过来即“使野者文”,使乡野的俗语变为文雅,即“以俗为雅”。钱先生又指出“选材取境,亦复如是。”把庸俗的变为雅正的,把陈旧的变为清新的,恐离不开选材取境。写作时,选取正确的新鲜的材料,抛弃庸俗的陈旧的材料,就能“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取境也是这样。
在《东坡题跋》里指出“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也有局限,倘为了“好奇务新,乃诗之病。”钱先生指出,这样讲,也像黄庭坚的称引这两句话,专为“用事”发。其实“选材取境,亦复如是”。这两句话所指,包括选材取境在内,不限于用事。因此苏轼的话,“似逊原语之通方”,假如在用事上好奇务新,“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确有局限。但在选材取境上“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就没有局限,如钱先生《宋诗选注》选郑文宝《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注里称:“这首诗很像唐朝韦庄的《古离别》:‘晴烟漠漠柳毵毵,不那离情酒半酣。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是江南。’但是第三第四句那种写法,比韦庄的后半首新鲜深细得多了。”郑文宝的诗,就属于在选材取境上比韦庄的诗新鲜深细,所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