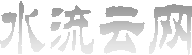七、风格
(一)南北文学风格之别
文人相轻,故班固则短傅毅①;乡曲相私,故齐人仅知管晏②。合斯二者,而谈艺有南北之见。虽在普天率土大一统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为己长彼短之本。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义之评量③,更类七国五胡之争长④,亦风雅之相斫书矣⑤。《三国志•吴志•张纮传》裴注引陈琳书曰⑥:“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⑦,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谈,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⑧,足下与子布在彼⑨,所谓小巫见大巫⑩,神气尽矣。”已为北文不如南文张本⑾。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略谓⑿:“洛阳江左,文雅尤甚。江左贵乎清绮⒀:河朔重乎气质⒁。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按但言“质胜”,即是文输⒂。是以北朝文士,邢邵、魏收实为冠冕⒃,而《北齐书•魏收传》载邵讥收“于任昉⒄,非宜模拟,亦大偷窃”,收斥邵“于沈约集中作贼”⒅;则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机杼⒆。张鷟《朝野佥载》记庾信入北⒇,谓北中文事,“惟韩陵温子昇碑堪共语(21),余皆驴鸣大吠聒耳”。南人轻北,其来旧矣。宋自靖康南渡(22),残山剩水,隅守偏安,以淮南淮北之鸡犬声相闻(23),竟成南海北海之马牛风不及(24)。元遗山以骚怨弘衍之才(25),崛起金季,苞桑之惧,沧桑之痛(26),发为声诗,情并七哀,变穷百态。北方之强,盖宋人江湖末派(27),无足与抗衡者,亦南风之不竞也(28)。虽以方虚谷之自居南宋遗老、西江后劲(29),《桐江续集》卷二十四《次韵高子明投赠》七律论北方词章,亦不得不曰:“尚有文才与古班,诗律规随元好问。”汪尧峰好挦撦南宋作家(30),而《钝翁类稿》卷八《读宋人诗》第四首亦曰:“后村傲睨四灵间(31),尚与前贤隔一关。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让遗山。”遗山论诗,《中州》名集,实寓南宋偏安之意;故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三十八所载宋流人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32),即云:“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而况于在中州者乎”,《则堂集》失收。可谓义正而词婉者。(150—151页)
①班固:汉代著名史学家,著有《汉书》。傅毅与班固共校典书。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看轻)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作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②管:春秋管仲,相齐桓公。晏:春秋晏婴,相齐景公。《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③四始六义:按《毛诗大序》谓诗有四始,据郑玄说,以风、小雅、大雅、颂为王道兴衰所由始。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
④七国:指战国时的封建诸侯国秦、楚、燕、齐、韩、赵、魏,彼此争雄。五胡:东晋南北朝时北方西部的少数民族匈奴、羯、鲜卑、氏、羌。
⑤相斫书:《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谓隗禧称《左传》为“相斫书”。
⑥南朝刘宋时史学家裴松之,为晋陈寿撰之《三国志》作注。陈琳:建安七子之一,有文集十卷。
⑦雄伯:出类拔萃。
⑧景兴:三国魏经学家王朗字。
⑨子布:三国吴史学家张昭字。
⑩小巫:陈琳自比。大巫:指三国吴张纮、张昭,孙策创业,张氏二人并为参谋,后张纮辅佐孙权,陈琳自认不如他们。
⑾张本:犹伏笔。为北文不如南文之说预先造了舆论。
⑿李延寿:唐代史学家,撰有南北史。
⒀江左:指南朝文人。他们作诗文注重表现清丽脱俗和华美艳丽的文采。
⒁河朔:指北朝文人。他们作诗文注重表现质直的气度。
⒂质胜文输:指北朝文学不如南朝。
⒃邢邵:北齐文学家,时温子昇为文士之冠,世称“温邢”,温死,又称“邢魏(收)”。撰有文集三十卷。魏收:北齐作家,与温子昇、邢邵有三才之称,有文集七十卷。
⒄《北齐书》:唐李百药撰,五十卷。任昉:后汉文史家,有诗文三十四卷,《杂传》二百四十七卷。
⒅沈约:梁文史家,有文集百卷。
⒆自然机杼:指创造、创作。
⒇张鷟《朝野佥载》:唐人笔记,一卷。庾信:北朝文学家。初仕南朝梁,后仕西魏、北周。
(21)《朝野佥载》记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时温子昇作《韩陵山寺碑》,为庾信所称赏。
(22)靖康南渡: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亡,宋高宗南渡建南宋。
(23)鸡犬声相闻:见《老子》八十章。这里是比喻淮南淮北相距之近。
(24)南海北海之马牛风不及:《左传》僖公四年:“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北海与南海的不相及,好比马与牛不相引诱。这里指淮南淮北分属两个王朝。
(25)元遗山:元代文学家元好问字。有《遗山诗集》二十卷、《中州集》十卷。弘衍:广博。
(26)苞桑之惧:《易•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苞桑之惧即亡国之惧。沧桑之痛:沧海变桑田,即亡国之痛。
(27)江湖末派:南宋陈起编《江湖集》,有《前集》、《后集》、《续集》等,少则二十八家,多至六十四家,为江湖诗人,称江湖派。《四库总目》称:“宋末诗格卑靡,所录不必尽工。”
(28)南风不竞:《左传》襄公十八年:“师旷曰:‘不害。我弦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即南不如北。
(29)方虚谷:元方回号。因生于南宋,宋降元后,自称遗老,为江西派后劲。有《桐江集》八卷,《续集》三十七卷。
(30)汪尧峰:清文学家汪琬,字苕文,号钝翁,晚号尧峰。撰有《钝翁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三十卷。
(31)后村:宋代作家刘克庄,自号后村居士。四灵:南宋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辉)、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
(32)《国朝文类》:即《元文类》,七十卷,元代苏天爵编。《则堂集》:宋家铉翁撰,六卷。
这一则讲诗文有南北风格的区别,这是由于南北地域不同,文化风俗不同,学风不同,诗文风格也就有所不同。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政治原因,有过两次南北分治,先是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后是南宋与金的对峙,造成了南北的隔阂,文学上出现南北不同的风格,评论上也有南北之见。
(一)南北朝时期,文评者的南北之见,多表现在南人轻北。比如陈琳因去河北投袁绍,处在文人较少的环境中,成了出类拔萃的文学家,但是,在他给江苏广陵同乡张纮的信中,表示与张纮、张昭相比,还自惭不如,为北文不如南文之说先造了舆论。
温子昇、邢邵、魏收,都是北朝文学的佼佼者,但从《北齐书•魏收传》看,邢魏所以成名,因为邢邵师法沈约,魏收师法任昉,然“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机杼”,所以,邢魏互相讥笑为“偷窃”、“作贼”。《朝野佥载》也记载了南人庾信到了北方,瞧不起北文,以为只有写《韩陵山寺碑》的温子昇才配与他共语。可见,“南人轻北,其来旧矣”。这里指出,所以有南人轻北的原因,主要是与中国长期以来积淀的文化心理因素有关,一是文人相轻,二是乡曲相私。
南北的文学风格,究竟不同在哪里,据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里说,南方文风文雅,贵清绮,重形式,文辞华美,以诗擅胜,宜于咏歌;北文文风质朴,贵刚直,重内容,气质高昂,以文见长,便于实用。概括地说,就是北文理胜其辞,南文辞过其意。因为南人北人的自然环境、生活习惯不同,造成性情气质上的差异,已带有传统性,反映到诗文上自然有不同风格。
先说民歌的风格,南北就明显的不同,南方多委婉曲折的情诗,如“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子夜歌》)对恋人的思念深沉含蓄。北方民歌抒情的气势豪宕,境界宏阔,情感粗犷,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再说文人的风格,南方重形式和音调,如梁沈约的《登北固楼》:
六代旧山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柳色天。伤时为怀古,垂泪国门前。
又吴均《发湘江赠亲故别》之三:
君留朱门里,我至广江濆。城高望犹见,风多听不闻。流苹方绕绕,落叶尚纷纷。无由得共赏,山川间白云。
虽是不同题材的诗,却都写的委婉含蓄,自然流畅,给人一种格调清新之感,在音律上已有了律句的格调。北方文人作品的风格,不像民歌的特色鲜明,可能是由于模仿南风,反而缺少北方豪放的气概。如魏收《挟琴歌》: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筯下成行。
又,邢邵《思公子》: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这两位都是北朝著名的文学家,可是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就从这几首明白如话的诗来看,他们确实受到南方香艳诗的影响不小,其中虽也不乏清远敦厚之趣,却不给人格调刚健之感。抛开文暂且不谈,单以诗相比,南北朝时期,北方确实逊于南方,直到南方的庾信到北周,王褒也留在北方以后,他们以清新绮艳的风格吸引了北方文士竞相模仿,才出现了南北风格互为影响的新局面。
(二)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临安(今杭州)以后,使文坛起了变化。淮南淮北虽如往常鸡犬之声相闻,但已成为南宋与金不同的两个社会。太原的元好问,具有汉民族良好的文化教养和他本人过人的天赋,身处金国,国破家亡之痛,使他在多方面显露出才华,成为金朝文坛上的大家。他文师韩欧,诗师杜甫,词学周邦彦,多方面丰富自己,“发为声诗”,“变穷百态”,不是南方的江湖末派可以相比的。清汪琬好摘取南宋作家诗,但他在评论宋人诗时,把元好问推作中原的代表,这个评价并不过份。让我们看一看无好问诗的风格,如:
南朝辞臣北朝客,栖迟零落无颜色。阳平城边握君手,不似铜驼洛阳陌。去年春风吹雁回,今年雁逐秋风来。春风秋风雁声里,行人日暮心悠哉。长江大浪金山下,吴儿舟船疾如马。西湖十月赏风烟,想得新诗更潇洒。(《送张君美往南中》)
又,《怀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谷口暮云知郑重,林梢残照故分明。洛阳见说兵犹满,半夜悲歌意未平。
两诗沉挚悲凉,读来可歌可泣,创造出自己的声调,自己的风格。
最后钱先生举引元苏天爵的话作这一则的小结:地域有南北之分,人无南北之分,因为南北继承的文化传统是共同的,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也都是中州文化。元代以后的诗文发展更证实了苏氏的论断。可见苏天爵的见解是“义正而词婉”。
(二)唐宋诗风格之别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①,《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②,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③,则宋人之有唐音者。《杨诚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诗序》曰④:“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刘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小序》仍以后山、陵阳、子勉、均父、二林⑤等皆非江西人为疑,似未闻诚斋此论。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序之恉。(2页)
后见吴雨僧先生宓《艮斋诗草序》⑥,亦持是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⑦。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叶横山《原诗》⑧内篇卷二云:“譬之地之生木,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谢而复开。”蒋心余《忠雅堂诗集》⑨卷十三《辩诗》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可见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极之有两仪,本乎人质之判“玄虑”、“明白”,见刘邵《人物志•九征》篇。按即Jung:psychologischeTypen所分之Introvert与Extravert⑩。非徒朝代时期之谓矣。乃尚有老宿⑾,或则虐今荣古,谓宋诗时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则谓唐诗太古,宜学荀卿之法后王⑿。均堪绝倒。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⒀,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⒁。若木之明,崦嵫之景⒂,心光既异,心声亦以先后不侔⒃。明之王弇州⒄,即可作证。弇州于嘉靖七子,实为冠冕;言文必西汉,言诗必盛唐。《四部稿》中⒅,莫非实大声弘之体。然弇州《续稿》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屡和东坡诗韵。《续稿》卷四十一《宋诗选序》自言,尝抑宋诗者,“为惜格故”,此则“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苏长公外纪序》于东坡才情,赞不容口,且曰:“当吾之少壮时,与于鳞习为古文词⒆,于四家殊不能相入⒇,晚而稍安之。毋论苏公文,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糅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读书后》(21)卷四《书苏诗》后曰:“长公诗在当时,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其后则若垓下之战(22),正统离而不再属。今虽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颇不以为然。”下文详言东坡神明乎少陵诗法之处,可与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艺苑卮言》论东坡语参观。然《卮言》以东坡配香山、剑南为正宗而外之广大教化主(23),又曰:“苏之于白,尘矣”;此则径以苏接杜,识见大不同。《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后放言》云:“死亦不须埋我,教他蚁乐鸢愁”,全本东坡“闻道刘伶死便埋”一绝,则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苏诗矣。虽词气尚负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则已悦服。故钱牧斋《列朝诗集》丁集(24)、周栎园《因树屋书影》卷一皆记弇州临殁(25),手坡集不释。要可征祖祧唐宋,有关年事气禀矣。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诗学之不同,非谓弇州晚年诗胜早年也。吴梅村《家藏稿》(26)卷三十《太仓十子诗序》有“拯晚近诗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词雄响,而表晚岁颓然自放之言,诎申颠倒”云云,议论极公。弇州《续稿》中篇什,有意无韵,木强率直,实不如前稿之声情并茂;盖变未至道,况而愈下者也。近来湖外诗家(27),若陈抱碧、程十发辈(28),由唐转宋,适堪例类。唐宋诗之争,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与施兰垞书》,《随园诗话》卷十六引徐朗斋语等调停之说(29),当时亦早有。如戴昺《东野农歌集》(30)卷四《答妄论唐宋诗体者》云:“不用雕锼呕肺肠,词能达意即文章。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不知格调之别,正本性情;性情虽主故常,亦能变运。岂曰强生区别,划水难分;直恐自有异同,抟沙不聚。《庄子•德充符》肝胆之论(31),东坡《赤壁赋》水月之问(32),可以破东野之惑矣。(3—5页)
①严仪卿:宋诗论家严羽字,号沧浪逋客。著有《沧浪诗话》一卷,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类论述宋以前诗。
②少陵:唐杜甫自称少陵野老。昌黎:唐韩愈,郡望昌黎。香山:唐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东野:唐孟郊字。
③柯山:宋张耒号。白石:宋姜夔,号白石道人。九僧:指宋代九诗僧:淮南惠崇,剑南希画,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维凤,江东宇昭,峨眉怀古。有集《九僧诗》,已佚。四灵:指南宋后期浙江永嘉四诗人:徐照(字灵辉),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四人字号中皆有“灵”字。
④《杨诚斋集》:宋杨万里(号诚斋)撰,一百三十三卷。江西诗派:宋诗流派之一,以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荮、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等二十五人。他们效法杜甫、韩愈,主张无一字无来历,追求奇崛、用典,提倡“脱胎换骨”,致使形式雕琢。
⑤《刘后村大全集》:宋刘克庄(号后村)著,一百九十六卷。后山:宋陈师道,号后山居士。陵阳:宋韩驹,字子苍,有《陵阳集》。子勉:宋高勉字。均父:宋夏倪字。二林:指江西诗派的林敏修、林敏功。
⑥吴宓:近人,又字雨生,号藤影荷声馆主。
⑦畛域:界限。
⑧叶横山:清叶燮号,原名叶星期。撰有《原诗》四卷。论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作法等。
⑨蒋心余:清蒋士铨字。撰有《忠雅堂诗集》二十七卷。
⑩太极之有两仪:《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是生两仪(天地)。”刘邵:三国魏人。撰有《人物志》三卷。Jung:译名荣格,瑞士现代心理分析学家。其《心理学类型》所分之内向性格与外向性格。
⑾老宿:指老成有学问的人。
⑿荀卿:战国时人,著名哲学家荀况的尊称。法后王:见《荀子•非相》,取法于当代的君王,是荀况针对孔孟法先王而提出的,他认为法若与当代君王不一致,便要走到斜路上去。
⒀唐体:诗之一体。指长于丰神情韵的诗作,不限于唐代人的作品。
⒁宋调:诗之一体。指以筋骨思理取胜的诗作,不限于宋代人的作品。
⒂若木之明:若木,《山海经•大荒北经》指日出处的一种树,此指人的早年。崦嵫:山名,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古人称为日落处。
⒃不侔:不等。
⒄王弇州:明王世贞,号弇州山人。
⒅《四部稿》:王世贞撰,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零七卷。王氏才学富赡,虽称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然其早年诗作近于唐体,晚年作风有变,渐操宋调。
⒆于鳞:明李攀龙字。
⒇四家: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序》:“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长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这是于四姓文章中独推苏轼。王世贞、李攀龙两人少时不喜欢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他们少时论文,言必称秦汉之故。
(21)《读书后》:王世贞撰,八卷。
(22)求封西楚,垓下之战:项羽灭秦后,分封诸侯王。垓下战后,兵败自刎。用以比喻苏诗之遭遇。
(23)香山:唐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剑南:宋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有《剑南诗稿》。广大教化主:唐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一卷,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诗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称广大教化主者,于长庆得一人,曰白乐天;于元丰得一人焉,曰苏子瞻;于南渡后得一人,曰陆务观:为其情事景物之悉备也。就苏之与白,尘矣;陆之与苏,亦劫也。”钱先生认为“苏之与白,尘矣”,当指白居易较苏轼为尘俗,所以说“径以苏接杜”,以苏轼直接杜甫。
(24)《列朝诗集》:清钱谦益(号牧斋)选辑,八十一卷。约收明代两千多诗人之代表作。
(25)《因树屋书影》:清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著,十卷。
(26)吴梅村:清吴伟业号。有《吴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
(27)湖外:指湖南湖北。
(28)陈抱碧:当见于程十发《湘社集》四卷中。程十发:近人程颂万号。有《十发庵类稿》三十二卷,附《湘社集》四卷。
(29)袁子才:清袁枚字,号随园老人。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卷,《随园诗话》十六卷。袁枚《答施兰论诗书》:“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也,与唐宋无与也。”徐朗斋:清徐嵩号。《随园诗话》卷十六:“徐朗斋嵩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则宋、元、明三朝诗,俱号称唐诗;诸公何用争哉!须知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生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也。”
(30)戴昺:宋人,字东野。有《东野农歌集》五卷。
(31)《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出一也。”这是说,从异者看,唐诗中也有宋体;从同者看,宋诗中也有唐体。
(32)苏轼《前赤壁赋》:“客亦知夫水与月乎?……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视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是说,从变看,唐诗也有变;从不变看,唐宋诗都是不可变的。
这里两则讲唐诗、宋诗之别,主要不在朝代的区别,而是由于两种不同的风格,譬如天下有两种人,便有两种性情,也就分出两种诗来。
(一)风格是人的性情决定的,相同的朝代里,也会出现不同风格的作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唐诗、宋词,是以朝代区分盛行的文体,唐以诗胜,宋以词胜。钱先生称唐诗、宋诗是以风格区别的,他在《宋诗选注序》里讲得很透彻,这里袭用序中举引唐释皎然和宋姜夔的话来说明。皎氏云:“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唯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复忌太过”,“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诗式•复古通变体》),这是唐人作诗、评诗的标准,把“通变”看得比“复古”重要,写作上重在表现自我。姜氏云:“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白石道人诗集序》),这是宋人的话,只能在“合”中求“异”,甚至从古人作品中寻求作诗的灵感和榜样,再以说理、议论、故实入诗,形成了一种与唐诗不同的风格。宋代诗论家严羽第一个提倡断代论诗,便是为了研究诗歌发展到各个时期所表现的带有总体性的特征,他说宋人“尚理”,唐人“尚意兴”,是一个大致的概括,于诗前冠以唐、宋,也是为了称谓的方便,并不是说唐诗必出自唐人之手,宋诗必出自宋人之手,而是说诗“尚理”者近宋,“尚意兴”者近唐。袁枚《随园诗话》卷八亦云:“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
这里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也是一个大致的概括,在于指出所谓唐体、宋调的不同特征。比如杜甫、韩愈,都是唐代大诗人,而他们的作品却为宋调开了路。像杜甫的《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首诗中间两联在发议论,在说理,不在写意兴,不正是开宋诗的说理吗?再像韩愈的《龊龊》:
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氿澜。……
不也是在说理吗?
宋人诗作而有唐音者,这里列举张耒、赵师秀的诗作,可以看到他们的风格。如张耒《初见嵩山》:
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
真是潇洒自如,情景交融,丰神情韵均类唐诗。又如赵师秀《约客》: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其诗清新圆润。写景抒情之亲切,宛如出自唐人之手。说唐诗、宋诗主要是指诗的风格,正如杨万里说江西诗派,“诗江西,非人皆江西”,都是指诗的风格而言。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是江西人,他以“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的主张,团结了一批诗人,共同取法于各体的优点来作诗,形成一个风格接近的诗派,世人遂以江西称之,不是说这个诗派的成员都是江西人,也不是说这个诗派的诗都是在江西写的。
(二)时代与地域对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决定作品风格的主要是人的禀性。近人吴宓讲的“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也是指诗的两种不同风格。宋以后诗人辈出,似都未能跳出唐体、宋调。唐以前各代诗作的风格,似也可这样分析。正如叶燮在《原诗》里的比喻:木生于地,开出宋诗这朵奇葩,宋以后的诗,只是花开花谢、复开复谢的差别,终究离不开宋调。“木”便是人的秉性。蒋士铨《辩诗》也是这个意思。诗分唐宋,仿佛在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之时,便已经有了天地之别。魏刘邵撰《人物志》,把人的品性判作思虑深沉型和单纯开朗型,也就是荣格《心理学类型》里分的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这两种不同的品性,与朝代时期或地域环境,不能说没有关系,但都关系不大。(三)唐体宋调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而风格之别,本于性情,性情不是一成不变,风格也会随之变化。譬如人的一生,早年才气横溢,喜为唐体,暮年老成持重,易操宋调,王世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早年他的诗作多“矜气高腔”,如《登太白楼》:“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海阔天空,气势音节均似李白;到了晚年,他的作风有变,“平直切至”,如《太保歌》:“太保入朝门,缇骑若云屯。进见中贵人,人人若弟昆。太保从东来,一步一风雷。行者阑入室,居者颔其颏。……”写奸相严嵩耀武扬威的声势,历历在目,却风格朴实。王世贞对苏轼的看法也有前后的区别,少壮时是排苏,后来好苏,临死时竟“手坡集不释”。可见,继承唐体宋调与年事、秉性的关系颇大,但这并不是说王世贞晚年诗作就一定胜于早年。
总之,唐宋诗的风格不同,孰胜孰负,南宋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袁枚曾举引徐嵩的话:“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出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败石瓦砾,传自洪荒,不可谓之宝”(《随园诗话》卷十六)。袁枚举引徐嵩的这段话,该使人明白对于唐宋诗,似乎已无必要决出胜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