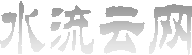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五)论水月镜花
《傅与砺诗集》冠以揭傒斯序①,有曰:“刘会孟尝序余族兄以直诗②,其言曰:诗欲离欲近;夫欲离欲近,如水中月,如镜中花。”今本《须溪集》中无此序③;《揭文安集》亦未收《傅诗集序》④,仅卷八《吴清宁文集序》称辰翁云:“须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论诗,数百年来一人。”傅诗揭序所引辰翁语,虽碎金片羽,直与《沧浪诗话•诗辩》言“神韵”⑤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云云,如出一口。
“不可凑泊”、“欲离欲近”,即释典所言“不即不离”。僧肇《释宝藏论•离微体静品》第二⑥:“离者,体不与物合,亦不与物离。譬如明镜,光映万象,然彼明镜,不与影合,亦不与体离。”唐译《华严经•十通品》第二十八⑦:“譬如日月、男子、女人、舍宅、山林、河泉等物,于油于水于宝于明镜等清净物中而现其影;影与油等,非一非异,非离非合,虽现其中,无所染着。”唐译《圆觉经》⑧:“世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不即不离,无缚无脱。”禅宗拈此为话头,而易其水镜之喻,如《五灯会元》卷十七黄龙祖心曰⑨:“唤作拳头则触,不唤作拳头则背”,又禅林《僧宝传》卷十二荐福古曰⑩:“臂如火聚,触之为烧,背之非火。”然则目辰翁为沧浪“正传”,似无不可,何止胡元瑞所谓“别传”哉⑾。“不触不背”、“不即不离”,视儒家言之“无适无莫”(《论语•里仁》)似更深入而浅出也。辰翁《陈简斋诗集序》亦《须溪集》所漏收,有云:“诗道如花,论高品则色不如香,论逼真则香不如色”;则犹陆农师《埤雅》卷十三引“俗谚”云⑿:“梅花优于香,桃花优于色。“香”自是诗中神韵佳譬。《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载张芸叟《评诗》⒀,于王介甫曰⒁:“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闻见,难有着摸”;正借释氏语,特不切介甫诗耳。声与色固“难着摸”,香只是气味,更不落迹象,无可“逼真”。西方诗人及论师每称香气为花之神或灵魂或心事流露,颇相发明。(426—427页)
《沧浪诗话》曰:“语忌直,脉忌露。”渔洋《师友诗传续录》曰⒂:“严仪卿以禅理喻诗⒃,内典所云⒄:不即不离,不脱不粘,曹洞所谓参活句⒅,是也”;《香祖笔记》曰⒆:“余尝观荆浩论山水而悟诗家三昧⒇。其言曰: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按魏尔兰谓(21):“佳诗贴切而不粘着,如水墨晕。”即此旨也。《沧浪诗话》曰:“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按《宾退录》卷二载张芸叟(22)“评本朝名公诗”:“王介甫如空中之音(23),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困学纪闻》卷十八纪栾城论文(24),“以不带声色为妙”。言有尽而意无穷,一唱三叹之音。”《诗镜》曰(25):“诗被于乐,声之也。声微而韵悠然长逝者,声之所不得留也。凡情不奇而自法,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食肉者不贵味而贵臭(26),闻乐者不闻响而闻音。”与前所引法德两国诗流论诗妙入乐不可言传云云(27),更如符节之能合。魏尔兰比诗境于“蝉翼纱幕之后,明眸流睇”,言其似隐如显,望之宛在,即之忽稀,正沧浪所谓“不可凑泊”也。(275—276页)
①《傅与砺诗集》:元傅若金(字与砺)撰,二十卷。揭傒斯:元代作家,字曼硕。
②刘会孟:宋刘辰翁字。
③《须溪集》:宋刘辰翁撰,十卷。
④《揭文安集》:揭傒斯撰,十四卷。
⑤《沧浪诗话•诗辨》:宋严羽撰,一卷。分诗辩、诗体等五节论述。
⑥僧肇:音代名僧,撰有《释宝藏论》一卷,亦称《肇论》。《离微体静品》是其中一节。
⑦唐译《华严经》: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卷。
⑧唐译《圆觉经》:唐佛陀多罗译,一卷。
⑨《五灯会元》:宋释普济撰,二十卷。
⑩《僧宝传》:宋释惠洪撰,三十二卷。总括五宗,传八十一人。
⑾胡元瑞:明代作家胡应麟字。有《诗薮》内、外、杂、续四编。
⑿《埤雅》:宋代作家陆佃(字师农)撰,二十卷。
⒀《苕溪渔隐丛话》:宋胡仔(自号苕溪渔隐)撰,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诗评》:宋代作家张舜民(字芸叟)撰。
⒁王介甫:宋代作家王安石字。
⒂《师友诗传续录》:清刘大勤问,王士禛答,一卷。
⒃严仪卿:宋严羽字。
⒄内典:佛之教典。
⒅曹酒:唐良价禅师,一称洞山。
⒆《香祖笔记》:清王士禛撰,十二卷。
⒇荆浩:后梁山水画家,字浩然,自号洪谷子,撰有《山水诀》。三昧:犹奥妙。
(21)魏尔兰:十九世纪法国诗人。
(22)《宾退录》:宋赵与时撰,十卷。张芸叟:宋张舜民字。
(23)王介甫:宋王安石字。
(24)《困学纪闻》:宋王应麟撰,二十卷。栾城:宋苏辙,撰有《栾城集》五十卷等。
(25)《诗镜》:即《诗镜总论》一卷,明陆时雍撰。
(26)臭(xiù秀):气味。
(27)法德两国诗流:指法国诗人魏尔兰、马拉梅、瓦勒里与德国浪漫派诗人瓦根洛特、蒂克、诺瓦利斯等,议论相近,认为诗不必言之有物,如乐无意,又如乐含意。
这里第一则从宋代诗人刘辰翁《须溪集》漏收两篇文章的片言只语谈起,论述了诗歌艺术的风格,贵在神韵的道理。
刘辰翁在为揭傒斯兄诗集序中说:“诗欲离欲近,如水中月,如镜中花”;在《陈简斋诗集序》中说:“诗道如花,论高品则色不如香,论逼真香不如色”,确是见解非凡。与他大约同时期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讲到诗的神韵,也有水中月,镜中象,“透澈玲珑,不可凑泊”的说法,讲到诗之品,也有深远飘逸,如空中音,相中色的说法,看法完全一致。“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八个字,就是“欲离欲近”的意思,也就是佛典上所说的“不即不离”,僧肇所说的“不与影合,亦不与体离”,“非离非合”,如同水中看月,镜中看花,可望而不可即,透激有余而终不可得。水如明镜,月映其中,月影与月既不能相合,也不能相离。可见他们都是以禅喻诗,解释诗的艺术性贵在形象思维,贵在神韵。
刘、严论诗的见解很高,因为他们悟到了艺术的真谛。姑且举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来说明: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诗里含有一夜不睡的意思,从“夜来风雨声”里透露出来。这里又含有破晓时入睡的意思,所以称“不觉晓”,这跟“处处闻啼鸟”有关,因“闻啼鸟”知天已放晴,所以安然入睡。从不睡到入睡,正透露出诗人对花事的关心。这些心情的变化,都不加点明,是用形象思维的写法。
刘辰翁又以花喻诗,花好在香不在色,譬如梅花,只要远远闻到她淡雅的香气,便可以想到高雅之美,无须看到她的形象。好诗也一样,神韵和情趣好比花香,不在乎写了什么或用什么形式。再譬如桃花的美则在色不在香,必得亲眼看到她的艳丽时,才会觉得她美,比起梅花自然不如,在诗也是略逊一筹的。张舜民解释空中音,相中色的妙处是“人皆闻见,难有着摸”,而“香”更是飘渺无迹,看不见,捉不到,留不住,迁不去的气味,用“香”来喻诗的神韵,实在恰切。西方诗人曾称香味是花的灵魂,那么,也可以说神韵是诗的灵魂了。
第二则引严羽说:“语忌直”,王士禛讲曹洞禅师所谓的“参活句”,都是针对诗文艺术手法和风格说的。王士禛在《香祖笔记》里总结出诗家的秘诀,即:“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因为“目”“波”“皴”需在近处方能看见,这是生活常识,电影中特写镜头的处理是写近景,“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是是写远景。魏尔兰说的“贴切而不粘着”,似不如严羽说的更为形象,“透澈玲珑”就是“贴切”,“不可凑泊”就是“不粘着”,如空中音、相中色、水中月、镜中象,就是“贴切面不粘着”。这也说明似隐如显、朦胧模糊的含蓄境界,如纱幕后的明眸流睇,有着无穷的吸引力。陆时雍说诗重在音节,与德国的蒂克主张诗以声调写心言志,十分吻合。诺瓦利斯也说作诗“仅有声音之谐,文字之丽”,“诗之高境亦如音乐,浑含大意,婉转而不直捷”。可见,中外谈艺者无论用什么比喻说诗,意思大致是共同的,即:诗应有含蓄的风格,要达到一种“似隐如显,望之宛在,即之忽稀”的境界。
(六)诗有别才别趣
自“同光体”起①,诸老先倡“学人之诗”。良以宋人诗好钩新摘异,炫博矜奇,故沧浪当日,深非苏黄,即曰:“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以才学为诗。其作多务使事,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唐人之风变矣”云云。东坡谓孟襄阳诗“少作料”,施愚山《蠖斋诗话》至发“眼中金屑”之叹;而清初时浙派宋诗亦遭“饾饤”之讥②。加之此体巨子,多以诗人而劬学博闻,挥毫落纸,结习难除,亦固其然。然与其言“学人”之诗,来獭祭兔园、抄书作诗之诮,不如言诗人之学,即《沧浪诗话》“别才非学而必读书以极其至”之意,亦即《田间诗说》所云“诗有别学”是也③。沧浪之说,周匝无病。朱竹垞《斋中读书》五古第十一首妄肆诋諆④,盖“贪多”人习气。李审言丈读书素留心小处,乃竟为竹垞推波张焰,作诗曰:“心折长芦吾已久,别才非学最难凭⑤”。本事见《石遗室诗话》卷十七。陈石遗丈初作《罗瘿庵诗叙》⑥,亦沿竹垞之讹;及《石遗室文》四集为审言诗作叙,始谓:沧浪未误,“不关学言其始事,多读书言其终事,略如子美读破万卷、下笔有神也”云云。余按“下笔有神”,在“读破万卷”之后,则“多读书”之非“终事”,的然可知。读书以极其至,一事也;以读书为其极至,又一事也。二者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沧浪主别才,而以学充之;石遗主博学,而以才驭之,虽回护沧浪,已大失沧浪之真矣。沧浪不废学,先贤多已言之,亦非自石遗始。宋小茗:《耐冷谭》卷八曰⑦:“少陵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千古学诗者之极则。《沧浪诗话》云:‘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持论本极周密。自解缙《春雨杂述》截取沧浪首四句⑧,以为学诗者不必读书,诗道於是乎衰矣。仆昔有:‘沧浪漫说非关学,谁破人间万卷书’之语,亦由少年无学,循习流俗人之说,使沧浪千古抱冤。”钱星湖《衎石斋纪事续稿》卷五《颐采堂诗序》曰⑨:“自严沧浪论诗曰妙悟,曰入神,后人不喻,辄曰何必博闻。此竹垞之所深斥也。顾吾观严氏之说,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是虽严氏亦何能废书哉。”陈恭甫《左海文集》⑩卷六《萨檀河白华楼诗抄叙》曰:“严沧浪云:‘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卓哉是言乎。犛牛不可以执鼠,干将不可以补履;郑刀宋斤、迁乎地而勿良,櫨梨桔柚、相反而皆可于口。此别才之说也。五沃之土无败岁,九成之台无枉木;饮于江海,杯勺皆波涛;采于山薮,寻尺皆松枞。此多读书之说也。解牛者目无全牛,画马者胸有全马,造弓者择干于太山之阿,学琴者之蓬莱山,此多穷理之说也。世徒执别才一语,为沧浪诟病,亦过矣。”谢枚如《赌棋山庄余集》卷三引《屏麓草堂诗话》载何歧海说⑾,谓:“近世瞀儒摘别才不关书一语⑿,以资掊击。”余考锺嵘《诗品》曰:“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即沧浪别才不关书之说也。杜工部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文忠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又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即沧浪非多读书不能极其至之说也。瞀儒所执以诋沧浪,为皆沧浪所已言,可谓悖者之悖,以不悖为悖者矣。”张亨甫《文集》卷三⒀:《答朱秦洲书》略谓:“沧浪言别才别趣,亦言读书穷理,二者济美,本无偏颇。后人执此失彼,既昧沧浪之旨,复坏诗教之防。欲救今日为诗之弊,莫善于沧浪”云云。亨甫所谓“今日诗弊”,乃指南袁、北翁而言⒁。参观《文集》卷四《刘孟涂诗稿韦后》。一时作者,不为随园、瓯北之佻滑⒂,则为覃溪、竹君之考订⒃;卷三《与徐廉峰太史书》。譬如不归杨则归墨⒄,故欲以沧浪为对症之药。窃谓凡诗之空而以为灵,塞而以为厚者,皆须三复沧浪《诗辨》;渔洋未能尽沧浪之理,冯班《钝吟杂录•纠缪》一卷亦只能正沧浪考证之谬。(207—209页)
《沧浪诗话》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至”,又谓:“学诗者以识为主。”按《随园诗话》卷三曰:“方子云云:‘学荒翻得性灵诗’,刘霞裳云:‘读书久觉诗思涩’。非真读书能诗者不能道。”参观卷六王梦楼云条。又曰:“作史三长才学识,诗亦如之,而识为最先。非识则才学俱误,北朝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而知真师之所在。’识之谓欤。”卷四曰:“陶篁村谓作诗须视天分,非关学习。磨铁可以成针,磨砖不可以成针。”卷五曰:“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或骈文,何必借诗卖弄。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六曰:“司空表圣论诗⒅,贵得味外味。余谓今之作诗者,味内味尚不能得,况味外味乎。”《补遗》卷一引李玉洲曰:“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欲其助我神气。其隶事与否,作者不自知,读者亦不知,方谓之真诗。”与沧浪宗旨,有何不同。盖性之灵言其体,悟之妙言其用,二者本一气相通。悟妙必根于性灵,而性灵所发,不必尽为妙悟;妙悟者,性灵之发而中节,穷以见几,异于狂花客慧、浮光掠影。此沧浪之说,所以更为造微。子才引司空表圣,尤机锋泄漏,表圣固沧浪议论之先河;《与李生论诗书》所谓:“味在酸咸之外,远而不尽,韵外之致”,即沧浪之神韵耳。子才所引徐遵明指心事,出《魏书•儒林传》,酷肖禅宗不立阶梯、直指心源之说。《补遗》卷三《诗佛歌》亦云:“一心之外无他师。”彼法常言:迷心徇文,如执指为月。《观心论》中云:“伤念一家门徒,不染内法,著外文字。偷记注而奔走,负经论而浪行。”《宗镜录》卷九十二引。有檀越问安国⒆:“和尚是南宗北宗”,答云:“我非南宗北宗,心为宗”;又问:“和尚曾看教否”,答云:“我不曾看教。若识心,一切教看竟。”《宗镜录》卷九十八引,参观卷九十四引证。与子才说诗,若合符节矣。(200—201页)
①同光体:清同治光绪时期的诗歌流派,以陈三立、陈衍、沈曾植为代表,不专宗盛唐,以“江西诗派”为榜样,又称“宋诗派”,在诗坛上与“南社”相抗衡。
②浙派宋诗:清初吴之振与吕留良、黄宗羲等编刊《宋诗抄》一百六卷,即为浙派宋诗。
③《田间诗说》:清钱澄之(字幼光,自称田间老人)撰。
④朱竹垞:清代文学家朱彝尊号。有《曝书亭集》八十卷。
⑤李审言:近人李详字。丈:敬称。长芦:朱彝尊晚号小长芦钓鱼师。
⑥陈石遗:近人陈衍号。撰有《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石遗室文》十二卷。
⑦宋小茗:清宋咸熙字。撰有《耐冷谭》十六卷。
⑧解缙:明代作家,字大绅。有《春雨杂述》一卷。
⑨钱星湖:清钱仪吉,字蔼人,号衎石。撰有《衎石斋纪事稿》十卷,《续稿》十卷。
⑩陈恭甫:清代作家陈寿祺字。撰有《左海文集》十卷,乙集二卷。
⑾谢枚如:清谢章铤字。撰有《赌棋山庄余集》十四卷。
⑿瞀儒:指愚蒙文人,愚夫子。
⒀张亨甫:清张际亮字。撰有《张亨甫文集》六卷。
⒁南袁北翁:指袁枚、翁方纲。
⒂瓯北:清代诗论家赵翼号。佻滑:轻薄不实。
⒃覃溪、竹君:指翁方纲、朱筠。
⒄不归杨则归墨:指杨朱、墨翟。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哲学主张相反。
⒅司空表圣:唐代诗论家司空图字。
⒆檀越:梵语,施主之义。安国:即齐安国师,嗣法于马祖。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一部系统的以禅喻诗,偏重于论诗的艺术性的专门著作,对宋诗的弊病和诗坛上的宗派模拟,“好钩新摘异,炫博矜奇”,提出严厉的驳难。因此,自它问世以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若干问题的认识也引起了不少争论。
这里两则是专就才、学、识方面的问题,作出公正的评价,并指出袁枚的《随园诗话》与严羽的《沧浪诗话》、司空图的《诗品》一脉相承的关系。
一、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诗者以识为主”,“识”在这里是指对诗应具有的一种审美、品味、辨别高下的能力,也就是严羽说的对于入门“路头”的判断力,因此,他将“识”看得头等重要。他又说:“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讲的是“才”与“学”的问题,基本精神是重别才而不废学。钱先生认为:与其言“学人之诗”,遭抄书作诗之讥,不如言诗人之学,也就是严羽所谓别才非学,但必须读书极其至,亦即钱澄之所谓“诗有别学”。然而严羽的不废书,以读书达到最高境界的主张,却历遭非难,明黄道周指别才非学为“欺诳天下后生”的瞎说(《漳浦集》卷二十三《书双荷庵诗后》),明遗民周容以反问为责难说:“盛唐诸大家,有一字不本于学者否?”并诬严说为“流弊”(《春酒堂诗话》)。清朱彝尊指桑骂槐,诋毁说:“坐坛坫诗,不知自量”(《静志居诗话》卷十八),其实他仅注意严羽的别才非书,未注意下文,竟指严羽“不晓事”;汪师韩反击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诗学纂闻》);近人李详亦为朱彝尊之诬推波助澜,说别才非学靠不住,陈衍开始沿袭朱彝尊的错误,后为李详诗作序时,才说严羽的“非关书”,是指开始作诗时,因此不误。清人徐经《雅歌堂甃坪诗话》卷二有赞同严羽别才非学的话:“诗学自有一副才调,具于性灵”,“古人未尝不力学,而诗则工拙各异”,是因“才自有别,非一倚于学所能得”;张宗泰《书瓯北集后》(《鲁岩所学集》),亦支持严羽别才非书的立论,他从古今文人学士中有鸿才硕学、博通坟典者,于吟咏无一字留传的事实,证明诗乃别才非书;宋咸熙诗话《耐冷谭》亦称严羽“持论本极周密”,他指责明人解缙截取严羽《诗话》首四句,断章取义,以为学诗者不必读书,影响很坏,甚至“诗道于是乎衰矣”,他开始也是非难严羽的,及至学富之后改变了看法。钱仪吉在《颐彩堂诗序》里也肯定严氏论诗曰妙悟,曰入神,并未有废书之说。陈寿祺《萨檀河白华楼诗钞叙》亦称严氏别才非书、读书穷理“能极其至”之说“卓哉”,他还用了一系列比喻说明诗乃别才之说,认为诗抒性情与读书穷理是两种功夫,而多读书,就像饮于江海的人,可于杯勺中想见波涛;宰牛者一点一点动刀,画马者须胸有全马的构想,对此若不“穷理”,便难以成功。张际亮《答朱秦洲书》亦称严氏别才别趣,归之于读书穷理,是“二者兼美,本无偏颇”,并以为可救清诗之弊。这里认为凡诗之少料而以为灵,或诗之多料而以为厚者,皆须反复读三遍《沧浪诗话•诗辨》,至于冯班的《钝吟杂录•纠缪》,仅是纠正其《考证》的部分错误。这里还指出,陈衍说“多读书言其终事”不确,因杜甫读破万卷之后,方下笔有神,可见“多读书”非“终事”,严氏主张别才,以学补充;陈衍主张博学,以才驾驭,所以同是主张读书,意义却大不同。
二、钱先生举引若干例证,说明袁枚《随园诗话》论诗以妙悟为主,论文章以神韵为归,与严羽《沧浪诗话》、司空图《诗品》的立论暗暗相合,有着一种承继的关系。如:严氏别才别趣、非书非理、读书穷理之说,在《随园诗话》中能找到很好的解释,其卷三引方子云和刘霞裳的诗句,“学荒翻得性灵诗”和“读书久觉诗思涩”,是读书、作诗的经验之谈,因为读书和吟咏是运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读书要求记忆、理解、融会贯通,无论运用归纳或演绎,皆属逻辑思维,而吟咏则是抒发情怀或描景状物,纯属形象思维,所以袁氏说“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与严氏主张暗合。同卷中袁氏又说:“作史三长才学识,诗亦如之,而以识为最先”,这与严氏入门“路头”之说完全一致。《诗话》卷四引陶元藻的话是肯定“作诗须视天分”的说法,认为“与诗近者,虽中年后,可以名家;与诗远者,虽童而习之,无益也”,并用磨铁成针,磨砖不成针,比喻别才,显然,袁氏同意陶氏意见,又与严氏别才说相合。《诗话》卷六有一则引司空图论诗,透露了他们的相通之处:司空图论诗贵味外味,袁氏甚为赞赏,他以为今之作诗者味内味尚未得到,只好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为此他深感遗憾。他的《诗话补遗》卷一引李玉洲言,表明他赞同“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因为“必须胸有万卷者”,才能助神气,“若有心矜炫淹博,便落下乘”,这与严氏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多务使事,不问兴致”,以及用字押韵必有依据等,有碍表达性情的宗旨亦甚相合。谢章铤《赌棋山庄余集》引何歧海说:袁氏别才不关书之说,亦即锤嵘《诗品》所谓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之说,也就是严羽的别才不关书之说。这里通过若干具体见解的比较,捋顺了前后几部诗话的关系:“子才引司空表圣,尤机锋浅漏,表圣固沧浪议论之先河”,袁氏提倡神韵,亦即司空《与李生论诗书》所谓“韵外之致”。袁氏不好禅,甚至一再反对严氏借禅喻诗,或禅语之说,这里举引《诗话补遗》卷三的《诗佛歌》竟与《宗镜录》所引之《观力论》相同,说明袁氏亦在以禅说诗,他不明白禅具有一种哲理,而他在讲道理时虽非禅,亦合于禅。这一点很少有人道及。
(七)以禅喻诗
严沧浪《诗辨》曰:“诗有别才非书,别学非理,而非多读书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曰“别才”,则宿世渐熏而今生顿见之解悟也;曰“读书穷理以极其至”,则因悟而修,以修承悟也。可见诗中“解悟”,已不能舍思学而不顾;至于“证悟”,正自思学中来,下学以臻上达,超思与学,而不能捐思废学。犹夫欲越深涧,非足踏实地,得所凭借,不能跃至彼岸;顾若步步而行,趾不离地,及岸尽裹足,惟有盈盈隔水,脉脉相望而已。Kierkegaard以跳越为人生经验中要事①。沧浪继言:“诗之有神韵者,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澈玲珑,不可凑泊②。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云云,几同无字天书。以诗拟禅,意过于通,宜招钝吟之纠缪③,起渔洋之误解④。禅宗于文字,以胶盆粘着为大忌;法执理障,则药语尽成病语,故谷隐禅师云⑤:“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见《五灯会元》卷十二。此庄子“得意忘言”之说也。若诗自是文字之妙,非言无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镜花,固可见而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能映影。王弼《周易略例》⑥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炎《读易笔记•自序》驳之曰⑦:“是未得鱼兔,先弃筌蹄之说也。”诗中神韵之异于禅机在此;去理路言诠,固无以寄神韵也。沧浪又曰:“言有尽而意无穷”;夫神韵不尽理路言诠,与神韵无须理路言诠,二语迥殊,不可混为一谈。《钝吟杂录》卷五驳沧浪云⑧:“诗者言也,但言微不与常同,理玄或在文外。安得不涉理路,不落言诠。”又云:“禅家死句活句与诗法并不相涉。禅家当机煞活,若刻舟求剑,死在句下,便是死。诗有活句,隐秀之词也;直叙事理,或有词无意,死句也。禅须参悟;若‘高台多悲风’、‘出入君怀袖’,参之何益。沧浪不知参禅”云云。按前段驳沧浪是也,后段议论便是刻舟求剑、死在句下,钝吟亦是钝根⑨。禅句无所谓“死活”,在学人之善参与否。譬如《参同契》云⑩:“执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此石头扫空事障理障之妙谛。而达观未离窠臼⑾,不肯放下,活语变死,药语成病,宜来谷隐之呵矣。(99—100页)
古人说诗,有曰:“不以词害意”而须“以意逆志”者,有曰:“诗无达诂”者,有曰:“文外独绝”者,有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者。不脱而亦不粘,与禅家之参活句,何尝无相类处。参而悟入,则古人说诗又有曰:“其源出于某”者,有曰:“精熟《文选》理”者,有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者,有曰:“得句法于某”者,有曰“脱胎换骨”者⑿。钝吟真固哉高叟矣。其乡后学王东溆《柳南续笔》卷三引钱圆沙语⒀:“诗文之作,未有不以学始之,以悟终之者”;以为可补沧浪之说,钝吟并妙悟而诋之过矣云云。实则沧浪之意本如是,初不须补也。胡元瑞《诗薮》内编卷二谓⒁:“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亦属强生分别。禅与诗、所也,悟、能也。用心所在虽二,而心之作用则一。了悟以后,禅可不着言说,诗必托诸文字;然其为悟境,初无不同。且悟即“造”之至“深”;如须“深造”,尚非真悟。宜曰:禅家讲关捩子⒂,故一悟尽悟,快人一言,快马一鞭。《传灯录》卷六载道明语⒃。一指头禅可以终身受用不尽。见《传灯录》卷十一。诗家有篇什,故于理会法则以外,触景生情,即事漫兴,有所作必随时有所感,发大判断外,尚须有小结裹。顾大慧杲老大悟至一十八遍⒄,小悟不计其数,则禅家亦未尝如元瑞所谓“一悟便了”也。(101页)
沧浪《答吴景仙书》自负:“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夫“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尚属泛言;诗“入神”境而文外独绝,禅彻悟境而思议俱断,两者触类取譬,斯乃“亲切”矣。沧浪“不涉理路,不落言诠者,上也”,犹《五灯会元》卷十二谷隐曰:“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即瓦勒利论文所谓⒅:“以文字试造文字不传之境界。”然诗之神境,“不尽于言”而亦“不外于言”,禅之悟境,“语言道断”,斯其异也(参观第100页《补订》一)。当世西方谈士有径比马拉美及时流篇什于禅家“公案”⒆或“文字瑜伽”者;有称里尔克晚作与禅宗方法宗旨可相拍合者⒇;有谓法国新结构主义文评巨子潜合佛说(21),知文字之为空相(22),“破指事状物之轮回”,得“大解脱”者。余四十年前,仅窥象征派冥契沧浪之说诗(23),孰意彼土比来竟进而冥契沧浪之以禅通诗哉。撰《谈艺录》时,上庠师宿(24),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25),不复如李光昭之自诩“一拳打蹶”矣(26)。兹赘西方晚近“诗禅”三例,窃比瀛谈,聊舒井观耳。(595—596页)
①Kierkegaard:十九世纪中叶丹麦唯心主义哲学家、作家克尔恺郭尔。
②不可凑泊:犹不可瞎凑、胡弄应付之意。
③指清代冯班(号钝吟)所撰之《严氏纠缪》一卷。
④指清代王士禛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将意在言外看作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之音看作弦上无音;将有话不说看作无话可说。
⑤谷隐:青原七世,襄州智静悟空大师。
⑥《周易略例》:三国魏经学家王弼撰,一卷。
⑦《读易笔记》:宋王炎撰,是其《双溪类稿》中的一种。
⑧《钝吟杂录》:清冯班撰,十卷。
⑨钝根:指本性迟钝。
⑩《参同契》:此指唐衡山石头山和尚希迁撰者,主要是在发明禅理。希迁称石头和尚,省称石头。
⑾达观:明僧可真字,世号紫柏大师。
⑿“其源出于某”:见梁锺嵘《诗品》讲各家诗,其源出于某家。
“精熟《文选》”:见杜甫《宗武生日》诗。“读书破万卷”:见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脱胎换骨”:不易其意而选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见释惠洪《冷斋夜话》。
⒀王东淑:清王应奎号。撰有《柳南随笔》六卷,续笔四卷。钱圆沙:清钱陆灿号。
⒁胡元瑞:明胡应麟字。撰有《诗薮》内编六卷,外编六卷,续编二卷,杂编六卷。
⒂关捩子:物的紧要处。
⒃《传灯录》:宋景德元年,吴沙门原道备录释迦以来之法语,三十卷。
⒄大慧杲:宋杭州经山之佛日禅师,名宗杲。大悟:指能破一切迷妄而开真知的廓然之悟。
⒅瓦勒里:现代法国诗人。
⒆马拉梅:十九世纪法国诗人。文字瑜珈:通过文字使口与意符,意与身合,三者相交的佛教语。
⒇里尔克:十九、二十世纪德国诗人。
(21)法国新结构主义: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种分析文化现象的方式,这种方式起源于费•德•索绪尔分析语言的各种方法,以为文化也像语言一样有结构,目的在于揭示相似性。
(22)空相:佛家语。指直空的体相。
(23)象征派:近世西方文艺的一个流派,注重情调象征化的表现,有时流于晦涩难解,犹如严羽的以禅论诗。
(24)庠:学校。
(25)严仪卿:宋严羽字。
(26)李光昭:清人,有《铁树堂诗抄》三卷。
这里是从解悟、证悟、诗悟、禅悟讲起,以帮助对《沧浪诗话》的认识和理解。首先须明白什么是悟。悟,就是觉,觉悟的意思,是对迷而言。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里关于悟有个绝妙的比喻,他说:“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然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故悟亦必继之以躬行力学。”(卷三)《谈艺录•妙悟与参禅》中更进而讲到“悟有迟速,系乎根之利钝、境之顺逆,犹夫得火有难易,系乎火具之良楛(kǔ苦)、风气之燥湿。速悟待思学为之后,迟悟更赖思学为之先。”比喻同样绝妙,亦深入浅出,清楚明白。所谓速悟、迟悟,似亦如禅家所谓顿悟、渐悟。
一、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所说诗有别才非书、别趣非理,多读穷理,以极其至,是以禅喻诗。这里认为其“别才”是“宿世渐熏而今生顿见之解悟”,宿世,是佛家语,指前世;渐熏,犹言天才遗传。这里说的“别才”是指天生具有的才能,比方有人具有天生的好桑子,这个好桑子是从遗传得来的,这就是宿世渐熏而今生顿见。“读书穷理,以极其至”,是经过后天的学习锻炼来达到极高的境界。这两者可以结合,有了好嗓子还要学习唱歌,可见诗的“解悟”,离不开悟后的修行,也就是多读书的磨练。证悟则是“因修而悟”,是先经过不断读书和思考的磨练,由浅入深,从自身的思学中来。这里用了一个欲跨深涧,必得跳跃的比喻,如果足不踏实地,步步而行,便不能跃至彼岸。丹麦作家克尔恺郭尔亦将跳跃看作是“人生经验中要事”。这是指质的飞跃。
二、严羽又说:诗有神韵,如水月镜象,“透澈玲珑,不可凑泊”,“不涉理路,不落言诠”。又是以禅喻诗。他认为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即不借助才学和议论,这实际上就是形象思维。诗不靠学术和议论得来,靠的是形象思维,所谓似隐如显,如水月镜象,朦胧可见,不可凑泊;禅理中有诗悟,即不即不离,如水月不能离月,水又不等同于月,恍惚迷离,无迹可求。这番以诗喻禅的道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诗用形象思维,通过形象反映生活,形象与生活之间应当有一个距离,它既离不开生活,又不等同于生活。所以说严羽是以禅喻诗。
三、严羽又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认为这是诗有神韵的一种高境界,即是通过形象来表达情思,不是靠议论可以达到,因此不必涉理路,只要把握言不说尽,意在言外的写作方法,使其朦胧含蓄,便自具神韵。冯班在其《杂录》卷五的《严氏纠缪》中,从儒家主张诗言志的立场出发,批驳严氏以禅喻诗或以诗喻禅的故弄玄虚,而强调诗是语言艺术,不能不涉理路,就是不懂诗可以通过形象来表达思理。至于冯氏所谓“禅家死句活句”云云,这里认为禅句无所谓“死活”,而在于是否善于参禅,是否了悟。对于诗来说,自古以来大诗人的“入神”之作不少,但后人若死死去模仿,“生吞活剥”或是“句剽字窃”,便是刻舟求剑,死在句下,所以作诗需不落案臼,意从心出,把握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方法,即通过形象来表达情思,方可具有神韵,达到最高境界。
四、清人钱陆灿说:诗以学始,诗以悟终,以为是补严说,实则与严羽所谓别才非书、别趣非理是一致的。胡应麟以为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是将禅与诗区分过清,实则禅与诗用心所在虽有不同,但求悟是相同的,均须了悟,不悟不进。而了悟之后,禅与诗不同了,禅不必写为文字,诗则必得以文字表达了悟到的东西,将随时的感发写出来,所以说禅与诗在悟境阶段是相同的,释家道明认为禅在了悟之后,如果尚须深造者,即不是真悟,因为禅家最紧要的就是悟,一悟尽悟,受用终生,胡应麟与道明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宗杲禅师至老有大悟十八次,小悟不计其数,可见也不是一悟尽悟。所以说不论是解悟、证悟、禅悟、诗悟、了悟都不是止境,都不是与书与学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