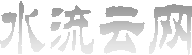(五)柏梁体
堆垛物名,仿“柏梁体”之句①,唐宋以下,作者偶为之,不复覙缕②。所见莫如诸襄七锦《绛跗阁诗集》之乐此不疲者③,兹举五七言古近体各一例。卷一《述怀》第三首:“蓑笠铚耨俯④,弓庐陶旖段。砗磲玛瑙珠⑤,鱼菽盐豉蒜”;卷八《又赋玉瓮诗》:“卣壘敦*鬳匜鬲,觚隸角洗槃盂彝”⑥;《七虫篇》:“鼃黾蛾螳鼠雀蝉⑦,飞鸣跳伏阶庭前”;卷十《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经》:“沈贺钱陈董,虞洪宋李韩。隶真行狎草,长短瘠肥宽⑧”。先于徐文靖所为者⑨,南宋郑青山清之《安晚堂诗集》⑩卷七《病后再和前韵》第二首:“事业镂冰何所有,之乎者也已焉哉。”《随园诗话》卷四载张璨《戏题》⑾:“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张南山《花地集》⑿卷二《曾朴园》:“烟霞泉石风花月,柴米油盐茶醋糖”;《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四引郭臣尧《捧腹集•村学诗》⒀:“赵钱孙李周吴郑⒁,天地玄黄宇宙洪”⒂;又柏梁体之打诨也⒃。(523—524页)《明诗综》⒄卷八范嵩《过太平府有感》:“昨夜月明乡梦醒,杜鹃啼上杜鹃花。”
清人唯金和能于叙事长篇中着堆垛物名句,爽利贯注,不滞不佻,远非诸锦、张维屏所能及。《秋蟪吟馆诗钞》卷二《原盗》之八⒅:“井灶庖廥厕,楣槛屏柱墙;一一搰之烂⒆,惟恐屋不伤。盆钵鼎豆壶,几匮橱椸床⒇;一一撞之碎,惟恐物不牫”;又《六月初二日纪事》:“先期大飨聊止啼,军帖火急一卷批;牛羊猪鱼鹅鸭鸡,茄瓠葱韭菰菔藜,桃杏栌芍菱藕梨,酒盐粉饵油酱醯(21)。”运用柏梁体可谓能手矣。(《谈艺录》增订本补正,《钱锺书研究》22页)
①柏梁体:七言古体联句。相传汉武帝筑柏梁台宴群臣时的七言联句,句句押平声韵,称柏梁体。
②覙缕:细述。
③诸襄七:清诸锦字,有《绛跗阁诗集》十一卷。
④铚(zhì至):大镰刀。耨(nòu):除草的农具。俯(tiāo祧):古量器。
⑤旖(fǎng访):捏土为瓦器。段:锥击成物。砗磲:同车渠,海中软体动物的贝壳。
⑥卣(yǒu友):古代中型酒器。壘(léi雷):古盛酒器。敦(duì对):盛黍稷器。*(fǔ斧):礼器,盛稻梁用。鬳(yán言):古炊器,分两层。匜(yí移):洗手盛水器。鬲(lì力):炊具,一层。觚(gū姑):古酒器。隸(hé河):温酒器。彝:青铜祭器。
⑦鼃,同蛙。黾(měng猛):金线蛙。
⑧《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经》:杭州六和塔上刻有宋刊《四十二章经》,这经是沈、贺、钱、陈、董、虞、洪、宋、李、韩十个人写的,他们用了隶、真、行、狎、草五种书法来写,有长、短、瘠、瘦、宽多种形体。
⑨徐文靖:清学者,字位山。工于考证古体。
⑩郑清之:原名郑燮。有《安晚堂诗集》六十卷。
⑾《随园诗话》:清袁枚撰,十六卷,补遗十卷。
⑿张南山:清张维屏字。
⒀《两般秋雨庵随笔》:清梁绍壬撰,八卷。
⒁《百家姓》读本的首句。
⒂《千字文》读本的首句。
⒃打诨:以诙谐的语言相戏谑。
⒄《明诗综》:清朱彝尊编,一百卷。
⒅《秋蟪吟馆诗钞》:清金和撰,六卷。此处所引《原盗》句,《清诗纪事》题作《痛定篇十三曰》。
⒆廥(kuài侩):藏刍稿处。搰:掘穿。
⒇豆:高脚盘。椸(yí移):床前小几。
(21)菰:茭白。菔:即莱菔。俗称萝卜。藜:一种野菜。栌:栌橘。醯:醋。
提到柏梁台诗,最早的是《东方朔别传》、《汉武帝集》,稍晚的是《艺文类聚》、《古文苑》。清人顾炎武认为是伪作,游国恩据颜延之《庭诰》云“挚虞文论,足称优洽,《柏梁》以来,继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进而考证这首托于古人以文为戏之作,似乎在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里已经录入,则其作不能早于魏晋。而魏晋时代尚清谈,一些士大夫遇事互相调笑时,有用联句语、联句诗、联句赋者,如《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谢太傅寒雪日集儿女讲论文义事,雪下大了,公曰:“大雪纷纷何所似”,兄子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便可以看作是韵同义贯的咏雪联句诗。
相传的柏梁台诗,首句是“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接着是“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各述各自职位需要说的意思,“皇帝曰”“梁王曰”的内容都与他们的身份相称。又如“丞相曰:总领天下诚难哉。大司农曰:陈粟万石扬以箕”等等,亦复如是。全篇共二十六句,都用某某曰以下七字句的形式,句末皆谐声用韵,形成联句体的格式,同时带有游戏谐谑的意味,人称这种诗体为“柏梁体”。发展到后来,仿此体堆垛物名,也不限于七言联句,更极尽俳谐之能事。
这里讲唐宋以后的作者很少有人再写这类诗作,但清代的诸锦喜用此体,举了他的四首作品,使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柏梁体”的特点及其流变。《述怀》每句五字,连用二十字,从日常用品到贵重物品,从海产到调味品,内容全不搭界,却包括了生活的全部,读起来句句有韵,无一虚字,仿佛是在游戏。《七虫篇》写七种小虫,有飞的,有叫的,有爬的,有跳的,聚在门前,好不热闹,这可能是天气变化前后的某种景象,除“前”字外,一句全是名词:“鼃黾蛾螳鼠省蝉”;一句四个动词:“飞鸣跳伏”,两个名词“阶庭”,堆垛成诗,还颇有味道。清经史学家徐文靖是讲求实学的人,也尝有柏梁体戏作。南宋的郑清之,在《病后再和前韵》中,一连堆垛七个虚字,再生动不过地反映了他病后对毕生事业无限感慨、痛苦无奈的心情,真是“之乎者也已焉哉”,一言难尽。张璨的《戏题》,也是自己生活的写照。头两句写他家境尚好时的生活:“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自在潇洒,后来他的父亲跛了,家道败落,需要他日日亲自侍奉,生活起了变化,一天七件事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前后两样的生活内容,都是实实在在的实物名词堆垛于诗中。清梁绍壬所引的郭臣尧的《村学诗》,虽不能令人捧腹大笑,但也把村学读书的内容,默写出来了。
清金和很善于写长篇叙事诗,其中也有堆垛物名的诗句,向不为人注意,《清诗纪事》所引到的若干诗评中,也未有道及这个特点的,钱先生指了出来。《原盗》是一首百六七十韵的长诗,这里引出堆垛的二十个字的器物名称,囊括了家中的动产和不动产,在强人手下,统统“搰之烂”,“撞之碎”,把太平天国军队进攻时的猛烈形象,勾勒得维妙维肖。《六月初二日记事》,堆垛了二十八个物名,这是太平天国军的一张军贴征用的物名,其中没有山珍海味,都是平常的荤素菜蔬和果品调料,也只有当他们造了统治阶级的反之后才能得到。一首长诗中连用四句品物的堆垛,既烘托出当时十万火急的气氛,又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
读过钱先生举引的柏梁体诗,与最初此类诗作比较,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形式上仍保持句句押韵,表面上也保持了游戏取乐的特色,实际内容则有了很大拓展,它既能表达诗人的情感,又能反映现实生活,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六)章咒气与偶颂气
纪晓岚《点论李义山诗集》①卷下评《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云:“终恨有章咒气”②;《点论苏文忠诗集》卷四评《读道藏》云:“作僧家诗③,不可有偈颂气④;作道家诗⑤,不可有章咒气。此固未免于章咒。”(546页)
①纪晓岚:清纪昀字。
②章咒气:毫无文采,如同奏书,文尽意尽。
③僧家诗:指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之作。
④偈(jì寄)颂气:佛教里的赞美诗有一定格式,不论几言,必四句为一偈,到将颂赞之意说尽为止,毫无文采。
⑤道家诗:指那些上天入地求仙访道之作。
李商隐《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这首诗讲的“会静”,指道家凝神养静修炼说,在这时候,作者想象飞腾,就会想到许多神仙故事,如说:
大道谅无外,会越自登真。丹元子何索?在己莫问邻。蒨璨玉琳华,翱翔九真君。……
这是说,修炼神仙的方法,想来只有一种,没有别的。合于这种方法,可以超越人世,自然“登仙”。“丹元子”指道家修心养神的一种方法,怎样求得这种方法,在于自己的修炼,不必去问别人。修炼得道后就可以会见神仙,像会见仙人上元夫人,看到她穿着非常美丽的玉带,看到仙人九真君,在天上飞翔。这样写,就同道士写的章咒讲到神仙的话相似了。清纪昀评点李商隐此诗说:“诗无风旨可采”,“杂之通明(陶弘景)《真诰》中,殆不可辨。然终恨有章咒气。”《真诰》所记皆神仙授受真诀的事,叙述典雅,像给上级写的公文,恭敬庄重至极,朱熹曾怀疑陶弘景撰写此书时,从佛家的《四十二章经》里窃得不少,特别是关于下地狱、托生等荒诞之说,更是窃自佛书中。这里纪昀没有说李商隐从《真诰》中作手脚,但也指出他写得跟《真诰》一样。因为李诗中写升仙经历,就是从《真诰》中学来,李商隐根本没有升仙的事。所谓“章咒气”,就是指诗从《真诰》里来的,带有《真诰》的章咒气。然而,苏轼的《读道藏》却不同:
嗟余亦何幸,偶此琳宫居。宫中复何有?戢戢千函书。盛以丹锦囊,冒以青霞裾。王乔掌关籥,蚩尤守其庐。乘闲窃掀搅,涉猎岂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岁厌世去,此言乃籧 篨。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忧吾未除。
苏轼的诗,是一篇诗体读书笔记,先写《道藏》的来历和存放,以及如何珍视等等,后写道家虚心求悟,像荷花的皎洁。否则厌世而去,气绝之后,用粗竹席裹尸。人皆不注意学道,归于土苴(泥和枯草),何暇治天下,这是我的幽忧。这首诗写出作者对《道藏》的看法,跟道士的章咒气不同,也就是说苏轼的诗写得比李商隐好。指出诗的风格应避免有章咒气,避免有偶颂气。
(七)以诗品作诗
以“诗品”作诗,可上溯《诗•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①;少陵“翡翠兰苕”②,退之“鲸牙龙角”③,滥觞于是矣。(《钱锺书研究》11页)
①吉甫: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助宣王中兴。
②少陵:杜甫。句见《戏为六绝句》之四:“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③退之:韩愈。句见《调张籍》:“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又《送无本师归范阳》:“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贾岛初为浮屠,名无本。
以“诗品”作诗,可以追溯到《诗经•烝民》,尹吉甫作诗送别仲山甫,称所作的诗“穆如清风”,用诗句来讲这首诗。用诗句来讲诗的,叫以“诗品”作诗。最突出的是唐代司空图的《诗品》。《诗品》二十四首,是二十四篇评诗之作,又是二十四首诗,即以诗来评诗。“穆如清风”便是以诗句来评诗,所以是以诗评诗最早的。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也是以诗评诗,用诗句来评两种风格:一种翡翠兰苕,是秀丽的风格;一种是鲸鱼碧海,是雄伟的风格。韩愈的《调张籍》:“刺手拔鲸牙,举飘酌天浆。”是赞美一种雄奇的风格。又《送无本师归范阳》:“蛟龙弄牙角,造次欲手揽。”是赞美一种惊险的风格。此外如刘禹锡的《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韵》:“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棠弃刀尺。”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里称为以诗评诗的“佳例”。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也是以诗体谈艺者,然杜韩以诗评诗最为著名。
为具体了解以诗评诗之体,特列举元好问《论诗绝句》中的几首,以助从中窥见运用绝句形式写作诗论、诗评的一斑。如第一首:“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开宗明义,他对汉魏以来诗作“纷纭”,孰为“正体”,无人评说的情况不很满意,才决意自己以诗评诗。三十首绝句,从汉魏的古诗到宋诗,摘其要者几乎都发表了意见,形成一组有系统有见解的文学批评佳作。元好问对陶潜的评论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陶诗语言天然浑成,内容真淳自然的特点,他很赞赏。元好问是以建安风骨为论诗准则,所以对刘琨、张华,有自己的看法:“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他认为好诗要有风骨,要有悲壮慷慨之气,刘琨正以悲壮取胜,所以赏识;张华虽然儿女情多于风云气,但他以为也胜过李商隐、温庭筠。对待民间文学,他推崇具有清新刚健之气的《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引此四章,便可看出元好问的好恶,他对历代文坛诗作,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理论,有文采,使其成为以诗体论诗的重要作品。
(八)传记通于小说
平景荪《樵隐昔寱》卷十四《书望溪集书左忠毅公逸事后》①云:“篇中自‘史前跪’以下数行文字,奕奕有生气。然据史可法《忠正集》崇祯乙亥十一月祭忠毅文云②:‘逆珰陷师于狱,一时长安摇手相戒,无往视者。法不忍,师见而颦蹙曰:尔胡为乎来哉!’忠正述当日情事,必不追讳,岂易以一言哉。《龙眠古文》一集左光先《枢辅史公传》③亦只云:‘子已至此,汝何故来死!’”按《戴南山全集》④卷八《左忠毅公传》记此事云:“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⑤。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罗而捕之⑥。今子出身犯难,殉硁硁之小节,而撄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又与史、左两文所记不甚合。然《望溪文集》⑦卷九《左忠毅公逸事》中此节文自佳:“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无愧平氏所称“奕奕有生气”。盖望溪、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溪更妙于添毫点睛,一篇跳出。史传记言乃至记事,每取陈编而渲染增损之,犹词章家伎俩,特较有裁制耳(参观《管锥编》117页又《宋诗选注》论范成大《州桥》)。刘子玄读史具眼⑧,尚未窥此,故坚持骊姬“床第私”语之为纪实⑨,只知《庄子》、《楚辞》之为“寓言”、“假说”而不可采入史传(参观《管锥编》165页、1297页)。于“史”之“通”,一间未达。譬如象之杀舜⑩、子产之放鱼⑾,即真有其事,而《孟子•万章》所记“二嫂使治朕栖”、“郁陶思君尔”、“圉圉焉、洋洋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等语,断出于悬拟设想。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堪入小说、院本。儒宗“传记”(参观赵岐《题辞》),何减“园吏”“骚人”之“伪立宾主”哉。当吾国春秋之世,希腊大史家修昔底德自道其书记言⑿,早谓苟非已耳亲聆或他口所传,皆因人就事之宜,出于想当然而代为之词,信不自欺而能自知者。行之匪艰,行而自省之惟艰,省察而能揭示之则尤艰。古希腊人论学谈艺,每于当时为独觉⒀,于后代为先觉,此一例也。(363—365页)
《毛颖传》词旨虽巧⒁,情事不足动人,俳谐之作而已。唐人却有以与传奇小说等类齐举者。李肇《国史补》⒂卷下云:“沈既济撰《枕中记》⒃,庄生寓言之类⒄。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⒅。二篇真良史才也。”评小说而比于《史记》,许以“史才”,前似未见。《山谷外集》卷十《廖袁州次韵见答》云:“史笔纵横窥宝铉,诗才清壮近阴何”⒆,自注:“干宝作《搜神记》,徐铉作《稽神录》,用意亦同”。李卓吾、金圣叹辈评《水浒》“比于班马”(29)、“都从《史记》出来”等议论,阿堵中已引而未发矣。(21)(384—385页)
《望溪集》卷二《书〈刺客传〉后》论太史公“增损”《国策》本文,不啻金针度人(22)。读其《左忠毅公遗事》时,当解此意。参观《管锥编》166页《增订之二》。(《钱锺书研究》11页)
①平景荪:清平步青字。撰有《樵隐昔寱》二十卷。左忠毅公:明诤臣左光斗,为阉党魏忠贤所害,惨死狱中。
②《忠正集》:明名臣史可法撰,四卷。
③《龙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李雅、何永银辑。左光先:左光斗弟。
④《戴南山全集》:清戴名世(字南山)撰,十四卷。
⑤国柱:国家栋梁。
⑥逆党:阉党魏忠贤。
⑦《望溪文集》:清古文家方苞(晚号望溪)撰,十八卷。又撰《望溪集》八卷。
⑧刘子玄:唐史学家刘知几字。撰《史通》二十卷。
⑨骊姬:春秋时骊戎国之女,晋献公伐骊戎,获骊姬,立为夫人,献公卒,被杀。
⑩象:人名,舜之同父异母兄弟。
⑾子产:春秋时公孙侨字。
⑿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腊历史学家,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⒀独觉:独知独觉。
⒁《毛颖传》:韩愈假托毛笔为传。
⒂《国史补》:唐李肇撰,三卷,多记开元、长庆间事。
⒃《枕中记》:唐传奇,写卢生在邯郸遇吕翁事。
⒄指《庄子》一书中的寓言。
⒅史迁:汉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
⒆《由谷外集》:宋黄庭坚撰,十七卷。宝铉:晋干宝,撰《搜神记》二十卷;宋徐铉,撰《稽神录》六卷。阴何:梁诗人阴铿、何逊。
⒇李卓吾:明代思想家李贽字。金圣叹:清代评论家金人瑞字,原名张采。两人评《水浒》,将其比作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
(21)阿堵:唐代俗语,犹言这个。
(22)《国策》:《战国策》,汉刘向编,共三十三篇。不啻(chì赤):犹言不仅,不但。金针度人:犹言传授秘诀。
这里讲到传记、历史散文与传奇小说有相通处。这是三种不同的文体,钱先生认为从不同文体中可以看到相通之处。
平步青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叫好,说文字“奕奕有生气”,不是凭空虚赞,而是与史可法的祭忠毅公文和左光先的《枢辅史公传》、戴名世的《左忠毅公传》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左忠毅公是明代著名的诤臣左光斗,遭到阉党魏忠贤的诬陷,死于狱中。他是人中的伯乐,在史可法还是书生时,便发现他是个人材,给以提携和训导,史可法后来终成抗清名臣。
钱先生举引戴名世、方苞、史可法、左光先四人所写史可法去狱中探望左光斗一段,目的就在于说明不同才力的人运用不同文体所产生的不同效果。现比较如下:
史可法祭文:“法不忍,师见而频蹙(忧愁不乐)曰:‘尔胡为乎来哉!’”左公只说了这样一句感叹的话,可以看作是史可法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
左光先《枢辅史公传》:史可法在狱中见到左公,左公说:“予已至此,汝何故来死!”这是弟弟为兄作传时代言的话,提到了“死”,多了一点危险的内容,进了一步。
戴名世《左忠毅公传》:史可法去狱中探望,左公竟说了六十二个字的话,把入狱的前因后果,都说得有条不紊,并对史可法作了日后的交代。显然这些都是戴氏构想中代左公立言。这个写法在当今的作品中常见运用,是作者生怕读者看不明白,才虚构得头头是道,句句是实话,可惜没有顾及到当时危急的情势,是否有条件说这些话。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最为生动感人。“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仅用九个字,形象地写出史可法探监之难,左公已遭酷刑之惨,都见于言外。接着写左公听到史的声音,却睁不开眼,“乃奋臂”把眼睛拨开,“目光如炬”,怒斥史,说了四十七个字的话:“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把左史的关系,彼此的情感,以及两人不可一世的气概和会见的气氛,都写得“奕奕有生气”,感人至深。
对此,想到以下几点:
(一)方、戴都掌握到史、左狱中会见的实情,好比骨头架子,各人需以自己的揣测和想象附之以血肉,方苞更妙于画龙点睛,更能把握环境,传达史、左两人高贵的品质和情操,以及埋在人们心里对史、左两人的崇敬之情。因此,方苞对人物的刻画和对环境气氛的渲染,都使人觉得合情合理。戴名世则对这些方面把握得不够。
(二)文学作品,无论反映历史事件,还是现实生活,都离不开写人与事,而怎样写才能给人以真实感,从戴《传》、方《逸事》的写法可以得到启示:琐细的表面现象不等于真实,而与所写有关的入情入理之言与事,则不可有所遗漏。如《管锥编》117页写禽言之“拟声达意”,即出于想象。又如《宋诗选注》范成大《州桥》注:“确确切切的传达了他们(沦陷区人民)藏在心里的真正愿望”,“我们读来觉得入情入理”,这也靠想象和体会。不仅文学作品如此,中国工于记言的史籍也不例外。如《管锥编》166页:“《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又如《左传》写骊姬床笫私语,介之推与母亲偕逃前的对话,皆是“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所谓“记言”,皆由史家“悬拟设想”,“揣想生象”,虚拟合情合理的言与事,使其达到“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的效果。所以说文学作品和历史,在写法上有相通之处,就在于摆脱不掉虚构和代言。
(三)韩愈为毛笔作传,虽以“传”名,实则是以传记文学的手法写作的一篇警世讽时之寓言故事。韩愈把毛笔人化,以戏谑的文词写出,引人大笑,发人深思,柳宗元认为司马迁的《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若壅大川”,“必决而放诸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李肇亦认为韩愈此文“不下史迁”,“真良史才”(《国史补》),白居易也赞韩愈“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这些评论皆意在说明文学传记、寓言故事与史的写法有相通之处。
(四)不仅中国有文学作品通史的看法,希腊大史学家修昔底德也称自己书中的记言,并非亲耳所听或他人相告,而是“因人就事”,根据自己的设想揣摩,代为立言。因此,这里指出史家与作家不能自欺欺人,自己应当首先明白这一点。《管锥编》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录于此作为补充。钱先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并举例说:“《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左传正义•隐公》)真是切当宏伟的高论。
(五)由此,联想到《管锥编•全宋文卷三四》的一段话颇有深意:“据此以订史,是为捕风捉影,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又云:“吾国子书(笔记小说类)所载,每复类是。均姓名虽真,人物非真。有论《庄子》中膺篇《盗跖》者,于其文既信伪为真,于其事复认假作真,非痴人之闻梦,即黠巫之视鬼。”可惜,《管锥编》出版迟了,早在1975年批儒评法之际,闻知某院校正在新编文学史,其所谓新者之一,便是增加了没有作品的作家盗跖的章节,显然是上了《庄子》的当。由此可见,钱先生所指出的,对治史治文者均有裨益。
(九)八股文通于戏曲
八股古称“代言”,盖揣摹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优之道①,扶圣贤之心。董思白《论文九诀》之五曰“代”是也②。宋人四书文自出议论,代古人语气似始于杨诚斋③。及明太祖乃规定代古人语气之例④。参观《学海堂文集》卷八周以清、侯康所作《四书文源流考》⑤,然二人皆未推四书文之出骈文。窃谓欲揣摩孔孟情事,须从明清两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汉宋人四书注疏,清陶世征《活孔子》⑥,皆不足道耳。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故与杂剧传奇相通。徐青藤《南词叙录》论邵文明《香囊记》⑦,即斥其以时文为南曲,然尚指词藻而言。吴修龄《围炉诗话》卷二论八股文为俗体⑧,代人说话,比之元人杂剧。袁随园《小仓山房尺牍》⑨卷三《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一书,说八股通曲之意甚明。焦理堂《易余籥录》卷十七以八股与元曲比附⑩,尤引据翔实。张诗舲《关陇舆中偶忆编》记王述庵语⑾,谓生平举业得力《牡丹亭》,读之可命中,而张自言得力于《西厢记》⑿。亦其证也。
此类代言之体,最为罗马修辞教学所注重⒀,名曰prosopopoeia⒁,学僮皆须习为之。亦以拟摹古人身分,得其口吻,为最难事。马建忠《适可斋记言》⒂卷二有《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记卒业考试,以拉丁文拟古罗马皇贺大将提都征服犹太诏等⒃,即“洋八股”也。(32—33页)
董思白《论文九诀》不见《容台集》中⒄,李延昰(古文“夏”字)《南吴旧话录》卷四记董行书《制举文办法》手卷⒅,佳绢二十余丈,旧藏李氏,为马士英勒索以去⒆。备载其文,说“代”曰:“代当时作者之口,写他意中事。如《逍遥游》代鷟鸠笑大鹏⒇,说曰:‘我决起而飞’云云。太史公称燕将得鲁连书曰(21):‘与人刃我宁自刃’”(参观《管锥编》164—166页)。《容台集•文集》卷二《俞彦直文稿序》亦云:“往闻之先辈云:岭南廖同墅为孝廉时,以行卷谒吾乡陆文裕公。公谓之曰:‘曾读西厢、伯喈否。’(22)廖博雅自命,不读非圣书,颇讶其语不伦。又经月,复以行卷谒公。公曰:‘尚未读二传奇何也。’廖始异其语,归而读之。’倪鸿宝有《孟子若桃花剧序》,见其弟子郑超宗所选《媚幽阁文娱》中(23),未收入《倪文贞公文集》,略云:“文章之道,自经史以至诗歌,共禀一胎,要是同母异乳,虽小似而大殊。惟元之词剧,与今之时文,如孪生子(24),眉目鼻耳,色色相肖。盖其法皆以我慧发他灵、以人言代鬼语则同。而八股场开,寸毫傀舞。宫音串孔,商律谱孟(25);时而齐乞邻偷,花唇取诨;时而盖驩鲁虎(26),涂面作嗔;净丑旦生,宣科打介则同。”贺子翼《激书》(27)卷二《涤习》略云:“黄君辅学举子业,游汤义仍先生之门。每进所业,先生辄掷之地,曰:‘汝能焚所为文,看吾填词乎。’乃授以牡丹记。闭户展玩,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变化,在于是矣。’由是文思泉涌。”袁子才《小仓山房尺牍》(28)卷三《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云:“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29),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摩口吻为工,如作王孙贾(30),便极言媚灶之妙,作淳于髠、微生亩(31),便极诋孔孟之非。犹之优人,忽而胡妲,忽而苍鹘(32),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妇奸臣,此其体之所以卑也。”李元玉《人天乐》(33)第十七折亦云:“昔年诸理斋负笈遨游,囊中惟携《西厢》一卷,说道:‘能活文机’。”何屺瞻《何义门先生集》卷十《书塾论文》反复于八股须“顺口气”(34),正董、倪所谓“写他意中事”(35)、“以人言代鬼语”耳。陶世征《活孔子》梗概见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八(36),余未得而读也。(360—361页)
①俳优之道:俳优俗谓滑稽戏,此指不庄重的方法。
②董思白:明董其昌,字元宰,号思白。
③四书文:用“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出题作文,自发议论,宋时称为时文。《学海堂文集》卷八侯康《四书文源流考》:“四书文,今谓之帖括。帖括二字始于唐。”宋宝应二年,杨绾上疏请废帖括,“神宗熙宁四年,用王安石议,更定科举法。”郑灏若《四书文源流考》:“四书之文,原于经义,创自荆公。”但在写作上,这种时文,用排偶句法,代圣贤立言,又似始于宋杨万里(号诚斋)。因侯康《四书文源流考》中又说:“惟杨诚斋传文三首,汪六安传文五首,与今体略同。”
④侯康《四书文源流考》:“至代古人语气,则起自明初,乃明太祖与刘基所定。”《明史•选举志》: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试士,“盖明太祖与刘基所定。”
⑤《学海堂文集》:清阮元编,十六卷。其卷八有《四书文源流考》。
⑥陶世征《活孔子》:清陶世征平生模学孔子,由一部《论语》追想孔子之神貌,遂写《活孔子》。
⑦徐青藤《南词叙录》:明徐渭(字文长)自号青藤山人。著《南词叙录》。《叙录》专论南戏,称:“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邵璨字)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诗经》杜诗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即指斥他以时文的排偶句作南曲。
⑧吴修龄《围炉诗话》:清吴乔(字修龄)撰,六卷。论八股文为俗体:“学时文甚难,学成只是俗体,七律亦然。……自‘六经’以至诗余,皆是自说己意,未有代他人说话者也。元人就故事以作杂剧,始代他人说话。八比虽阐发圣经,而非注非疏,代他人说话。”
⑨袁随园:清袁枚(字子才)因卜居江宁小仓山之随园,自号随园老人,仓山居士。
⑩《易余籥录》:清焦循撰,二十卷。卷十七称:“元人曲止正旦正末唱,余不唱。其为正旦正末者,必取义夫贞妇忠臣孝子厚德有道之人。余谓八股文口气代其人说话,实为本于曲剧。而如阳货、臧仓等口气之题,宜断作,不宜代其口气,是当以元曲之法如法。”即认为对八股中写到的坏人,不当代坏人口气说话。
⑾张诗舲:清诗画家张祥河,有《小重山房集》、《南山集》等。王述庵:清王昶,字德甫,号述庵。
⑿这里讲戏剧代剧中人说话,与八股代圣贤说话,代人口气相同,所以读了《牡丹亭》、《西厢记》,对写八股文有帮助,并可考中。《牡丹亭》: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代表作,写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西厢记》:元代戏曲家王实甫代表作,写书生张珙与崔莺莺恋爱故事。
⒀罗马:古罗马帝国。
⒁Prosopoeia:译音“普罗索珀皮亚”,意即修辞学上的拟人法,使虚幻的人物具体化,或使抽象的事物人格化。
⒂马建忠:清人,曾游学法国。撰有《适可斋记言》四卷,《记行》六卷。
⒃拉丁文:古意大利罗马人的语言为拉丁语,文字为拉丁文。犹太:指古罗马时代犹太人的故国巴力斯坦。诏:向下属发布的文告。
⒄董思白: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号,有《容台集》二十卷。
⒅《南吴旧话录》:清李延昰(初名我生,字辰山)撰,二十四卷。
⒆马士英:明魏忠贤奸党,字瑶草。
⒇《逍遥游》:《庄子》名篇,寓言。鷟鸠:斑鸠。《逍遥游》:“蜩(蝉)与学鸠笑之(大鹏,一飞九万里)曰:“我决(疾貌)起而飞,枪(突)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21)太史公:司马迁。指《史记•鲁仲连传》。
(22)西厢:即《西厢记》。伯喈:元代戏曲家高明(字则诚)撰南戏《琵琶记》的男主人翁,姓蔡名伯喈,赴京应试,中状元后,历经种种磨难,最终与贤妻赵五娘团圆。
(23)倪鸿宝:明代书画家倪元璐,字玉汝,号鸿宝。郑超宗:明郑光勋。有《媚幽阁文娱》一卷。
(24)孪生子:双生子。
(25)宫音串孔,商律谱孟:指用八股文的排偶句代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宫商指音律,八股的排偶句要合于对偶句的音律。(26)齐乞:《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是写齐人出外乞食。邻偷:《孟子•滕文公下》“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盖驩:《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与盖大夫王驩出吊于滕,驩独断独行,孟子不与驩说话。鲁虎:《论语•阳货》讲孔子遇阳虎事。阳虎即阳货。这里是指八股文中代这些人说话,好像戏剧中的生旦净末丑都有。
(27)贺子翼:明贺贻孙字。有《激书》二卷。
(28)袁子才:清袁枚字。有《小仓出房尺牍》十卷。
(29)优孟衣冠:春秋时,艺人优孟,善诙谐,曾在孙叔敖死后,著其衣冠,代其子争得封地,后人以此称假装似真者。
(30)王孙贾:春秋时人,欲使孔子赏识他,对孔子说:“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为孔子拒绝。奥,黑暗的墙角。
(31)淳于髠:战国时人,滑稽多辩。《孟子•离娄上》,淳于髠责问孟子为何不援天下。又《告子下》,淳于髠讥孟名实不副。微生亩:春秋时隐士,尝问孔子:“丘何如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
“非敢为佞止,疾固也。”
(32)胡妲:旦角的一种。周密《武林旧事•舞队》称傀儡戏有粗妲、细妲。苍鹘:戏曲中的副末。《辍耕录》:“鹘能击禽鸟。”
(33)李元玉:清李玉字。《人天乐》见《古本戏曲从刊三集》,撰者署笑苍道人。《曲海总目提要》云黄周星撰。第十七折《净旦》:“小生:‘那稗官野史之书,虽是俚词,无非学问,若是会读书之人看之,大可触发聪明,增益意智,所以杨升庵《词品》上说道: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昔年诸理斋负笈遨游,囊中惟携《西厢》一卷,说道:鸢飞鱼跃,能活文机,莫过于此。冠翁读破万卷,想于此道亦必留心。’”
(34)何屺瞻:清何焯字,号义门。有《何义门先生集》十二卷。卷十《书塾论文》:“八股与讲义区别者,在顺口气,而今人顾乃莫之也。口气非描头画角所能有,举其隅,亦曰观圣贤之气象而已。明季以来……若《论》《孟》文字,口气概乎无辨也。”
(35)董倪:董其昌、倪元璐,皆明代书画家。
(36)唐鉴:清人,字镜海。有《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
一般文学史讲到明清两代文学,多注重小说、戏曲,故使一般读者对诗文知之甚少,尤其是八股文,是怎样一种文体,有些什么特点,了解不多,仅将它看作是应举的必修课。这里两则指出八股文的渊源、与戏曲相通的特色,均为前人所未明确论述的。
(一)八股文是骈俪的支流,对仗的引申。清阮元在《揅 经室三集》云:“洪武永乐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是四书排偶之文,上接唐宋四六。”此番话仅将这种文学现象追溯到唐宋四六文句对偶的影响,清人周以清、侯康专门研究四书文的源流,也没有触及到四书文出自魏晋六朝的骈文,钱先生在此作了补说。这里不妨举出几个事例,如初唐四杰对比已多,杨炯集里骈体比比皆是,如《群官寻杨隐居诗序》有云:“天光下烛,悬少微之一星;地气上腾,发大云之五色。”又“寒山四绝,烟雾苍苍;古树千年,藤萝漠漠。诛茅作室,挂席为门。石隐磷而环阶,水潺湲而匝砌。”又如《大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云:“由是五噫标兴,播金石而腾徽;七贵承荣,绾银黄而叠茂。”又“西园坐宴,侣明月而飞文;北土行康,望浮云而展足。”等等,都是两两相对的句式。“六代语整而短”,如梁代吴均的《与宋元思书》有云:“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排比对偶句式,亦可见一斑。这里将八股文排偶句的渊源直接追溯到六朝的骈文。八股文只是六朝及唐四六文的发展,每股的字数多于四字六字句。
(二)八股文与杂剧传奇相通。八股文古称“代言”,是就它依据四书五经,揣摹古人思想口吻写作的一种方法而说的,“代言”者,即代替古人说话。这里指出太史公称燕将得鲁连书曰:“与人刃我宁自刃。”(参观《管锥编》)即指出史家已有代言体。“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钡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而“设身处地,发为文章”很重要,犹如对演员的要求,要求他能进入角色,表现角色。或“代当时作者之口,写他意中事。如《逍遥游》中代鷟鸠讥笑大鹏”说的话,实际上是庄子代鷟鸠讥笑大鹏说的话。清代陶世征,他从《论语》中追想孔子当日的声音笑貌,处处模仿,维妙维肖,说明八股文与戏剧相通。明徐渭《南词叙录》指出邵璨的《香囊记》里混有四书文排偶句,让不识字的人也用《诗经》、杜诗来讲话,不是按照角色的口气说话,因而失败了。这里还举引了清人吴乔将八股文的代人说话看作是“俗体”,与元杂剧的代人说话有相似处。袁枚曾说八股通曲,焦循也将八股文与元剧比附,认为元剧不让坏人唱曲,八股文也该不代坏人说话。明清两代盛行八股文,所以研治者也多,但是论说最为透彻的是明倪元璐,他将元剧与八股文看作双胞胎,“眉目鼻耳,色色相肖”。最耐人寻味的是例举两位应试者成功的经验之谈,都说自己所以能考中,有赖于熟读过《牡丹亭》、《西厢记》的缘故,学会了代人说话的本领。
(三)八股文不是中国独有的文体。这里举出罗马的修辞教学也注重普罗索珀皮亚,即拟人法的讲授,让小学生就开始学习怎样使虚幻的人物具体化,或使抽象的事物人格化,他们也认为揣摹古人声口,摹拟古人身份最为难事。这里还举到《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在留学期间的结业考试,便是代古罗马皇帝拟写诏书,并风趣地称之为“洋八股”。看来,在“代言”这一点上,中外有相类似之处。说明这种代言体要体会古人的神情,用古人的口气说话,是一种学童必须学习的修辞教学。但这种代言体只代古人说话,不说自己的话,所以吴乔称它为“俗体”,贬低它的价值。